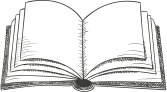
2.两次鸦片战争
马嘎尔尼北上之时,中英的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除了一般商品贸易之外,鸦片贸易也以灰色方式进行着,而后者之所以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商品贸易无法在中国打开市场。
无法打开市场的原因,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 1852年英国官员米切尔写信给乔治·文翰爵士,就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国际贸易之间的格格不入。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粗斜纹布和平布重量的三倍。

小农经济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使得中国人可以自给自足。他们的家庭小手工业因为是在农闲或者农余时间进行,这些时间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副业甚至就是一种填补生活空白的需要,因此也就没有人工成本的概念。
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投入与产出的精密计算以及低成本即可抢占市场的信念相违背。米切尔对此的解释非常详细: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英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庞大市场”,是根据他们自身习惯的逻辑想象出来的。
前面提到,宫崎市定更加简洁地指出过这一矛盾:西方人试图卖给中国人刀叉和钢琴,并且试图在地处亚热带的广州销售毛衣和纺织品,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然而英国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则是刚性的,一开始,丝绸、瓷器、香料、药草,尤其是茶叶,都是奢侈品,但英国社会习惯之后,就在 18世纪转为了生活必需品。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指出,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发展为占 19世纪英国家庭年平均收入 5%的支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增长,从 17世纪晚期约每年 200磅,到几十年后约 40万磅,再到 19世纪初期的 2800万磅。“对于崇尚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支付这些茶叶。”

在矛盾推动下,英国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拓展鸦片贸易,因为这是一种一旦接触就无法抗拒的商品,并且它的成瘾性会让需求循环增加。
此时的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把货物运到中国非常便利。鸦片最早在唐代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但中国传统上主要用于医药。被作为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是由东印度公司推动的,它在南亚种植的鸦片很快取代棉花成为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
从 18世纪晚期到 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 10倍。到了道光初年,已有多达六分之一的英国王室税收来自中国贸易,如果没有关键商品鸦片的贩卖,这一贸易早已崩溃。所以尽管一些有良知的商人意识到这样做的罪恶性,传教士也时有谴责——比如亚历山大·马地臣就从其参与创建的怡和洋行辞职,不愿继续在中国推广毒品——但英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如果触动了这一利益,唯一的结果就是战争,而清朝政府的决定马上就要触动这一利益。
尽管鸦片贸易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但清朝政府并未承认其合法性。雍正时期就禁止贩卖和使用鸦片,即便是道光帝也未曾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上松口,鸦片贸易的事实上合法化是在咸丰八年对其征税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据估计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吸食鸦片上瘾,士人军队尤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效能。而鸦片泛滥带来的最大麻烦是贸易失衡,白银外流,国内物价飞涨,财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威胁。
经过了政权上层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道光帝决定强力禁止鸦片贸易,把立场强硬的官员林则徐派到了广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毒品贸易的冲突下最后打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有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在销毁鸦片的同时,他在广东进行了严密的布防,以战争准备宣示禁烟的绝对决心。但英国人并未在广东过度纠缠,而是沿着海岸线挥师北上,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英国人在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后拿下镇江,等于掐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
京杭大运河是明清两代的经济动脉。 1415年,为了避开倭寇骚扰,明朝停止了海运,所有货物流动均走漕运。其中京杭大运河一般占据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三,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也集中在运河沿岸。清朝继承了这一运输格局,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期间。所以长江下游一被攻击,清朝很快就丧失了抵抗意志,提出议和。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除了割地(香港岛)、赔款( 2100万银圆),还要增加通商口岸,从原来的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不但拥有了一块完全控制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商业和军事的桥头堡,而且成功地把贸易前沿推进到长江下游,这样既利于他们的产品销售,也能更便捷地收购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产。由于在上海能收购到的物产远比广州丰富,价格也更便宜,欧美各国随后纷纷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由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一举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
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扩大其产品(主要是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一段时间里,确实发生了白银回流的状况,但好景不长,顺差很快又被逆转。基于同样的目的,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在前后十几年间发生,它们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事实上是两场白银战争,是西方工业国家以军事为经济利益开路的典型案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马克思,正在英国伦敦,他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时事分析文章,主要涉及的就是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冲突背后的逻辑。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金融根源:
在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银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建立领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输出白银还不怎么能觉察到。到 17世纪初,荷兰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同东亚的贸易,这种金属的需要量才增加,但真正大量增加则是从 18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迅速增长以后,因为英国人为购买中国茶叶汇去的几乎完全是白银。到 18世纪后期,白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乃至吸收掉很大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
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白银流通,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动,有过互相交替的高潮时期与低潮时期。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性运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7世纪起到 1830年左右,第二个时期从 1831年到 1848年,最后一个时期从 1849年到现在( 1856年)。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输出的白银,总的来说是增加的。在第二个时期,这种输出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出现回流,亚洲第一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纪内吸收去的财宝的一部分源源输还欧洲。在第三个时期,——目前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上升阶段——情况又变回去了,亚洲以空前的规模吸收着白银。

战争的开始,都需要一些堂皇的借口,比如销毁鸦片破坏贸易规则、“亚罗号”事件中中国士兵侮辱英国国旗……但最根本的事实则是,在“自由贸易”中,只能强者获益,为了获益可以采取任何不道德的手段。如果你妨碍我获益,或者客观上我无法获益,我就对你动武。
中国人所认识的强权世界,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对于世界究竟是不是绝对的丛林社会,后来者一直还是心存幻想,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玫瑰色想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社会还对威尔逊抱以“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在这最后的一次期待破灭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彻底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