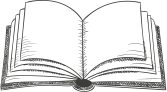
3.衰落的“国祚”和太平天国的鞭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耻辱史,而这部耻辱史是从道光时代开始的。清朝皇帝的气质变化,也从道光开始。
过去的皇帝一般杀伐决断,说一不二,但自道光以来,就变得左右摇移,立场非常不坚定。一时要战,一时要和,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逃跑主义交叉上演。
道光时期,是清朝“国祚”衰退开始表面化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入关 100多年后通过军事征服、文化融入、意识形态控制、对士人阶层的收买与“感化”以及政权建设而树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从道光起进入了瓦解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展开的,一步一步越发深入和艰难的互动,使得中国朝野建立于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自信心逐步崩溃。
面对英国人时,道光帝在战和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这样的高层立场,严重影响军队士气。然而道光其实还不算一个坏皇帝。一般而言,历史上以“宣宗”为庙号的皇帝,大多并非昏聩无能之主。
1813年(嘉庆十八年),李文成、林清率领 100多名天理教教徒,在内线太监接应下从隆宗门攻入紫禁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手持火铳,当场打死两名造反教众。这时的道光可谓英气勃发,年富力强的他喜爱西洋火枪,据说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就感慨万端,思考中国人何时才能制造出如此精致的产品。
把国势衰弱归咎于某几个皇帝或少数高层统治者,这样的思维既简单幼稚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在“李约瑟难题”的笼罩之下,在西方近代科技优势的压迫之下喘不过气来。
而就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国家能力方面逐步倒转的过程中,中国反而越发封闭起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感知越来越稀缺。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就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部分中国人了解了这些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其开放程度比明朝大幅倒退,在与外界的科技交流、从外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大不如前。乾隆时,当英国使团出现在眼前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还认为西洋人没有膝盖,腿是直的,所以只要突破火力范围进行近身搏击,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了。由于西洋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个说法也流传开来,即西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大黄,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因此只要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就可以不战而胜。
此类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知识”,在当时却是举国共享的,就连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林则徐,一开始也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中国还能维持着传统的区域性朝贡体系格局,不必与更大的世界交流,那么这种对外域的无知以及在生产方式、科技发展方面的落后并不会对文明生存产生恶果。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它将永此终古”。
然而问题正在于西方的蒸汽动力舰船已经开到了家门口。那些来往于广州的商人,连接着万里之外的工业生产,而在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自我循环、增殖与扩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机制,一个个商人,事实上是“人格化的资本”。
这个时候的英国,机器生产已经逐渐普及,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工场手工业。蒸汽动力的机器是高效的、不停歇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维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广阔的原材料来源和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二是机器的高效率积累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部分剩余,作为新的资本投入生产,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正如大卫·哈维的分析,“如果他们不能找到它的出路,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在英国国内,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迅速扩大,资产者通过雇用更多的仆役来消耗剩余并向社会释放购买力,同时服务于机器生产的机器制造、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掘等行业也在迅速扩大。然而这还远远不足以抵消机器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后带来的生产力膨胀。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说:“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瘫痪是资本主义最可怕的状态,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地理和时间的转移,来解决资本剩余的处置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是一种社会必需。于是,“从 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扩大亚洲市场”。

这个“毁灭人种”的办法,就是鸦片贸易。
要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把它放到比我们快一拍的西方现代史的视域下去打量,这是无法回避的。先进、落后,胜利、失败,都与当时客观的大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资本主义是一个天生的进攻型机制,而传统的中国文明则是防卫型的。过去的防卫有效,建基于冷兵器战争的背景,而现在打上门来的新的“蛮夷”,是以机械动力和火器武装起来的。作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一战,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清朝一败涂地,清帝国第一次向“蛮夷”低头,签下城下之盟。
外因推动着内因起作用,内患由此而生。
我们再次回首马嘎尔尼对北京的访问,当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开放广州以北的更多港口。乾隆皇帝拒绝了所有要求。不仅是因为礼仪问题,还有现实考虑——担心突然的路线更改,会让传统的南北货物运输线上产生大量失业者。当时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经历长距离运输,而且必须越过五岭的天然障碍才能抵达广州。这种低效率的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乾隆虽已年迈,但对内部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依然清醒。宫崎市定指出,开放的港口北移,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失业,而且动摇了清朝国本——太平天国运动正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之后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因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由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

一批愤怒的游民,在一个四试不第的愤怒的草根领袖洪秀全带领下,揭竿而起。正是沿着他们最熟悉的广东、广西、湖南再到长江的传统货运线路,一路杀去。历时 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创建新的国号,并定都天京(南京)。
祸不单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个时期”—— 1849年到 1856年,白银再次回流中国,英国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打到北京城,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由于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自称与西方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将他们引为“兄弟”,对西方国家资产富集的上海也没有发动真正有效的攻击,所以前期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一直持观望态度。《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国家基本确认了一个逻辑,那就是维持腐朽的清朝政府的统治最为符合自身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对中国予取予求——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清政府被革命推翻。于是他们和清政府联合起来,一同对太平天国发起了围剿。
清朝在合作围剿中,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士大夫深受震撼,同时也产生深刻的忧思。
本书开头提到的胡林翼“突然晕倒”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这一现实。太平天国的军队,其思想武装或曰控制工具,虽然是被歪曲的基督教思想,但这的确让他们对洋人以及他们的器物持有比清政府系统内部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支军队在前期和中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和他们大量使用西洋火枪密切相关。在长达 14年的军事对抗中,他们的表现也推动着作为对手的清政府重新认识了西方器物,尤其是武器,并产生了态度转变。后来的自强运动,也称为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被刺激的结果。
太平天国造成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其带有浓烈的绝对平均主义味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超前的主张仿效西方发展实业和改造社会制度的《资政新篇》,虽说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施,却以成文的形式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启发。
在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社会动员,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知道,后来孙中山先生正是沿用并且完善了这一口号,用以号召共和革命。本来,这一口号应该是有煽动力的。清朝作为外族政权,合法性始终存在疑问,而当时面对西方侵略,结果都以丧权辱国告终,合法性危机正是爆发的时机。然而“拜上帝会”既纵容了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想象力,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眼光。
“拜上帝会”以基督教一神论,横扫一切民间信仰,拆毁庙宇砸碎菩萨,让贫苦人民突破思想障碍跟随起义,这对运动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它对待儒家信仰,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就把自己和整个士大夫、知识分子系统对立起来。
洪秀全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事实证明后果非常糟糕。他自称上帝次子,是耶稣的弟弟,称呼耶稣为“天兄”,称呼上帝为“天父”。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说自己见证过上帝召见孔丘的过程,上帝指责孔子写的书都是错误的,中国民不聊生,都是因为他的误导,把人教坏了,于是就动手把孔子暴打了一顿,打得他屁滚尿流,不断求饶。
这个瞎编乱造的故事无形中惹了大麻烦,士大夫、知识分子尊敬皇帝,但在皇帝与孔子之间,后者的地位更高——所谓“道统”,这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存在的价值。你可以说后人对孔子的理解是错的——正如后来康有为所做的那样,但不能直接说孔子错了,这对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一种极限侮辱。洪秀全不但这样做了,还说孔子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人之常情,这么干谁受得了?于是我们就发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应该能号召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加入起义行列,但结果最后却是他们出头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清朝是外族政权,但它是归化儒家、尊崇儒家的,所以对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儒家信仰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没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参与的起义,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而当我们回顾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时,则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门面功夫,这些人是认同还是反对,直接决定了起义的最后结局。
太平天国的反儒家立场,之所以能激起汉族士大夫起而反对,是因为它提示了一个现实: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权危机,还是文明危机。也就是说,不但可能亡国,还可能亡天下。亡国因为亡的是异族之国,可以由他去,但亡天下是儒家文明亦即中华文明的灭亡,这是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儒生们所不能袖手旁观的。
当然,即便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消灭清朝,也不见得就意味着“亡天下”,洪秀全尽管摆出彻底的反儒家姿态,但其本人却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内心里是服膺这一个体系的。真正的“亡天下”的威胁力量,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内部斗争中对此有了深入认识之后,这些人紧接着就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坚。
对于“曾左胡彭”而言,他们的出手,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以器物的效仿为特征。历史是交错进展的,李泽厚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分界线,但文化意义上的救亡,应该说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
我们说过,洋务运动的肇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刺激,它的刺激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拜上帝会”,一个和儒家对立的伪意识形态,竟然可以发动半个中国,这是过去欧洲国家的在华传教活动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局面。
二是《资政新篇》里表述的虽然不曾“落地”但却系统性超前的设想,带来了制度忧思。洪仁玕这一套西式制度表述,在当时的中国是新鲜的,但对于少部分相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而言,这也已经是他们思考中西差别的知识背景。容闳造访过天京,和洪仁玕有过一番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议,说明洪仁玕其实并不孤独——有些考虑,甚至比洋务运动之后的戊戌维新还要激进。
三是作为西洋文明的代表的器物——洋枪洋炮的威力在太平天国的采用、湘军淮军的引入以及欧洲雇佣军的演示下,造成了极强的军事、政治震撼。
从文明存续的角度,我们把这三个刺激条分缕析一下。
“拜上帝会”看上去当然就是要直接消灭儒家(尽管本意未必如此),所以汉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就被惊扰了。
《资政新篇》对西方制度、经济和社会运作的介绍——更具现实威胁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一个临时、局部的政权很有可能移植这个系统,让中国精英感受到了制度危机,而制度是保证儒家文化运作的强制力。
洋枪洋炮,以及发射洋炮的西方舰船告诉人们,意识形态、文明、制度,其实就是靠它们开路。
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近代(对于西方而言就是现代了)军事技术,可以对内平叛,对外御侮,就意味着制度可以保存,进而文明可以无恙。
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汉族精英奋起了,洋务运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