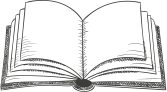
4.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果
把上一段用到的天真二字打上引号,意思是不要苛责前人,他们不是真的太过稚嫩,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能允许他们做到这一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洋务派在后人看来,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中体西用”以及在这个概念笼罩之下具化而来的“唯武器论”,最后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后看来理所当然,但即便是“唯武器论”,也已经非常不容易。
就在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作为极端守旧派的领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蒙古学者倭仁先生的话是有经典出处的,《礼记·儒行》里记载,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倭仁先生在当时是代表清流,这是从汉朝开始,“道统”被政治化以来,中国政治运转当中一直存在的一股制约力量。它有时很先进,有时很“反动”。它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将近 2000年时间里(表面上)确实是依赖这一套体系在运转,运转成功的条件在于,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在这个封闭世界里儒家文化圈是绝对的强者。到了清朝中后期,这个运转成功的条件已经消失了,但清流并未知觉——或者说,因为利益立场,无法知觉。
我们不能说倭仁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知道世界变化,不了解一种强迫性力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穿透力——前面已经由同时代的马克思解释得很清楚了。
在胡绳先生看来,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分歧,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致的目的,都是维护清朝的统治基础。只不过,洋务派认为不变等死,而极端守旧派认为变则速死。
反正,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历史的结果,也不能离开人力的赞襄。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一些新意,让它和过去的农民起义有很大的不同,用宫崎市定的话说就是“动摇清朝国本”。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但它本身是动态延续的,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震撼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持续地体现“动摇清朝国本”这一后果。
和太平天国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咸丰帝逃避到热河,皇帝把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䜣留在被英法联军占领的京城去张罗议和事宜,其中可能包含借用外力消灭这个精明的弟弟、至少让他身败名裂的意图,但谁知这次主持议和这一最重要的“朝政”,反而成就了恭亲王,把他推到了世界的前台。
咸丰帝在《北京条约》达成之后迅即去世,恭亲王和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成为真正的实权者。恭亲王,以及他所能运用的权力资源,从此以后就成为改革派的核心。
所以,恭亲王的“冒头”,标志着洋务派的抬头。
恭亲王代表清朝签订的《北京条约》,涉及三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事方的英国、法国,以及趁火打劫的俄国,每一方都有一个版本的《北京条约》。在中国人的感受当中,俄国是传统的强盗,目的是抢占土地,中国此番在它的趁火打劫中失去了 4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英法则主要还是开放、赔钱,为一目了然计,我们把条约的概要内容罗列一下。
中英《北京条约》:
1.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
2.清朝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3.清朝增开天津为商埠;
4.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 800万两;
5.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
6.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中法《北京条约》:
1.清朝批准中法《天津条约》,赔款增为 800万两;
2.归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财产;
3.中文版条约第七款明定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及建造自便,但法文版无此条;
4.清朝同意开放大连为商埠。
在中国近代史上,俄国从中国取利最多,它的存在往往也成为多方博弈的撬动力,或曰借口。但就世界格局而言,俄国仍然属于与中国清朝同类的前现代帝国,它在趋势对抗中的角色意义并不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对象还是西欧列强。
定下了这个基调,我们再回头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结果的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里面都提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事实上是在此基础上的加码。
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天津条约》呢?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原本应该在 1858年就结束了, 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1858年攻陷天津大沽口,到了天津,清政府就已经受不了了,马上派人议和,签订《天津条约》。
“要盟无质”——被强迫订立的盟约,没什么诚信可守,这是中国的传统认知。清朝本来就在所谓“国际法”的系统之外,签订和约在朝廷理解上本就有羁縻、拖延的意味,于是后来又提出英法使节常驻北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等节,“最为中国之害”,需要再次商量。英法对此无法接受,要求按照一年后正式换约的约定进京换约,与清朝最高统治者最终确定条约内容。
这就涉及一个将近一甲子的老话题了——西方使节如何“面圣”。马嘎尔尼在 1793年的到访,不是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接触西方人,但从那一次以后,中国统治者就觉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中国,“皇帝”诞生于秦始皇,这是中国郡县时代的开端。在秦始皇以前,最高的统治者是王,而王是有统治范围的。皇帝的统治是没有范围的,孟子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对这样一种设想(理想)的现实化。皇帝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君主,还是地球上(天下)所有人的共同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身份可以和皇帝对等,这是唯一的,是一个专有名词,因而不需要任何修饰,不需要任何限定。所以秦朝皇帝,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就是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在时间上它也是绵延接续的,所以就连年号,都是后来汉朝的发明,秦朝并不需要。后世一直继承着对皇帝这一先验性地位的理解,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航海——开始之前,这一理解也可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里通行无阻,历代沿袭。
清朝的不幸就在于,它是从“历代”中剔除出来的,它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所以,所谓真正的威胁,就是西方人的对等要求。和中国交往过程中,英王乔治三世曾经两度给乾隆捎带私人信件,在第二次的信件中自称“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护者”,以及“海上霸主”。
 一方面强调本国的强大和个人的尊荣,另一方面也有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含义。
一方面强调本国的强大和个人的尊荣,另一方面也有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含义。
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对被称为“夷”非常不满,屡提抗议。 1832年英国商人林赛等到上海谋求通商,上海道台在复文中便称他们为“夷国”的“夷人”,林赛等对此很不舒服。后来中英《天津条约》的第 51款中,特别强调:“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于是往后的外交正式文书就以“洋”字代替“夷”字。
进京换约,必然涉及的就是对等问题,而皇帝最不愿意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使节常驻北京的影响,用当时的话来说则是,朝廷已“为外夷所监守”。
中华文明衰落的危机,是各方已经感受到的,但如果“夷人”的国君可以和皇帝对等,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这一现实,而这将对帝国的统治基础造成信仰上的威胁。即便《天津条约》已不可更改,皇帝也不希望在北京换约,至少在京城以外换约还可以留点体面,表明屈辱的条约并非皇帝亲自负责的。所以尽管已经对西方列强难以招架,咸丰皇帝仍然拒绝他们的使团进京。
英法强行进京,在1859年二次攻击大沽口。这个时候防卫大沽口的是蒙古王爷、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他率部奋起抵抗,在一昼夜的炮战中击沉敌舰4艘、重创敌舰 6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 484人,重伤英军海军司令贺布。这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像样的胜仗,连马克思都在文章中赞扬中国人的反侵略精神,他写道:“ 6月 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 2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军遭重创后只得退却。”

1860年初,英法两国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兵力,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咸丰皇帝多次在战与和之间反复,英法一步步逼近北京, 1860年 9月 21日,他们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僧格林沁的部队几乎全军溃散,侵略者兵临城下。咸丰皇帝在听到八里桥败绩的消息后逃到了热河行宫。
10月 18日,英法联军在一番抢劫之后,纵火烧毁圆明园。
如果说洗劫对于西方军队而言是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那么纵火则是一种附加的惩罚。一则为了惩罚清朝的缺乏诚信、“出尔反尔”,二则报复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的胜利,三则他们进入北京后发现前面派出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受到了虐待,一部分人还被折磨致死——这是前现代中国的“传统”。按照《哈佛中国史》的说法,“暴怒的额尔金”曾考虑烧毁紫禁城,但后来只破坏了城北的圆明园。“他推论这样就足以惩罚清廷而罪不及中国的好人。”
 总之,烧毁圆明园在英法的视角下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一个比烧毁紫禁城更不坏的结果。
总之,烧毁圆明园在英法的视角下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一个比烧毁紫禁城更不坏的结果。
时至今日,国内也有一些人按照这种逻辑来评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行为,显得非常冷静、理性,不带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人认为,近代史教给中国人的一个道理就是,“贸易进不来,子弹就会进来”,所以我们必须热情拥抱“自由贸易”。然而这是一种“荒谬的理性”,因为观点脱离了基本前提,丢失了大是大非的历史视野。无论清朝多么保守、落后和不遵守“文明世界”的规则——这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基本前提是英法是侵略者,正义还是邪恶由动机和角色决定。不得不承认,具有这种朴素善恶观同时又有条件发出声音的人,古今中外一直非常稀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欧洲,也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雨果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底线。
在一个丛林法则主导世界的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别人打上门来的时候,奢谈规则相当于“费厄泼赖”,就连今天的刑法也用正当防卫原则嗤之以鼻。人们可以不喜欢清朝,但必须理解它的处境。
北京城被攻陷,圆明园被烧毁,“天朝上国”被肆意侮辱,迷梦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