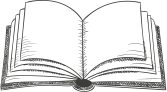
5.清朝的“改革开放”
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奕䜣,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第一笔,就是和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这位 29岁的王爷,是道光帝的一个文武全才的儿子,一开始是个主战派。受命留京之初,曾主张整顿各军,固守京城,认为非战非守不能争得议和。和议开始时,他也曾态度强硬,要求英法联军退兵、释放战俘,然后才会商续约、盖印画押。但清朝军队一路溃败,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弱国无外交”,最后只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
英法侵略者都知道,对清廷的过度逼迫,最终会激起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和对抗,所以达到目的之后,态度大变,以“讲情理代替武力恐吓”,对恭亲王表现得非常谦恭、尊敬,这让奕䜣大感意外。在与额尔金和葛罗的交往中,产生了英法夷人“渐觉驯顺”的印象,特别是当英法联军遵约从北京撤兵,更让奕䜣感到西方侵略者与中国古代的夷狄入侵者不同,他们不想占领中国领土,没有破坏祖宗家业和皇家统治权,只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因此他认为朝廷“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此后便放弃了主站立场,主张“以诚相待”“真心和好”。
和恭亲王一样有新的认识的高官大员甚多,如文祥、曾国藩、沈兆霖。户部尚书沈兆霖认为:“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
恭亲王前期主战,是对清朝国力缺乏真实了解,后期主张“以诚相待”,则很大程度上由于对侵略者的善良想象,两者都是错觉。但无论如何,他在往后领导清朝外交中的总体风格取向,就在此时奠定。
对于中国而言,《北京条约》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捩点,意义极为重大。宫崎市定简单评述说:“《南京条约》时中国只是开放了港口,这回却不得不打开国门了。中国天子接见外国公使,不得不以对等礼仪交际,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最不喜欢《北京条约》的一点,就是外国可以派驻公使常驻首都。清朝政府不得不常态性地与外夷对等地打交道——这一点事实上根本性地终结了秦朝以来“天子”所具有的神圣光环。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埠通商的结果还能用朝贡体系来粉饰,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就不仅在中国百姓所能感知的形式意义上,而且在实际运转的制度结构上,都已经无法再维持天子原有的尊荣。
皇帝最不喜欢《北京条约》的一点,就是外国可以派驻公使常驻首都。清朝政府不得不常态性地与外夷对等地打交道——这一点事实上根本性地终结了秦朝以来“天子”所具有的神圣光环。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埠通商的结果还能用朝贡体系来粉饰,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就不仅在中国百姓所能感知的形式意义上,而且在实际运转的制度结构上,都已经无法再维持天子原有的尊荣。
使节驻京这一点,是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最强烈抵制的“开放”内容,按照皇家的逻辑,如果外国人不跪,那么中国人也会慢慢地不愿跪,而这显然不仅仅是颜面问题。
在过去,清朝政府的外交,就是处理朝贡事务,由鸿胪寺负责。鸿胪寺,在秦朝叫“典客”,汉朝改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改名“大鸿胪”,直到清朝,这个官署的任务都是“引导仪节”。“引导”包含一个假定,即这一切都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对内是流程的引导,而对外是规矩的传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交不再是实质的或表面的“朝贡”,而变成了西方民族国家所主张的对等接触,过去的一套全部作废。因此在 1861年 3月 11日,在军机处下建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领导者就是“成功”处理了《北京条约》缔结的恭亲王奕䜣,恭亲王断断续续地领导这个机构达 27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意味着清朝衰落已经名副其实,如何在接踵而来的列强进逼下维系生存成了主要的“朝政”。所以总理衙门事实上的角色就是以前的军机处,手握重权。总理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加上虽非隶属关系但通过总理衙门进行上下沟通的南洋通商大臣,证明了支应外部危机成为清朝生存之所系。
中国,在坚船利炮的游弋、轰击下,“改革开放”了。
与我们所熟知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在开放逻辑上截然相反,这是被迫开放。被迫开放意味着不情愿,甚至是恐惧。
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在今天仍然必须思考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为何如此不愿意,甚至害怕开放?
第一,先要明确什么是开放。
简而言之,在当时的情势下,开放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贸易,二是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又主要表现为欧洲国家的传教活动。
明确开放的意涵之后,就可以讨论中国不情愿甚至害怕开放的原因了。
从边沁主义
 的角度考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统治结构的上层不在意同时也不能从与外国的商业往来中获利。
的角度考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统治结构的上层不在意同时也不能从与外国的商业往来中获利。
不在意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商品没什么需求,那时的欧洲商品在中国比较好卖的是钟表、鼻烟,都是上层阶级的奢侈消费品,所以这种贸易扩展的空间本身就非常有限。
有限的贸易给上层政治结构带来的收益也是有限的。鸦片战争之前全国只有广州一个海关,隶属于朝廷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家的私人收入,这些收入主要用途就是购买西方的钟表,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的藏品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购入的,因此皇家对贸易的需求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不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对鸦片贸易征税,这种实质上占据输入商品货值最大比例的货物对公共财政和皇家私人收入都没有意义。
上层收益不大,不意味着整个政治结构无法从中获益。管辖着通商口岸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灰色地带获取巨额寻租收益。所以面对鸦片输入,中央和地方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这也是尽管属于非法行为,但鸦片输入仍然在 18世纪上半期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马嘎尔尼进京之前,英国内政大臣亨利·登达斯就提醒说:“你必须小心他们可能会向你要求一项约定,即如同欧洲法律已经禁止的一样,将鸦片贸易排除于中国领土之外。如果这个议题被提出来讨论,则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毫无疑问在我们印度生产的鸦片实际上销往中国的不在少数,但如果必须提出确凿的正式命令,或是拟以商业协议的条文要求我们不能把这些药运往中国,你必须接受,而不要因为护卫我们的自由而冒失去实际利益的风险。”
 由此可见,即便双方都认同鸦片贸易在中国不合法,但它仍然事实上进行着。这既是国家官吏自身腐败的结果,也有鸦片贸易的主动和持续腐蚀的推动。
由此可见,即便双方都认同鸦片贸易在中国不合法,但它仍然事实上进行着。这既是国家官吏自身腐败的结果,也有鸦片贸易的主动和持续腐蚀的推动。
第二,郡县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道德法则、文明教化、统治的方法论以及政治结构和相应的制度,都依赖于长时间里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形态。尽管商税(如市税、关税、山泽税等)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目和种类,但支持中国社会伦理和政治运转的基础一直是农业。与外国的通商会改变贸易所及地域的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从而破坏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力。而且清政府非常清楚,一旦贸易渗透到某一地区,就“尾大不掉”,“夷人”来了就不肯走,并且注定会得寸进尺地要求各种权利,削弱主权。
第三,开放带来的传教活动严重破坏支撑整个上层建筑的底层基础。
《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英国打了胜仗获得了利益,法国、美国随之而来,不需要亲自打败中国就可以仿照英国订立条约获取利益。中法《黄埔条约》就规定开放教禁,因为法国是当时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它认为自己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法国人只想开放天主教,但通过这一条约新教也获得了正式地位,而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就和新教的传入有关。
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天主教迅速在乡村蔓延,很多教案就由它而起,引发了很大的纠纷。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因宗教靠山而获得了很多特权,比如加入基督教的人常常挑战地方社群的传统规范,拒绝贡献向全村或全镇收取的庙宇和年节基金,不再参与传统活动的凑份子,但却仍要享受其好处,因而与未入教的群众产生激烈冲突,从而撕裂了中国底层社会;当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卷入与邻居的财产纠纷时,经常在向县官陈述案件时主张自己受到了宗教迫害,让简单的事实复杂化,甚至让法条失效;此外女子入教、男女共处一室进行宗教活动等,也冲撞着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原则。其中更为严重的冲突则是天主教禁止偶像崇拜,又把中国人的祭孔祭祖定义为偶像崇拜,这其实等于一铁锹挖向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从而动摇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合法性。
地方正统精英应对异教挑战的方式之一就是散布西方传教士耸人听闻的谣言,如绑架儿童、挖眼制药等, 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正是由此而生,天津教案直接导致前往调查的曾国藩仕途终结,并于 1872年在羞辱与沮丧中去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新教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教教士创办如《万国公报》这样的报纸,输入西方思想,打开信息渠道,对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有客观上的启蒙作用。不过对于清政府而言,启蒙却是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大致地说,以上便是清朝不情愿乃至惧怕开放的主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开放会让它像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一样地解体。妄自尊大、自我闭锁和腐朽堕落是传统归因,尽管也是重要原因,但却是主观的,也是表象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意味着开放已经成为事实,清政府已无法逃避,主动地自我调整在所难免,洋务自强运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
同样地,与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逻辑不一样,清朝的改革开放导向的客观结果不是自强,而是日益艰难的处境和渐趋崩溃的统治——所谓逻辑不同,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独立自主”。从事后的角度看,清朝统治的崩溃,本身是中国在新世界再度自强自立的历史必需,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扫清现代化障碍的社会革命奏响了前奏。
作为源头,这一事实又在社会上产生了另一个困惑,似乎列强的侵入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这种观念甚而愈演愈烈,在极端情况下发展为“侵略有功论”“殖民有利论”,乃至到了 21世纪,仍然有人主张中国想要继续进步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奇谈怪论见怪不怪,一言以蔽之就是,无知者无畏。
的确,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正是西方国家发动的殖民战争,但其真实目的在于控制、掠夺与倾销,以“边缘地带”的受损来支持“中心”的发展,而不是像表面所说的那样“传播文明”。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不符合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甚至与他们的利益根本相悖——事实就在眼前,这从今天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的道路迈向复兴便遭受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择手段的围堵便可以得到印证。
历史学家胡绳指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胡绳接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典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作者注)。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

因此,即便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借兵助剿”,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与侵略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朋友”关系,但后者的动机不在于帮助清朝发展,而是从农民战争中意识到,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它们想要的结果是既让清政府继续存在,有能力去镇压人民的反抗,又让清政府保持腐败、羸弱,只能屈服于外国压力。事实上,这正是洋务自强无法达到目的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其进程就会被打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殖民主义者当时的诉求全部实现,随后欧洲的法国和普鲁士爆发战争,中国得到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而太平天国运动已让清政府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 30余年,在思想上首先做出有影响力的贡献的是林则徐,只是在林则徐那里,“洋务”还称为“夷务”。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从林则徐处获得西方国家制度、社会、文化等资料的魏源后来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核心精神的概括,这一思想事实上也是林则徐的主张。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左宗棠奉林则徐为师,受到林则徐精神与学识的深刻影响。后来左宗棠力主出兵,平定新疆,很大程度上也与林则徐的新疆经历以及对俄国侵略的忧患意识有传承关系。
洋务运动在中央的领导者是奕䜣、文祥等满洲贵族大臣,而地方代表也是实际的执行者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族士大夫。曾、左、李都从与太平天国的长期战争中出头,张之洞则是清流出身,立场转变后获得政治资源,随后平步青云。
历史就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在长达 200年时间里,汉族士人受到清朝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歧视,但正是他们在风雨飘摇之际维护了清朝统治,并借此走进了政治舞台的核心。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由于其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唯武器论”的影响,所以顺序上是先强兵后富国。军事上积极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筹建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经济上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民用企业;文化上兴办新式学堂,向外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当时创办的工业企业,大致上按照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顺序出现:强军需要制造武器,因而兴办了军工企业;军工企业需要用到大量的煤炭,因而兴办了采矿业;矿业带来运输需求,因而兴建铁路提上日程;兴建铁路需要大量钢铁,所以又延伸到钢铁生产。
对洋务运动,不能简单以“失败”视之。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缺少了它,近代化的整个链条也就不成立。而且对待历史、对待前人,我们还是应当怀有必要的敬意,不能总以“不是坏就是蠢”的眼光来打量过去。
洋务运动强军事、兴实业,这些举措对于“强兵富国”而言是必由之路,但即便如此,仍然受到诸多非议与掣肘。朝廷中那些只善于动口的官员,动辄“奏请停办”。内阁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办造船厂,理由包括“靡费太重”、“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造出来也打不过别人等等;另一位大臣要求停办矿务,则以破坏风水、毁坏坟墓为由。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让实干的人疲于应付,不断重复着不改革将被历史潮流淘汰这类老生常谈,正是在这种言论交锋中,李鸿章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幸而朝中主政的恭亲王等也是改革派,对前线的实践者非常理解和支持。
尽管“形格势禁”,但洋务运动还是在工业近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重视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李鸿章分别在 1965年和 1871年参与筹建的江南制造局和招商局,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在新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江南制造局, 100多年后成为今天的江南造船厂,为共和国制造先进的海军舰艇,最具代表性的是国产新型航母。
当时由左宗棠主导成立的马尾船政局,在 1869年制造出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排水量是日本自造蒸汽机船“千代回”号的十倍,造船设备也堪与西洋媲美,远超日本同期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聘请洋师洋匠帮助造船,还强调自身要掌握技术, 1876年以后就逐渐改为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
军事建设也颇有成效。光绪十四年( 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根据《美国海军年鉴》的分析,当时北洋水师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这支海军,也代表着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过去的耻辱,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防能力太弱,尤其是没有自己的海军,外国军舰在沿海和内河如入无人之境。
北洋舰队似乎昭示着,中国扬眉吐气了。但历史证明,自强远比想象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