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彪尖刀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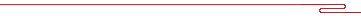
汀泗桥是由湘入鄂的第一道门户。
汀泗桥位于鄂南咸宁,始建于南宋,桥东群山叠嶂,桥西湖泊密布,素有天险之称,是北伐的必经之路。汀泗桥东面横贯的河流水深浪急,南北只有粤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行。桥北更是丘陵起伏,只有桥南猪姆冈高地,稍稍平坦,为入鄂必经之要道。
吴佩孚已派出4个旅守护该桥,试图阻止北伐军进入鄂境。如果北伐军被阻断于汀泗桥,等到吴佩孚的七万援军到达夹击,北伐军将被迫回师广东,北伐也将宣告失败。
汀泗桥之役是北伐最关键的一仗,也是吴佩孚北洋军生死所系。四军由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下3个团:缪培南第三十五团、黄琪翔第三十六团、叶挺独立团担当主攻任务。
汀泗桥一带,北洋军更是集中了三万人马。就连实力最强的洛阳军官学校六千名久经战事的军官也拉上去了。这些军官,被吴佩孚编成两个军官团,每团配备数十门火炮,六十余挺机枪,分别由少将刘维黄、上校张大庆担任正副团长。这可是自直系北洋军建军以来,少有的超级装备!督战委员会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的亲信张席珍全权指挥。
“这样的部署,再守不住一个汀泗桥,岂不成了古今笑谈?”吴佩孚信心十足。
四军指挥层观看地图,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粤汉铁路上汀泗桥以南的中伙铺车站,占领此处可以截断粤汉铁路,扼住溃敌退路。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受领任务的部队必须在30个小时之内强行军100多里,翻越3座高山和两条河流,在行军途中还可能与溃敌相遇或被南下的直系部队主力咬住。
“哪个部队愿意担任抢占中伙铺的任务?”
军事会议上,广东清远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一连问了三遍,手下师团长面呈苦色,无人作声。坐在陈可钰身旁的党代表廖乾吾知道,各部队连续几天作战已经十分疲劳,需要做一些休整,马上又去执行这么艰巨的先遣队任务,各师团长都怕自己的部下吃不消,再打起仗来冲不上去,万一失手责任重大,所以,大家都不肯冒这个险。
“希夷呀,你们独立团是不是再当一次先遣队呀?不过,困难是有的,但军部相信你们能够征服困难,完成任务。”廖乾吾看着叶挺发了话。
张发奎也希望叶挺先去挑些能讲鄂语的士兵,组成一个尖刀排。
“上级叫我们去,我们就去,”性情刚烈的叶挺豁地站起来,向“老袍泽”们一拱手,“明天我们在中伙铺恭候诸位。”
当天,叶挺从团里还未减员的后卫营里,挑选出了能讲鄂语的两湖籍官兵组成一个尖刀排,由一周前刚出任后卫营第七连排长的林彪率领出征。
林彪,原名育容、育荣,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五卅”反帝运动中,林彪以一腔热血投身学生运动,并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后来,又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父母当时为他谋到一份教师职务,林彪说服父母,弃教从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1925年冬,林彪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从此,操练场上多了一个浓眉细眼、操着浓重湖北口音的军人。
就是这个寡言多思、常用心计和周士第、刘志丹比武的学生,赢得了蒋介石的欣赏与喜爱。
要斩断粤汉铁路,就要和火车赛跑!
对于黄埔军校生来说,这不算太难的事。在学校,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学生都要围绕长洲岛公路跑一周,全程大约15公里,尤其来自两广和湖南的战士以善于爬山见长,经过反复拉练,练就了一双飞毛腿。
茫茫夜色里,尖刀排连夜急行军,灰色的军服,跃动的人影,行进的队列像一条灰色的巨龙,蜿蜒曲折地在黑漆漆的山野上蠕动。几十人的步伐,由近及远汇成了犹如无数条小溪低语似的沙沙声。
尖刀排出通城,过崇阳,于8月25日拂晓到达汀泗桥南的中伙铺火车站,并联系到了铁路工人阻击队。铁路工人告知林彪,有一列兵车正从蒲圻开往汀泗桥,马上就到中伙铺。林彪赶紧命尖刀排战士沿火车站散开,并让部分士兵化装成铁路工人,与工人阻击队组成一个拆轨的交通破坏队,分组用铁锄、锤子、扳手拆开铁路钢轨,使敌人军车、铁甲车无法开动。
天蒙蒙放亮,一列满载由岳阳北上的敌军列车向中伙铺车站方向隆隆开进。刚驶入中伙铺火车站,即被尖刀排截住。尖刀排猛烈开火,突突地撂倒一大片。
火车站一片混乱,不断有敌军跳窗逃命。尖刀排投掷出一颗颗手榴弹,烟幕中,敌军被炸得身首异处。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吴军第二团团长李精明、营长邹化被迫投降。叶挺独立团一举切断了湘敌北撤的通道。
随后赶到的北伐军占领了黄石桥、大路寥、北路学校一带的敌军据点,敌阵渐乱,纷纷溃退。
扫清了进攻的屏障,独立团待命进攻汀泗桥。
汀泗桥最高的一座山名叫塔垴山,这是关系到双方成败关键的制高点。
1926年8月26日10时30分,国民革命军总部下达命令:缪培南三十五团沿铁路两侧向汀泗桥正面进攻塔垴山,黄琪翔三十六团从聂家港进入汀泗桥东张兴国一带,与北伐军第十师从右翼包围攻击。叶挺独立团作为预备队。
三十五团的前卫营向汀泗桥发起进攻,遇到敌人顽抗阻击,炮火非常猛烈,吴军部队在塔垴山上用十几挺重机枪向桥南居高向下扫射,三十五团连续三次冲锋均被击退,前卫营伤亡过半。三十五团必须仰攻,又受阻于急流,死伤惨重,却没有丝毫进展,又遇江水暴涨,第四军只有望桥兴叹。
黄琪翔三十六团的进攻也没有进展。
黄琪翔派出一组熟悉水性的士兵,到汀泗河秘密侦察河水深度,侦察敌人阵地配备情况,待后续增援部队到来。
枪声稀疏下来。北洋军已将船只掳过北岸,并在汀泗河上游浅水处及河心插上了密密匝匝的尖刀和竹签,黄琪翔派出的突击组用大刀扫除了尖刀和竹签,三十六团从浅水处过河,向塔垴山冲锋,敌军居高临下,用机关枪疯狂向北伐军扫射。红浪翻滚,鲜血四溢,短暂的几秒钟,战士就倒下五六个。
凌晨4时,援军第十师从峡山冲启程,快速抵达汀泗桥骆家塆,占领了后山阵地,炮兵营放列,向塔垴山轰击。第十师和黄琪翔三十六团的勇士趁夜色乘十几只小木筏顺汀泗河而下,在接近对岸时突然遭到吴军机枪扫射,小木筏纷纷被击沉,一排长和战士跌落湍急的河水,顷刻间被洪流吞噬。
进攻受阻,张发奎部伤亡惨重。
天快亮时,陈可钰、张发奎、廖乾吾等急急赶到汀泗桥南前线查看地形,只见塔垴山地势险要,河水一片汪洋,浩如烟海,桥上布满铁丝网和炮楼,桥四周也布满机枪和火炮,易守难攻。要从三万守军手中夺下汀泗桥,拿下塔垴山,实在不易。陈可钰心中不免焦急万分。
关键时刻,黄琪翔三十六团立了大功。黄琪翔,广东梅县人,长得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是一位著名的美男子。他不光长得漂亮,而且骁勇善战,是员虎将。他早在激战前就已经派人侦察地形,建议当晚开赴上游水浅处,强渡河流,直取汀泗桥的北岸,抄敌人的后路,大部队则从桥南猛攻敌军,腹背夹击,必可一举歼敌。叶挺也再次献计,让自己的尖刀排包抄到敌人后方进行突袭。
陈可钰、张发奎同意了黄琪翔、叶挺的作战方案,但关键是缺少渡河的船只。
黄琪翔微微一笑,原来,他已经从当地渔民那里买下了几十只渔船,足够一次性将全团渡过河去。
总攻击开始了。
一开始依然不顺利。北洋军在铁路桥上架设了铁丝网,又集中火力把大桥封锁起来,吴军团长刘维黄组成敢死队,用强大的炮火作掩护,往铁路桥南冲杀过来,北伐军抵挡不住,一些学生兵怯战,纷纷往后退守。驻在魏家塘的四军主力亦受到严重威胁。四军代理军长陈可钰急调战斗力强悍的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
“即刻驰援军部”,独立团二营营长许继慎接到叶挺命令后,振臂一呼:“跟我上!”二营战士们绕过吴军往北冲锋,向敌军后面发起进攻。猛烈的枪声使正往南冲的吴军大刀队阵脚大乱,一名凶悍的大刀队员举着大砍刀向许继慎挥来,许继慎往左一闪避过,反手用力一刀,大刀从敌军前心穿出,鲜血如泉,如坠落的石头般向水中跌落!又一名大刀队员哇哇叫着冲上来,许继慎眼中闪过团团怒火,匕首一闪,已经刺透敌军心口,带出一道血泉。
夜里,叶挺从团里选调了5名政治觉悟高、很能打仗的共产党员补充到尖刀排,再次由鬼点子多的林彪率队出发。
更深夜静,尖刀排绕到塔垴山北坡,在村子里找到了几个农民,询问地形。一听是给兵带路,农民怕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林彪心急如焚,几经周折,才终于找到当地一个农人做向导,并许诺事后给银圆作为酬谢。
午夜时分,尖刀排随向导穿过丝茅窝,往西南方向进山。向导带着大家沿着米埠垅上坡后,指着前面的山间小路说:“笔直上去是古塘角,那就是塔垴山的后方,你们自己上去吧。”
林彪边用袖子擦汗边对他说:“我们也不要你上去了,再上去就危险了,子弹不长眼睛。给你两块银圆,算作酬劳。再给你一张条子,证明你带路有功,如果我们胜利了,将来北伐军给你记功。”
尖刀排绕道爬山越岭走了40里山路,冲向塔垴山北后山窝。塔垴山守敌除了少数值班的,大部分还在睡觉,尖刀排悄悄摸至营房,用刺刀刺杀各碉楼守军,然后与潜伏在中部阵地上的黄琪翔三十六团、缪培南三十五团策应,一路横扫过去。本以为据险无忧的北洋军正在酣睡之中,忽然听到喊杀连天,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只顾得夺路而逃。
此时,担任主攻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十师二十九团也来到上游,向塔垴山方向涉水冲锋,北洋军居高临下疯狂扫射,北伐军死伤多人,继而在北桥头和敌军展开肉搏,双方死伤过半。三十六团的勇士们透着无尽杀气,如疯魔般向北洋军阵地猛冲,纷纷加入肉搏中,手臂挥动,血刃划破虚空,甚为惨烈。
“南兵疯了!南兵疯了!”
北洋军吓傻了,全线动摇,溃退到铁路桥北,纷纷逃入河中逃命。
北伐军所有部队全部投入进攻,三十团、二十九团吼叫着冲向塔垴山。双方激战至次日凌晨,塔垴山主阵地和北面的米埠垅一带被北伐军占领。残敌跑上铁路,向北面的咸宁城溃逃。四军炮营立即开炮拦击,巨大的爆炸声中,吴军的护桥工事被彻底摧毁,紧接着,缪培南的机枪连集中扫射扼守桥北的敌人,敌人被迫向东进入铁路。街上淹水一尺多深,被打败的北兵用装煤油的大铁桶垫在水中、上面铺着木板,一边踩着木板向后撤,一边扳动扳机,胡乱地往背后放枪,往咸宁方向溃退。黄琪翔与叶挺独立团南北夹击,终于全歼敌军,在8月27日凌晨夺下了汀泗桥,占领了塔垴山。
汀泗桥战役北伐军获得大胜。
“北伐中汀泗桥立下首功的当推黄琪翔团。”张发奎曾如此评价。尽管张发奎公开直言并不喜欢黄琪翔,但有一说一也是张发奎的个性。
黄琪翔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民主党派之中的所谓“大右派”。
当然右派身份属于错划,1980年黄琪翔得到了平反昭雪。
北伐军势如破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凭险固守,待机反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