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贺胜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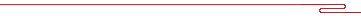
鄂南第二门户贺胜桥,本是一个小镇,但地势起伏不平,漫山遍野的榕树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其西南有黄塘岗,东北有梁子湖,河流纵横交错,低洼处早已被水淹成一片汪洋,唯有一条铁路可以通行。
从贺胜桥北至武昌只有50公里,这样,贺胜桥就成了防守武昌外围的唯一关隘了。
8月的贺胜桥,炎热如炽,泼一盆水在地上,咝咝一阵细响,腾起一缕白烟,霎时间地面上滴水不见。虽已入秋,但秋老虎正猛,依然烙得脚板像盐撒在伤口,辣蜇得生痛。无风闷热的火炉武汉,人稍一动弹就汗淋如雨,令人烦躁。
一连几日,吴佩孚在距贺胜桥不远的大帅专列火车里宛如一只庞大的困兽,来回踱步。
吴佩孚原本坐镇长辛店,准备大举征讨叛变南下的冯玉祥队伍,他认为冯玉祥就是一条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倒戈专业户,墙头草,忽儿左忽儿右,所以对冯玉祥恨之入骨,没有把太多精力放在北伐军身上。谁知自北伐军四军入湘以来,占安攸,破醴陵,夺平江,刚刚又端掉他的汀泗桥,摧枯拉朽,连战皆捷,势不可挡。这个时候,吴大帅才真正意识到北伐军的强大,他决定亲临贺胜桥排兵布阵,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三个月内,我吴佩孚不消灭南兵叛逆,誓不为人!”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原乃一介书生,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在直系老军阀曹锟的培植与宠信下,在各路军阀混战中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长、旅长、师长,不到几年就拥兵几十万,封为威孚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为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也是北洋军阀中最善战的骁将。
吴佩孚吸取平江和汀泗桥惨败的教训,率领鄂督陈嘉谟、总司令刘玉春、张占鳌、娄云鹤残部到贺胜桥,又集中嫡系两万多兵力,在桃林铺、印斗山和贺胜桥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还在可以监控贺胜桥的每个丘陵山头,都修了坚固的环形碉堡,配以火炮、重机枪,既能威慑前方又能兼顾左右,并且在北伐军任何能够通过的地方都设置了障碍物,埋设了地雷,还将主要阵地设于桥前杨林墚等处,盯紧后山尾巴,以防北伐军的尖刀排再度“插翅”飞到防线后面突袭。
1926年8月29日,炎热的夜空中,一列装甲列车徐徐由蒲圻驶抵咸宁,几个戎装男子簇拥着身披黑斗篷的蒋介石,匆匆进入一间临时战地指挥部。
李宗仁、陈可钰、张发奎、唐生智、白宗禧、黄琪翔、缪培南等将领早已在里面恭候。
会上,蒋介石和加伦将军经过反复商讨,制订了作战计划:第七军李宗仁部出咸宁东,进攻铁路以东之敌,从侧翼为正面进攻的第四军提供强大火力支援,其中,夏威指挥的第一队向徐家铺前进,准备占领鄂州;胡宗铎指挥的第二队向贺胜桥、王本立及以东地区之敌进攻,为整个部队打开通路;第四军李济深部沿铁路线及以西地区前进,正面攻击贺胜桥之敌,随后进攻武昌;第八军唐生智之一部及第一军之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第四军沿铁路推进。
次日早晨,李宗仁七军由咸宁向第一道防线横沟桥前进,遭吴军警戒部队猛烈火力射击,前进受阻。北伐军即转向吴军主要阵地进攻,守军依托碉楼顽强抗击,以优势兵力向北伐军阵地反扑。一时间,两军阵地炮火连天,官兵血肉横飞。关键时刻,唐生智第八军直捣敌阵,第四、七两军从左右两侧夹击敌军,将铁路沿线敌军阵地突破。吴佩孚见势不妙,急令卫队临阵督战,十几门大炮一起射击,依然挡不住北伐军兵锋。吴军退守,利用杨林以北的丛林和湖水,倾其全部兵力死守贺胜桥。第四军很快冲到敌军前沿阵地前。
贺胜桥的地形有利于北伐军,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视线十分不利于北洋军。诚然北伐军的行动难以掌握,而北洋军守兵的移动也不易察觉,这等于大家都看不清对方。只能盲打!
一时间,贺胜桥前各种枪炮齐鸣,震耳欲聋。
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担任主攻。
七军夏威部一马当先,攻破敌军第一道阵地后,上午9时向第二道防线进攻。守敌见北伐军凶猛冲来,慌忙跑人,跳水逃跑者数以千计。
吴佩孚以治军严明、训练有素而闻名,征战数十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勇猛的敌人,看到自己的部队节节败退,急令卫队临阵督战,令机枪手“向退却者扫射”。
可是依然阻止不了四散奔逃的官兵,吴佩孚羞愤至极,先后手刃旅、团长十余人,悬其头于电线杆上示众,以惩戒后退之官兵。他还令陈嘉谟、刘玉春率大刀队分赴几路作战。
刘玉春的大刀队会耍六合刀、追魂剑,每名士兵都配备一把大刀,这刀与一般的单刀不同,是由山西的镔铁打成,每把重7斤,全长7尺,刀面最宽处有4寸,刀沉力大,舞起来虎虎生风,很有杀伤力。大刀队员个个身强力壮,会使暗器,功夫过硬。
有大刀队助威,溃退残兵顿时有了斗志,拼死上前反击。当面的张发奎十二师,士兵们大多是手动上膛的枪支,火力羸弱,很难阻止吴军的靠近,于是大呼一声,冒着弹雨冲入敌阵,抵近肉搏,吴军的精锐大刀队也在督战队威逼下气势汹汹地杀来。
北伐史上最猛烈的进攻和最顽强的抵抗开始了。
在督战队咚咚战鼓声中,吴军的大刀队极为顽强凶暴。无数大刀翻着跟斗,冲北伐军官兵横飞而去,可怜一些北伐军不及招架,就被连劈带砸,血肉横飞,侥幸躲过的官兵,也被大刀队蜂拥围上,剁成肉泥,很多官兵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跑,只恨腿短。突然,一声暴喝响起,独立团新上任的二营营长卢德铭握紧短匕首,领着士兵冲在前面,卢德铭的勇敢激发了北伐军的血性,三十五团许多官兵从他身旁一跃而出,吼叫着向吴军冲去。
吴佩孚的北洋军大多是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临危不乱,拼死抗击。一吴兵如同疯了一般,大吼一声,抡起带血的大刀,就朝卢德铭刺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卢德铭一拳击中吴兵的眼,趁着对方天旋地转,一刺刀捅进了他的心脏。刀光剑影中,一只只血淋淋的断手断脚掉在地上,鲜血将土地都渐渐染红。独立团和三十五团拼死肉搏,咬牙死撑,死伤过半,终于,吴军抵挡不住了,防线出现了崩溃。
吴军退潮般向后逃跑,迎面泼来督战队的弹雨,顿时积尸累累,血流成河。一溃逃的班长见督战队无情射杀自己人,怒火中烧:“弟兄们,当官的逼我们送死,断了自己的后路,横竖是个死,不如像刘维黄团长那样,投降北伐军,保住脑袋,将来还有一碗饭吃啊!和他们拼了。”
他端起一挺机枪,对着督战队一顿扫射,逃跑的士兵退无可退,也都掉转枪口向督战队开火。
突突突……没几下,督战队一片片倒下。敌军内部互相厮杀,乱作一团。
独立团和三十五团乘乱夺取贺胜桥。吴军将领仓皇驱车逃跑,车过处,败兵攀缘欲上,卫士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而坠,惨叫呼号,实不忍闻。
下午3时30分,吴军再度向北伐军阵地发起猛烈反击,吴佩孚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拔掉北伐军第四军、七军这两颗钉子,第四军、七军凌厉还击,守军损失严重。炮声停止了,怒吼声隐隐传来,吴佩孚突然发现中央阵地上的守军正在向阵地后面退去,他以为北伐军开始撤退,高兴起来,即刻传令,命预备队驰援,又令各阵地严阵以待,并整夜施以枪声,以震慑北伐军,为部队壮胆。
是日午夜时分,如漆的夜空,又下起了大雾,滑腻腻、黏稠稠地,就像天地间注满了浓稠的墨汁。
次日凌晨3时,尖厉的冲锋号声划开了雾的衣裳和夜的胸膛,汗涔涔埋伏在贺胜桥百米处的第七军奋力向敌军发起冲锋,吴军也施以雷霆万钧之还击,顿时,急风暴雨的枪弹声犹如海潮扑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似山崩地裂。
指挥部里,黯淡的油灯下,张发奎、叶挺、缪培南、李宗仁、聂荣臻等紧张地分析敌情,认为敌我距离太近,相峙过久,于我不利。敌彻夜放盲枪,表明他们也看不清我方,应集中兵力,破其一点,而后实施总攻击。
拂晓,十二师向铁路沿线左右两侧之敌进击。全部预备队对吴军阵地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顿时,战场上尘土蔽日,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一马当先,如同旋风一般领兵向吴军阵地冲去,狭小的战场上人头挤着人头,北伐军战场态势出现好转,已经分片包围敌人。
一面青天白日旗跃出山峦,“活捉吴佩孚!”的喊声传来,吴佩孚听到杀声越来越近,出来观看。吴佩孚本是个迷信之人,一看北伐军的一颗炮弹正中“吴”字帅旗,觉得是一个凶兆,在北伐军还未到达之前,马上命令撤退。吴佩孚原先依仗重兵把守天险,加之“贺胜”两字吉兆,以为稳操胜券,不想遭到如此惨败。至此,北洋军在贺胜桥铁路线布设的试图阻挡北伐军的三道连环防线全部崩溃,吴佩孚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进武昌城。
战后论功,张发奎这样认为:“在我的心目中,贺胜桥战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该战役被说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吴佩孚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事。他想死守贺胜桥,遂用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的脑袋来阻止退却。事实上,此时吴佩孚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贺胜桥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此役毙敌1000余,俘敌军官159名、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机枪30挺、步枪2000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497人。贺胜桥胜利的首功应记给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