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喋血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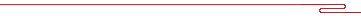
汀泗桥与贺胜桥两场大血战对决,都以常胜将军吴佩孚的失败而告终,折了他一世威名的正是第四军和第七军。从此,以广东军人为主组建的第四军得名“铁军”,声威一直流传到今天,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二七师的前身正是叶挺独立团,全师官兵的臂章上就印着大大的两个字“铁军”。
立下卓越功勋的新桂系第七军,也得到一个外号“钢军”。
逃回武昌的吴佩孚,悲愤交加,又羞又急,丢人啊。
“张发奎、李宗仁韬略无前,陈铭枢指挥若定,蒋光鼐谋定而战,叶挺勇冠三军。我军若是武昌一役再败,吴氏此生再无颜见列祖列宗了。”
吴佩孚不禁连连叹息。打仗,可不就是一攻一守吗,吴佩孚强打精神,连夜从指挥部走出来,打着手电筒检查防御工事。他跟士兵们趴在战壕里,盯着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送过来,再看看桥上碉堡,也都由钢板和三角铁筑成,坚固无比。从缝隙里伸出去的枪口,是德国、捷克的新式武器,火力够猛。为了既便于指挥,又不被对方的枪弹伤着,吴佩孚令人用厚钢板搭了很多个临时隐蔽所。
第二天凌晨,地雷运来,回到指挥所的吴佩孚喜不自胜,远眺南岸武昌的高墙深沟,心潮澎湃,成败在此一举。
北伐军第四军十师受领先锋印,日夜兼程,沿粤汉铁路向溃退之敌追击,越过纸坊,一直追到武昌城郊,炮击炸毁了敌军郊外的全部工事。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大部队开始向武昌进发。
1926年9月3日,拂晓时分,长江、汉水无声无息地奔涌着,波光潋滟、一望无际的水面缭绕着浓郁的硝烟气息。城外仍在黑暗里,城头却灯火通明,城上城下亮如白昼。
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
高大的城墙逶迤几十里,阻挡了北伐军前进的步伐!
北伐军万名官兵扛着向民间征集的数百架木梯直扑向城墙,第四军十师、第一军二师及第七军一部高举军旗呐喊着冲来。武昌城墙高耸,坚实无比,城外又有护城壕沟,部队接近城墙用梯攀登,却够不到城墙上端。城墙上的吴兵居高临下,滚木、礌石、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而下,北伐军伤亡惨重。
攻城总指挥李宗仁只好下令停止攻城,第一次攻城没有成功。
子时过了一大半,北伐军再次强攻,又遭遇顽强抵抗,伤亡更加惨重,第二次攻城失败。
次日,北伐军又发动了5次攻城战斗,仍被吴军强大的火力击退。
久攻不下,蒋介石心急如焚,当晚,他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命令李宗仁和第四军副军长兼副总指挥陈可钰率部再攻,“限于48小时以内攻下武昌”。态度严厉,没有丝毫商讨的余地。
战局更加胶着、悲壮而惨烈!
翌日,李宗仁和陈可钰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兵遣将,命令第四军全军及第七军胡宗铎部、第一军二师刘峙部配置9门大炮合编为攻城军。二师暂归第四军指挥,各师选400人,军官15人,组成10支奋勇队,皆以营长为队长带头冲锋。张发奎指定勇敢善战、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并着手准备竹梯。
奋勇队就是敢死队,只不过字面上文艺一点而已,这意味着谁参加奋勇队,谁就要把命舍掉。李宗仁釆取了抓阄儿打乱建制、编制组成敢死队的办法,也即抓阄儿决定生死。谁来帮他们抓“生死阄”呢?
如果没有人带头抓,这个办法行不通,难道用枪逼着跟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吗?这个办法很残忍,却也很管用,李宗仁、陈可钰、张发奎一时陷入矛盾中。
无人站出来,毕竟生命只有一次,长久的沉默里,共产党员、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以平淡而又坚定的语气说:“我看,我们团每个营都是一把尖刀,官兵勇猛,敢打硬仗,就不必打乱建制了。”
曹渊的壮举感染了四军、七军的所有官兵们。
一个小时以后,一营几个连、排长拿着几十封家书,交给了曹渊。
“战亦死,不战亦死,天下宁有不战而死、束手待缚之壮士哉?”
“我视死如归,立志已久,只恨一死未足以尽责。”
“请弹从口下!”
这些气吞山河的绝句,仿佛穿过山重水复的岁月,穿过发黄的历史,在耳边依然鸣响。
“好,都收下,都收下。”曹渊看着这些遗书,把溢出的泪水用力擦掉。当一脸稚气的曹渊把全营官兵写的家书交给团长时,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叶挺捧着这些“家书”,激动得泣不成声,泪如泉涌。
战事紧急,叶挺不敢怠慢,马上将第一营官兵的“家书”交给陈可钰和廖乾吾。捧读着一封封遗书,陈可钰和党代表廖乾吾强忍泪水。独立团留书攻城的壮举,立刻不胫而走,迅速在北伐各军和当地群众中传播。
4号拂晓,担任主攻任务的独立团第一营、第四、七军敢死队借着黯淡的星光,冒着敌军炮火潜近城脚。一营刚刚接近护城河,就被城头敌军发现,如蝗的步骑枪、机枪子弹嗖嗖地飞来,十几个士兵和两个排长胸膛中弹倒下了,热血直淌,几个腿上挂了花的敢死队员,也咬紧牙关,一个个忍痛爬着往前冲击。护城河水深没颈,再往前爬会溺水而亡,但他们宁可爬到护城河里赴死,也不肯留在原地求生。叶挺带领其他官兵在远处向城头猛烈射击,守城敌军在龟山、蛇山和楚望台等高地架设了多门山炮、野炮,加上长江中敌舰上的火炮,一齐向攻城的北伐军轰击,密集的炮弹冰雹般落在掩护攻城部队的阵地上,部队伤亡惨重。
尽管失去了后续部队的策应,曹渊仍手持云梯到达了城墙脚下。呼啦啦,十几架高达两丈的云梯矗立在墙头上,官兵攀缘而上,个个争先,一人倒下,众人冲上。吴军马上集中火力反击,爬在长梯上的敢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
曹渊眼睁睁看着战友纷纷倒下,泪如泉涌,悲愤中掏出钢笔迅速给叶挺写了简短的一封信:“现状至危,但革命军有进无退。我誓必率我可爱同志达成竖战旗于城上之任务!”
曹渊脱下帽子,把信交给身边的勤务兵,纵身跃上云梯。一排子弹射来,曹渊身中数枪,仍拼命双手扒住城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插上青天白日旗,高喊一声“革命军万岁”。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武昌城头,曹渊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张发奎指挥部电话铃骤响。夹着嘈杂的枪炮声,话筒那端传来叶挺颤抖之音:“师长,曹渊牺牲了!”
张发奎心中一颤,含泪道:“叶团长,代我向一营问好,告诉他们,曹营长精神不死。我们北伐军是支铁军,是打不烂打不垮的!”
一营敢死队勇士冒死攻城,一排子弹射来,敢死队无所畏惧,奋勇攀上城墙,宛如猛虎出笼,与守军展开了肉搏,“咔嚓”一声,一位班长右手被切掉,鲜血四溅。
“别救我,让我死!让我死!”一位勇士抱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痛得撕心裂肺的班长,号啕大哭起来。猛烈的子弾射来,两人倒在血泊中。
一营敢死队全部牺牲。北伐军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再次被迫退了下来。
城墙下满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熊熊火焰冲淡了许多的血腥气,第四军和第七军敢死队死伤大半,仍未能攻下城墙。
5日,钢七军再次攻城,敢死队队长大吼一声,纵身跃上城墙,搬开沙袋,三四十人拉住缰绳,吱嘎吱嘎将千斤闸一点点拉起来,突突突!猛烈的机枪火力从各个枪眼口喷射,第七军敢死队勇士全部牺牲。
情急之下,李宗仁对蒋介石的蛮干颇为不满:“那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呵!那么年轻,不能这样强攻了,乱弹琴。”
李宗仁决定挖开城墙地基,埋设炸药,炸掉城门。
叶挺本是学工程的,由他指挥爆破。他在通湘门附近改装了两辆吴佩孚弃置的载货车厢,四周围上钢板,两侧钻了枪眼,每辆铁甲车装载数十名独立团官兵,夜间用一节火车头推动这两节车厢向通湘门进发。一批士兵跳下铁甲车挖掘炸药坑,其余人留在铁甲车厢上用机枪火力掩护。
刘玉春不会束手待毙,当日即组织了一支600余人的精锐敢死队开路,阻击北伐军靠近蛇山炮台,又命三千人冲出通湘门,阻止叶挺独立团挖掘地道,并夺取了城外仓库的存粮。
埋设炸药行动失败。
一时间,北伐军陷入停顿和困境!
一天傍晚,天边仍有淡淡的血色余晖,城里传来稠密的枪声。心情沉重的蒋介石约李宗仁一道赴城郭视察,商量对策。李宗仁谈起汉阳地形和敌军守兵,谈起守城总司令刘玉春的部下第三师师长吴俊卿,蒋介石眼睛一亮,因为吴俊卿是他的旧交,他想到了派人策反吴俊卿,里应外合拿下武昌城的办法。
两天后,吴俊卿私下派他的参谋长混在出城的饥民队伍里,单独与第四军接洽,表示了投诚之意,并秘密商定择日打开第三师管辖的保安、中和、通湘三座城门,接应第四军进城。
1926年9月6日,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渡过汉水,夏斗寅攻下了汉阳,翌日何键登陆汉口,切断了长江南岸武昌敌军的粮食供应线,并向汉阳龟山炮台发起猛攻,付出了极大代价,占领了龟山炮台。北洋军防守龟山炮台的刘佐龙躲到文华书院,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蒋介石下令优待,刘佐龙声明加入革命军,蒋介石即委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随即指挥龟山炮兵,炮击吴佩孚在汉口的司令部。
9月10日晌午时分,汉口查家墩吴军总部树林中一间隐蔽的院子里,吴佩孚同幕僚们席地而坐,谈论前方战况,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而才搞清楚是刘佐龙师倒戈。
吴佩孚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逃离战场。刘玉春拒绝投降,紧闭城门死拼。
10月1日,吴俊卿第三师打开通湘门,叶挺独立团与第十师、第十二师立刻攻进武昌城,独立团官兵如脱弦利箭,扑向位于江边的蛇山炮台,因为武昌争夺战中,蛇山是一个要点,蛇山上的炮台可以俯瞰城内每一个角落,可以支援吴军每一处作战。
独立团攻到蛇山炮台之下,敌守军疯狂阻击。
“重机枪连全部瞄准敌炮台,狠狠地打!”叶挺大声怒吼,额头上暴跳的青筋和冒火的目光似一头发怒的雄狮。
“为曹渊烈士报仇。”
霎时间,蛇山上的敌炮台被交织的电光罩得密密实实,像一团烈火在燃烧,在焚毁。
吴佩孚也组织了精锐的敢死队反击,在通湘门向独立团发起突袭,夺去了独立团掩护工兵发掘坑道的铁甲车,并占领了通湘门车站及梅家山高地。叶挺再度暗遣两立奇功的林彪率其尖刀排,潜伏到敌军眼皮底下。林彪以3人为一组,亮刀出鞘,分散截杀,并命战士吹响冲锋号,大声呐喊,吴军敢死队听到冲锋号,以为陷入北伐军大部队重围,赶紧扔下到手的铁甲车,撒腿就跑。独立团尾随掩杀,经一日鏖战,敌军大部被歼,独立团攻占了蛇山敌炮台。
武昌城内的守敌见蛇山炮台被占领,失魂落魄,纷纷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10月10日,辛亥革命十五周年之际,名城武昌终克复!
武汉三镇全部被北伐军占领,吴佩乎被逐出两湖,溃逃洛阳,从此一蹶不振。
多年以后,张发奎在谈到北伐军克复武昌时说:“我的部属中在围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段话,反映了叶挺以及独立团,在一年后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占据的重要地位,预示着叶挺以及独立团在创建人民军队中的深刻影响!这是后话了。
战后论功行赏,叶挺升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李硕勋任政治部主任。独立团改番号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卢德铭任团参谋长,符克振任一营营长,部队驻扎在武昌南湖。
克复武汉的巨大胜利,震惊了全国!广州国民政府兴高采烈地迁都武汉。
之后,北伐军作了重大调整,中路军由蒋介石总司令亲自挂帅指挥,统率第三军、第六军、第七军为主力,与李宗仁率领的江左军以及程潜率领的江右军三管齐下,分进合击南京孙传芳;东路军由何应钦为总指挥,率第一军由粤入闽,讨伐驻扎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第四方面军;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第四军、第八军,自孝感沿京汉铁路进攻退到河南的吴佩孚。
蒋介石返回江西指挥战事,命兼任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代行指挥权。
北伐军又开始征战新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