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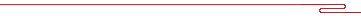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一切都在动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
北伐军节节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与杨开慧先后于11月上中旬离开广州。毛泽东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杨开慧和母亲则带着孩子返回湖南,住在长沙望麓园。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高潮,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有些地方随意杀人、公审枪毙。一时间天翻地覆。
其中,湖南农运规模最大,斗争最坚决,对北伐军支持力度也是最大的。
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到湖南,成为农运骨干。
到1927年1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猛增到203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两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湖南全省农民中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在农协领导下,农民对土豪劣绅、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斗争,并涉及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工作。
“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
毛泽东很兴奋。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北伐这个节骨眼上搞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
陈独秀对此时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深刻的担忧和恐惧,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会议上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时的考虑也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多年以后,当年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
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过火”了。
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毛泽东从汉口到了长沙,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的农民运动。他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被陈独秀派往武汉作指导工作,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则被分配到第四军政治部担任书记,也来到了武汉。
恰在此时,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加速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也使得陈独秀对毛泽东领导的农运反感加剧。
1927年1月3日,武汉大批工人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罢工示威,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聚集的工人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进入租界。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就将水兵撤回军舰。
当天上午,宋庆龄紧急召集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应对措施。她说:“我们应该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收回租界。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
外交部长陈友仁说:“我同意庆龄收回租界的意见,只是武汉聚集着约五十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一心想着北伐,说:“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宋庆龄却坚持己见,用流利的英语敦促陈友仁说:“陈部长,要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看作是您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陈友仁长得瘦小、皮肤黝黑、戴眼镜、留短髭、个性活泼机智。这位曾在伦敦上学的律师,是个很奇特的人。他是爱国的中国人、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却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有中国和非洲血统;当了短时间的律师后,他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更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他痛恨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和压迫,但又不喜农工运动。
正是因为宋庆龄的执着,感染了陈友仁,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并进行谈判。中方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承认并保持英国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中国领土。
但是鲍罗廷、陈独秀都害怕第二阶段的北伐遭农工运动破坏受阻。鲍罗廷的建议是,缩减工农运动,党的重心应在北伐上。他认为是搞农运的毛泽东先带坏了头,影响了国际关系,毛泽东在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鲍罗廷建议限制农民、工人行动,陈独秀提出支持北伐,限制过火的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1927年初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镇,其内部却正在悄悄分崩离析。同年2月12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昌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毛泽东率全家——开慧的母亲和岸英、岸青——由长沙迁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先驱者彭湃居住。毛泽东还有一间书房。
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杨开慧不顾身体虚弱,夜以继日地对丈夫的农运调查材料仔细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耗费了杨开慧多少个不眠之夜,又凝聚着她多少的心血。
在这份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会所做的“十四件大事”:组织农民入会,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直接枪毙),禁止牌、赌、毒——同时还禁止花鼓,禁轿子,禁酒,禁糖,限制养猪(猪吃苞米),限制鸡鸭,禁杀牛,禁酒席,禁游民,禁鞭炮……
对于“农会”的行径,毛泽东的评价一律是:好得很。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说:“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还在报告中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1927年上半年,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武汉的毛泽东和彭湃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并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也策应发动了拥有二百多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
与此同时,粤、赣等省区也呼应两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成立了农民协会。此时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多达八百余万人。面对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喜上眉梢。
3月5日,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将哥哥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主要文章就是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毛泽民是中共早期出版发行史上富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底,他从广州农民讲习所结业后,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负责管理党开办的长江书店和地下印刷厂。毛泽民化名杨杰,人们称他“杨老板”,长江书店有自己的印刷厂,专印党的刊物和马列书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度的憎恨和恐慌,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陈友仁等人也颇有微词,对暴力流血农运也很反感。而农运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得到完全赞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等人也认为农运过火。
但是,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支持农运,并勇敢地站出来为此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称赞毛泽东同彭湃一样是“农民运动的王”。
此时,毛泽东却明显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总书记陈独秀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彭述之两人不准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只勉强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和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却同时发表在湖南的刊物《战士》上。
陈独秀严肃地、甚至恼火地斥责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问题:“国民党中许多重要人物,尤其是北伐军中的各高级将领,如果按照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排序,其家庭与财产都应划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土豪劣绅’,按照湖南农会的说话,是要‘入另册’的。当前的农民运动已经严重冲击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这能不影响到当前国共合作的局面吗?润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重,为了保护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我们必须应该马上刹住,以保证北伐不至因此受到干扰!”
毛泽东没有回答,默默地思考着。
“润之,国共合作走到今天,其间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殊为不易。我们要设法维持这个局面不使其破裂,促成国民党早日完成民国革命阶段之任务,才能由我们共产党人合法接替其工作,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实现人类大同!”
毛泽东不高兴地问道:“那您的观点是什么?”
“‘过火’是事实。但过火到什么程度?怎么样制止‘过火’,我还没有好的思路。”
“农民运动到底要由谁来领导?”毛泽东火了。
“当然要由国民党出面领导。这些都是原则问题。”陈独秀很不高兴毛泽东跟他顶撞,“已经反复说过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限制各地过火的农民运动、更有组织化地开展工人运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减租减息,要纳入国民政府各地党部的统一领导,不要继续扩大和泛滥,更要防止乡下农民成为流氓、暴徒!”
“当务之急。那就是全力在国民党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同志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陈总书记一口气说完,似乎不容毛泽东辩解。
而正是此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陈独秀的友谊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水火不相容。两人之间突然变得生疏起来,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个追风少年,曾经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的毛泽东与总书记之间的裂缝在渐次扩大。
毛泽东心里很不高兴。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后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那个曾亲切地轻拍他的肩膀,唤他“二十八画生”的总书记,在他心里渐行渐远。
正当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时,北伐军正在各个战场上迅猛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