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团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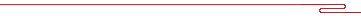
虽然廖案已终结,但因为廖案的“能见度”很低,尽管兴师动众侦查、审讯,且宣布全案告破,梁博等人被执行枪决,但案情依然扑朔迷离,有一些内幕至今尚未揭开。因此,国民党的右派并没有因此休牛归马,广东情势越发复杂多变。
这时,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让本不晴朗的广州天际迅速阴霾一片。
这个人就是留日生、将孙中山遗嘱提炼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国民党元老、思想家、理论家戴季陶,也是蒋介石的结义兄长,“国师”和“智囊”。孙中山死后,戴季陶慧眼识势地看到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危机重重,于是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叫嚣“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
戴季陶首先公开树起第一面反共大旗。可此旗一举便被扯下,因为有鲍罗廷在其间调和,汪精卫一如既往地袒左,汪精卫甚至批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此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尚能共进共退,国共合作还算愉快。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反共之火一旦被点燃,就不那么容易扑灭了。
本来孙中山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鲍罗廷等苏俄顾问的话当圣旨,就让国民党右派分子十分不满,他们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但出于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尊重和威望,不敢发难。孙中山一死,新的领导核心汪精卫的威信与能力都无法企及孙中山,根本无法镇住全党。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情绪愈来愈浓烈,声音也愈来愈高,公开跳出来反对,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治党能力也产生了质疑。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在神州大地开始兴起。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彭湃一起分批给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讲课、培训,这期间,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纷纷走上前台。
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底,因廖案逃至外国的国民党老右派胡汉民、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先后回到广州,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碰头密议,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10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召开了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的“西山会议”,出席“西山会议”的还有居正、叶楚伧、覃振、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邵元冲、石瑛、石青阳等13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反共议案,做出了决议: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理出去;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至上海。西山会议罗列了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西山会议虽然声势很大,可军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里,所以没有形成什么大气候。在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倒是西山会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颇有点像巫师的咒语,半年后汪精卫果真“出事”了。
当时正在广东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的消息后,愤怒地连骂一串“娘希匹”。这使他仍然维持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此时的北方,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各自为政,大小军阀战事不断。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作为军人的蒋介石意识到:军权至关重要,必须把国民革命军的最高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蒋介石最迫切做的事,便是“策动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一要职,堂堂正正地把蒋介石摆到了李济深、谭延闿、程潜等老前辈之上,蒋介石成了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长官。跃居权力中心的蒋介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他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支持下,制订了一套全面而翔实的北伐计划,还提出了1927年8月“克复武汉”的宏伟目标。
北伐在即,需要一位总司令,当初张静江力荐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然而任命书下来,总司令却成了总监,虽说都带“总”字,两者却有着性质上的区别,总司令有统领全军之义,总监则不是。这一任命,让原本相处得同声同气的汪精卫与蒋介石,迅速翻脸!
蒋介石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有些事不能找苏联顾问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便以为共产党要干掉他,或者汪精卫要抢他军权。
这期间,因廖案回避在外的国民党右派们重新被请回广州大本营,且委以重任,蒋介石又当上了北伐军总监,这一切让痛失丈夫的何香凝百思不得其解,许多人背地里议论,没有廖案的发生,蒋介石要迅速上升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据此怀疑有野心的蒋介石与刺杀廖仲恺有关。
9月的一天,何香凝应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邀请来到了东山周恩来家。寒暄几句后,大家心情沉重地说起最近发生的事,何香凝情不自禁地拉住邓颖超的手,流泪问道:“恩来啊,太可惜啦!你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不光是国民党的左派看不明白,连右派也看不明白!你们这样,无异于自毁长城啊!恩来,小超,请你们给我一个理由,贵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的邓颖超缄默无语,唯有陪她一起流泪。
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衬衫,和邓颖超并排坐在沙发上,同情地望着何香凝,凝重道:“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更是一个令人可笑的失败!”
何香凝擦擦眼泪,担忧地说:“把右派请回来犹自可,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倏然坐大,不仅成了中执委员,进入了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个新军阀的危险人物上台了!这,这难道不让人心惊胆战吗?仲恺先生的血怕是要白流了!”
这些日子以来,周恩来的心沉甸甸的,现在蒋的权力一天大似一天,第二次东征回来,蒋介石之风头已经盖过了汪精卫,北伐回来,那汪精卫兴许真要在蒋介石之下了。此时汪精卫却对黄埔军校的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引起了蒋的疑心与防备,周恩来觉察到蒋介石对汪精卫染指黄埔军校越来越不满,若他们两个为争夺军事实权而翻脸,共产党将陷入困境。
自从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不但去军校演讲,出席会议,还经常过问军校事务。这是否和蒋介石争夺军权的信号,还不能完全确定,虽然中央相信汪精卫仍是革命的左派,而蒋介石也仍以左派自居,可近来诸多右派迹象似乎已经显露出蛛丝马迹来,为什么蒋突然要军校学生名册,并注明哪些是共产党,哪些人不能重用,连在第二次东征战役讨伐陈炯明残部中救过蒋一命的陈赓也概莫能外。
黄埔军校里,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频起冲突,孙文主义学会是蒋介石成立的,而且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一直坚定地认为蒋介石是左派领袖,是不是自己多心了?就在昨天,蒋介石还签收了苏联军官押运到军校的加农炮12门、榴弹炮24门、重机枪538挺、子弹130万发等军械装备,准备北伐事宜……
浮想联翩的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局势的微妙变化。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扩充军力,组建一个党掌握的团,把铁甲车队充实到团里去,扩充进北伐的军队去,但此事又不能做得太明显。现在是国共关系紧张时期,而且共产国际反复强调一切要以维护合作为重,既不能给国民党右派以借口,也不能让国民党中立派担忧。
在此之前,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为防不测,曾经和陈延年、鲍罗廷商量,提过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但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陈延年为此事还和父亲陈独秀闹不和。
几天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彭湃在广东区委召集了秘密会议,周恩来说:“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正忙着扩编自己的队伍,多一个团对他来说正中下怀。但这个团我们不能让他染指。我们要把由我们党领导的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嵌进这个团去,再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中调一些人进去当军官,招募湖南、广西的贫苦农民来当兵,暗中扩充到2100人,怎么样?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那里要一个团的番号。”
彭湃听得异常兴奋,可又觉得似乎有点难:“恩来,这能办到吗?”
陈延年对目前广州的政局抱有清醒的认识,自然对周恩来的提议很赞成。
周恩来把叶挺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说:“叶挺同志是老粤军军官,与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还是小同乡,关系很好。因此,我建议这个团的团长,就由叶挺同志担任,大家有意见吗?”
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
叶挺,这位曾被毛泽东当面赞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的伟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1896年9月10 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归善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武昌起义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清革命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道路的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8年冬,年轻的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次年初到福建漳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一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役。后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叶挺奉命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几日,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10月的一个秋夜,苏联莫斯科。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急匆匆地在夜幕下的寂静街道上走着。他提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一幢哥特式红色尖顶的宏伟建筑——莫斯科东方大学。从此,莫斯科河边宁静而安详的林荫道下,多了一位喜欢一边走路一边背诵俄语单词的中国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派赴苏联留学的第一名国民党军人,也是班里唯一的非共产党人叶挺。在一年的紧张学习中,叶挺和同学王若飞、聂荣臻、陈乔年组成学习小组,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底,叶挺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底,叶挺毕业回国。
1925年11月,已入秋的广东肇庆,似乎依然眷恋着夏日的炽热不肯离去,微风犹带着热烈的气息,扑面而来。
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武装部队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
在一处隐秘偏僻的操场,不时有格斗操练的声音传出,这支由2100人组成的队伍已在这里进行秘密军事训练一个多月了。当时的番号是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周恩来、陈延年、彭湃、廖乾吾等人站在操场一侧,面色肃穆地凝视着这支英姿飒爽的军队。
叶挺身着军服,脚蹬马靴,手持军杖,威武地站在两千多名官兵前面。周士第、许继慎、卢德铭、周子昆等铁甲车队队员已成为各营连的指挥官。
陈延年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郑重走到叶挺面前,把一面军旗交给叶挺:“叶团长,你们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接过这面旗帜,让她高高飘扬!”
叶挺庄重地接过旗帜,然后对周士第、曹渊等命令道:“展开!”
一面红旗升到空中。
叶挺面对军旗大声说:“我们对军旗宣誓!”
穿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们整齐地举起拳头,跟着叶挺宣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永远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枪林弹雨、疾风暴雨中军旗不倒。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军旗的骄傲!”
1926年5月,第三十四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军官和士兵骨干几乎全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一支政治军事过硬的革命新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成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开端。
1886年12月1日,中国四川北部仪陇县的一个佃农家庭,诞生了另一个让历史铭记的伟人,他的名字叫朱德!
1915年12月,少年朱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投入川军步兵标(相当于团)当兵,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不久,报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他曾谈到那段时光:“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由于朱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才能,且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1917年7月升任滇军旅长,奉命移防泸州,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投身到反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中。那时的朱德处于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他开始抽鸦片麻醉自己。
1921年春,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他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写下了豪气干云的词句:“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
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1922年8月朱德远赴德国留学。在柏林,他结识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7月4日,朱德离开柏林,乘船前往苏联莫斯科。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下旬,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朱德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1926年夏天,朱德和共产党员房师亮等二十多人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海轮重返苦难深重、正在奋起中的祖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
一天下午,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停在上海一条里弄口。两位穿着长衫的男子朝四周望了望,急急拐进了弄口。走在后面的人正是刚从莫斯科回国接受任务的朱德,奉命接应的男子便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王一飞。两人在一间洋房门口停下,王一飞用暗号敲门。
开门的是陈独秀,他早早在家里等着了。王一飞介绍:“陈总书记,这就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这是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
朱德以前为入党的事见过陈独秀一次,当时的陈独秀对朱德抱有成见,态度冷淡,他认为一个在旧军队待过的人,沾染了旧军阀的习气,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而没有批准朱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件事对朱德伤害很大。
待王一飞走后,看着眼前壮实、质朴的朱德,陈独秀热情寒暄几句后便说:“朱德同志,4年了吧?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会对你那般冷落吗?
再次见到陈独秀,心里仍有些忐忑的朱德不好意思地:“呃……您大概是不太相信我吧?”
“是很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一个旧军阀出身的落魄军官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相信一个沾染了鸦片恶习的人能彻底革面自新!”陈独秀说话直截了当。
朱德附和着:“是的。很多人都不相信!”
陈独秀的眼睛流露出真诚,他看着同样真诚的朱德:“但现在我相信了!你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我证明、向党证明,你朱德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寻求人间正道、寻求伟大真理才来寻找共产党的!”
听到这话,朱德的心如照进三春阳光,一股暖流顿时涌入。
陈独秀交代了任务:“你在国外的学习、工作情况组织上已经了解。你很努力,很认真,非常好!鉴于你特殊的经历,我同意你去四川找杨森,做他的工作;当然,广东方面也很需要你,你也可以选择去广东,直接参加北伐。”
朱德略一思考:“总书记,那我还是去四川吧。我与杨森素有交谊,在我出国前路过四川时,杨还表示要对我‘虚位以待’。我去他那里,可能收效会比较大。”
陈独秀想了想:“那好,就去杨森部搞‘兵运’工作!不过,朱德同志,在你动身之前,我还需要你在上海稍作停留,利用你在滇军中的旧关系,去完成一项重要的调查任务。”
“好!”朱德说。
就这样,朱德——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以全部的精力和热血投入到了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中。
随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等黄埔将领和革命将士来了,从四面八方来了,等待北伐的战鼓擂响。而仍在广州的毛泽东,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步阐明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分析,确立了共产党对敌我友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