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一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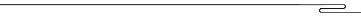
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乍一看跟传承了多少代似的,大有继烤鸭、涮羊肉之后成为北京餐饮名片的势头。不过论真了说,那些馆子里所卖的炸酱面将就着吃还可以,若论是否讲究可就另当别论了。也难怪许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吃了之后印象并不怎么样呢。
且不说那些面煮得是否透亮?酱炸得是否滋润?菜码布得是否讲究?小料配得是否精细?单瞧那些头发老长的服务员小伙子端上来一大堆不锈钢小碗,当着您的面儿叮咣五四地一通乱敲,把各种杂七杂八的配菜都折在面碗里,那份乱劲儿也不是老北京馆子的派头儿。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哪有那么闹腾的?再者说,老北京炸酱面都是在家里吃的,馆子里基本不卖。
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作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
比方说,中医有个说法叫药食同源。在中医看,凡是能够食用的东西,不论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等都既可以是“食”也可以是“药”,只不过是用量上的差异而已。因此严格来讲,药物和食物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像大米、白面、黄酱、白菜、生姜、大蒜、猪肉、羊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吃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通通是作为药物来记载的。
在《本草纲目》里,小麦被记载为气味甘、微寒、无毒。面粉则是甘、温、有微毒,还能消热止烦。而白菜叫做菘,“释名”中说:“白菜,按陆佃《埤雅》云: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名菘。今谓之白菜,其色表白也。”白菜的茎、叶“甘、温、无毒”。其主治是“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瘴气,止热气嗽,冬汁尤传佳。和中,利大小便”。在《本草纲目》里作为日常调味品的黄酱也是药。酱“咸、冷利、无毒”,可以治疗汤火伤、中砒毒以及妊娠下血等。
这又是白面,又是黄酱,又是白菜的,快做成一碗炸酱面了。其实,用中医的观点看,一碗炸酱面何尝不是一服方剂呢?
吃过中药的人都知道,一服中药是由许多味药材组成的。而“君臣佐使”就是中药的组方原则。这个原则形象地用古代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所起的不同作用生动地描述了一服方剂里各味药材的关系。《素问·至真要大论》里说:“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简称为“君、臣、佐、使”。君指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指辅助君药治疗主证,或主要治疗兼证的药物。佐指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使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这么一看,一碗炸酱面里的“君、臣、佐、使”就非常清楚了。
炸酱面,最主要的功效当然是充饥。中医说五谷为养。面提供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需的养分,没有了面,炸酱面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一碗炸酱面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面条,面条当然是“君”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滑润,煮出来也显得透亮。没有淀粉怎么也得是面粉,而没有像现在那些炸酱面馆里有棒子面的,那样煮出来快成一锅粥了。
“臣”,当然是炸酱。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炸酱面好不好吃,酱起着关键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猪肉丁,荤素配合,慢慢地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儿。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甘沃肥浓,香溢齿颊。过去拉车扛麻包的穷苦人吃不起炸酱,怎么办呢?就端个小碗去油盐店买上些酱油、醋、香油和在一起拌面将就着吃,美其名曰“三合油”,也算是炸酱的替代品吧。尽管有些穷欢喜,却也能真切地体会生活的乐趣。
一碗面里只有面和酱能不能吃呢?能。吃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不能的。只不过那就成了没有特色的光屁股面,一般人是不这么吃的。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与新鲜菜码的配合,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养、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用中医药的观点看,自然就是“佐”药了。
而醋、蒜这些起到了调和与引导作用的各种作料,刺激了食欲,开胃生津,配合酱和菜码让一碗面吃起来倍感舒坦,也就是中医药里所说的“使”。
看,一碗炸酱面就是一服搭配完美的中药,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说到炸酱面与中医药的关系,还想谈谈中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顺四时。简而言之,就是吃东西要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时令鲜蔬!而反季节蔬菜由于天道不合,最好不吃。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且不说应该依据中医的观点讲究四气五味,最简单地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
2010年冬天,我应邀担任一个中国炸酱面创新大赛的评委。那些选手真是下足了工夫,用尽了心思。酱里不仅加了番茄酱,有的还添了咖喱粉。菜码更是五彩缤纷,争奇斗妍。不仅有用苦瓜的,还有放海参的。可唯独没有一位放十冬腊月里最该放的大白菜的。创新是好事,但创新的前提是变而不离其宗,革而不失其理。海参本身没有任何味道,焯熟了做菜码未免糟蹋东西。而白菜是冬季最该放的菜码,尽管便宜,却体现了时令节气。用贵的东西未必是讲究,讲究和奢华是完全两回事。
《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热爱生活的祖先们观察到了自然的变化,把这些规律和饮食结合起来,和生活起居结合起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讲究。而那些规矩也好,讲究也罢,是经历了多少代人的积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为了让人们更加热爱生活。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就比如郑重其事地吃上一碗炸酱面。我们为什么不坐享祖先的智慧呢?
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儿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馨的气息。稍过个个把星期,伏地菠菜和火焰儿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焯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了那特有的鲜味。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儿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上,芹菜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
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
青豆嘴儿、香椿芽儿,
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莴笋片儿,
狗牙蒜要掰两瓣儿;豆芽菜,去掉根儿,
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批儿,
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
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
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是面码儿。
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疏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