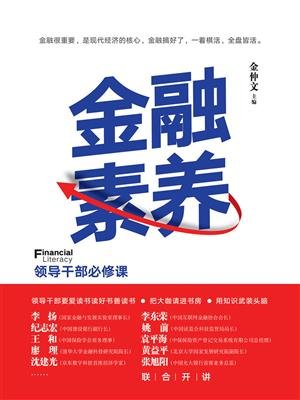三、优化金融结构
三、优化金融结构
在国民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结构问题居于核心地位。同样,在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金融结构也是所有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将优化金融结构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在现实中任何事物都是基于某种结构发挥作用的。当我们说现行的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指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严重扭曲,基于这样的结构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在金融学的术语体系中,所谓金融结构扭曲,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的“错配”上。
第一个“错配”是期限结构错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借短用长”现象。也就是说,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构,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们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资金来源期限短、资金使用期限长,两者之间存在期限错配,这是最主要的扭曲之一。虽然期限错配在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但在中国显然尤为突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工业化仍在进行中的国家,是一个正在大力推动城市化的国家,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对长期资金的需求比任何国家都强烈。但是,基于现行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我们的资金来源期限又相对较短,这就使得克服期限错配成了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众所周知,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严峻形势,中央在部署2019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发展任务时,再次强调了“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并且明确列示了11个主要投资领域。在这些主要投资领域中,除了“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之外,其他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等都需要长期、巨额的投资。这将矫正我国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之间的期限错配问题,并将其提高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一更为重要的地位上。
第二个“错配”是权益错配。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堪称“大爆炸”的巨变。正是这种变化,为我们提供了长期的、规模巨大且源源不断的储蓄资源,支撑了长期的高投资和高增长。然而,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结构下,我们动员的资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能形成资本、筹资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这就造成了权益错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经济规模扩张极为迅速,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此时资金结构的权益错配问题并不明显。然而,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行压力逐步显现,问题资产逐步“水落石出”之时,权益资金形成不足的问题就渐次显露。我们现在“谈之色变”的债务负担过重、杠杆率飙升、资本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与我国金融结构的权益错配密切相关。
第三个错配是服务对象的偏颇。迄今为止,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为有钱人、大企业、国企服务的。而面对广大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等这些更需要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我们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
因此,优化金融结构,就是要纠正以上三个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关于健全四种性质的金融结构体系问题,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已有了部署。遗憾的是,六年前的部署,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落实。提出四种性质的金融活动并举,是我国面对新时期、新任务的一大创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务是推动金融体系向着市场化、商业化方向发展——所谓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认为“过时”而扔到“垃圾堆”里;至于合作性金融,在中国历经多次“折腾”,至今仍举步维艰;而开发性金融,也只是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的新产物,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就更谈不上了。简单回顾历史便可知晓:我们发展金融体系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地从基层做起,发展信用社、发展村镇银行、支持小额信贷发展等,不一而足。但是,发展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大银行的天下”。更严重的是,无论何种规模、居于何地,银行的业务几乎是高度同构化的。所以,提出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切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弊端。
第二个方向,“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近年来,资本市场越来越得到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的重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也有所调整。在2019年2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经常念的“经”,似乎较少被提及,而资本市场自身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则被提到了首位。中央对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要求,如:把好市场入口、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等在过去也都比较少见。
论及发展资本市场,绝不能忽略一个略显尴尬的事实,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发展资本市场,但是至今结果不尽如人意。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对一个基本事实的长期忽略更值得探讨,即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根深蒂固,正是这个间接融资体系承担了资本市场原应促进资本形成的重任。
资料显示,2019年4月,中国存款类机构国内贷款余额共144.38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长期贷款高达89.808万亿元,占国内贷款总额的62%。这一比例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同期,美国国内持牌银行国内贷款余额15.045万亿美元。其中,中长期贷款5.152万亿美元,占比30%,仅及我国的一半。

进一步从中美双方银行资产中扣除对居民的房地产贷款,截至2019年4月底,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给工商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为54.2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国内贷款之比为37.5%,美国相应指标则锐减为0.334万亿美元,仅占其全部国内贷款2%。
列举上述数据并进行对比意在指出两点。其一,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因而,支持资本形成的金融结构也不尽相同。在美国,资本形成主要依赖高度发达的股票市场,而中国的资本形成则长期依赖高度发达的金融机构体系。从支持经济发展的客观效果来看,两种体系难分轩轾。其二,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一种制度被移植至其他国家,常有“南橘北枳”之虞。我们在经济和金融体制领域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在制度层面引进国外“最佳实践”时,一定要注意培养适合这些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性体制、机制条件。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未来改革发展的主攻方向,我们还须建立致力于长期融资的信用机构体系。其中,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住宅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长期信用机构应当成为发展的重点。同时,完善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推动新型产融结合以及发展助力资本形成的金融租赁等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方向,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这一战略安排意义深远。恰与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中发展迅速、同时也争议甚多、正在被整顿的资产管理有着密切关联。追求个性化、差异化和定制化,具体到产品和服务层面,就是“非标准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出表”(资金运用走出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出场”(资金交易走出场内,在场外进行)、“脱媒”(脱离金融中介,发展直接融资)等。近年来,随着金融领域创新迭出,我国金融产品“非标准化”趋势十分明显。由于监管未能及时到位,监管真空和重叠监管同时存在,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杠杆融资推波助澜,致使资管领域累积了大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管理业进行整肃,亦属正常。但是,要求资金由“表外”回到“表内”,由“场外”回到“场内”,由多样化变为单一化,由资本市场回到商业银行,只能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权宜之计。作为发展的方向,我们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还是要“出表”“出场”“脱媒”,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调整产品结构的另一任务,就是要增加中小金融企业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市场广阔、发展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这一类任务的提出,显然是与近年来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困境加剧密切相关,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对此进行纠正,自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