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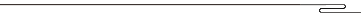
下姜村藏在群山的褶皱里,这种环境阻断了下姜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使下姜成了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的“孤岛”。如此,当地的土特产便无法与大市场对接,也就不能成为带动农民脱贫的利器。
“现在坐汽车从千岛湖镇到下姜,用不了一个小时。当年可不是这样。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行路难,我这条小命差点交待了。”下姜村村委会主任姜排岭是条精壮汉子,他粗粝的手掌厚实有力,和他握手时,只觉得有股劲道往骨缝里钻。
他撩起衣服,执意让我看他肚皮上那道长长的伤疤:“瞧见了吧,这道刀疤,是下姜交通不便的见证,也是过去贫困日子的见证。”
姜排岭告诉我,1971年出生的他,原名叫姜麦生,属于家族里的“麦”字辈,两个姐姐分别叫姜麦娜、姜麦娣。
大约半岁的时候,父母发现,原本很安静的麦生不安生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啼哭。刚开始大人没有当回事,可连着几天,麦生的动静越来越不对头了:不但躁动不安,还常常出冷汗、呕吐,再后来竟翻起了白眼。
父母这才意识到可能哪里不对了,赶紧把他送往村里的卫生所。村里的赤脚医生检查后认为:麦生的“肚子很重”(按现在的医疗术语讲,应该是“腹部包块”),必须马上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根据症状,再耽搁下去,性命难保。
父母急坏了,抱起麦生就往县城的方向跑。
县城在排岭镇(今千岛湖镇),当时还不通公交车,去一趟排岭镇要折腾大半天,不但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还要坐轮渡。
父母轮流抱着他,不停地跑啊跑,从上午一直跑到天擦黑,才赶到了医院。父亲的鞋底磨穿了,两只脚掌血肉模糊。
一到医院,医生马上把他送进了急诊室,确诊为肠套叠。
医生说,这本来是婴幼儿常见病,但耽搁得太久了,现在只能动手术试试看,能不能救过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院领导拍板,救人要紧,先做手术,手术费以后补上。
手术很成功,姜麦生捡回了一条命。
从医院回来后,为了纪念这次夫妻“远征”排岭镇的壮举,父母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姜排岭。
不过,为了把他从阎王爷手里夺回来,父母前前后后共花了9000多块钱。在以“分”和“角”为主要货币单位的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这笔巨款,父母靠出去打零工一点一点地攒、一点一点地还。全部还清,整整用去了8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去趟县城,就是出远门了。而去杭州,在我们心里,就像现在出一趟国一样让人兴奋。”曾担任过下姜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红马讲起了19岁那年第一次去杭州的经历。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杨红马接到一项任务——替生产队去杭州送货。要去杭州了!他激动得一宿没睡好,脑子里想象着从大人嘴里听来的有关杭州的一切。
父母得知这一消息,都替他担心,反复给他交代路上的注意事项。为了不让他在路上挨饿,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干粮。
第二天一早,他起得比谁都早,焦急地蹲在车旁候着,盘算着出发的时间。
“当时一起去的还有一位驾驶员和一个食品收购站的推销员。我们要把村里收购来的土猪,运到杭州农贸市场。”杨红马回忆。
那时通往县城的是一条盘山土路,不仅七弯八拐,而且坑坑洼洼,有的时候一个上下坡就得花掉一个小时。
刚出发,一切都是新鲜的。看着路两边的青山、绿水、房舍朝车后奔去,觉得蛮有意思。可是时间长了,就倦了。太阳已到头顶,还没有看到省城的影子。
他不停地问司机:“杭州还有多远?还有多远?”
司机永远是那句话:“早着呢!早着呢!”
当时的公路上,到处是雨水冲刷过的暗坑。车轮陷进去,要狠踩油门才能爬上来。有好几次,车轮打滑,差点翻车。杨红马出了一头又一头冷汗。
早晨5点不到就出发,直到太阳隐在地平线后,车子才有气无力地驶进了市区。
“一路上颠得我几次吐黄水。卸完土猪,办完事,我钻进车里就呼呼地睡着了。回去后,村里的人问我:‘看到西湖了吗?’我没好气地说,颠得我苦胆都要吐出来了。西湖就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我都懒得瞅上一眼。”
“下姜,困在山窝窝里,山珍土货运不出去,就是端着金碗也只能讨饭了。20世纪90年代,村里许多家庭种植了中草药,收购商对产品很满意。人家试着进村收购了一次,谁知回去的路上不停地抛锚,还差点翻车,人家一算账,觉得不合算,再也不来了。”
“那时候,好东西只能烂在手里。有几年,山上的竹笋都没人挖,因为挖了卖不掉。”杨红马无奈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