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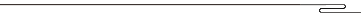
姜银祥,是我在下姜采访时接触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很注意穿着。基本上无论穿什么外套,里面都会搭配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很正式的那种,没有花纹,没有图案,衣服上唯一的装饰就是左胸前的口袋上别着的一枚党徽。搭眼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人当过干部咧!
他眼睛老花得厉害,但几乎不怎么戴眼镜,头发也染得乌黑,梳成偏分头,那道缝很直,两边的头发一丝不乱。用他的话说:“革命人永远年轻!”
记得他给我讲饥饿故事时,是个早晨。他执意要爬上村旁边那座最高的山的山顶,说,只有站得高了,才能看得远,话也才能讲得透亮。
清晨的下姜村,被淡淡的薄雾拥裹着。笼罩在柔和薄雾中的房舍,如同童话里的积木。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静,只有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河不知疲倦地“哗哗哗”流淌着。因为地势高的缘故,雾气凝成了团,微风拂过,白白的雾团飘来荡去。
在这样一个清晨,这样一个地点,姜银祥向我回忆过往时,一切都如同在梦里。而这个梦,是那样的苦涩。
“真正饿起来,恨不得桌子腿你都想卸下来吃掉。那种滋味,什么时候你都忘不了!”说这些话时,姜银祥的脸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1952年出生的他,是个遗腹子。
打小他就听母亲念叨:“啥时候才能填饱肚子?生在下姜,那是老天爷让你遭罪啊!”
父亲就是由于填不饱肚子,加上过度劳累,才早早撇下他们母子走的。
没了父亲,姜银祥只得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土改”后,家里分了三分五厘田。当时的水稻亩产是400多斤。三分五厘田,就是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产粮也不过100来斤。
三口之家一年100来斤粮,怎么着也不够吃呀!
小时候,姜银祥记忆最深的,就是母亲借粮的情景:每年刚过正月十五,母亲就会拿个口袋外出。傍晚,当她拖着疲惫的步伐回来时,大多时候满脸愁苦。
说是借粮,凭孤儿寡母这种状况,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亲戚朋友大多支支吾吾找个理由推脱。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家家都不宽裕呀。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几次碰壁后,她就对两个儿子说:“就是饿死,我们也不求人了。”她背起银祥,拽起大儿子上了山——她决计伐木烧炭,用烧好的木炭到山外换粮。
下姜村耕地少,但山地面积较大,漫山遍野长满了杂木。
烧炭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重体力活,一般人干不了。
一次次失败后,倔强的母亲终于找到了门道。几年后,哥哥把门道“接”了过来。
这时候,银祥已经可以帮着母亲、哥哥干活了:每天还没有睡醒,就被从床上拽起来,随着母亲和哥哥上山。早上一般没有东西吃,到了中午,母亲从布包里摸出两个饭团,看看哥哥,再看看银祥,然后长叹一口气,递给大儿子一个,因为砍柴、和泥这些重体力活都要靠大儿子。
她自己和银祥分另一个。而她手里拿的,总是最少的那一半。
半个饭团,哪够银祥吃!他三两口就吞了下去,又把目光投向哥哥。情况往往是这样:趁母亲不注意,哥哥再悄悄将自己的饭团掰一些给他。
烧炭要用硬柴。近处的硬柴早被人砍光了,哥哥砍一担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待硬柴砍回来,母子三人就围着窑坑一层层搭木头。搭好后,再把和好的泥糊在周围。
母亲说,要烧出一窑好炭,关键是留好透气孔:孔太小,火容易熄灭;孔太大,烧出的炭质量差,不经烧。除了这一点,还要把握封窑的时机,等到木柴都烧着了,就要用泥巴把透气孔糊上。这道工序更是要紧,要掐准火候,早封了晚封了都不行。
封窑之后,事情还没有完,得有人看守。这项工作,一般由姜银祥完成。母亲和哥哥还要忙田里的活计呢。
为什么要看守?莫非炭也有人偷?的确如此。那时候谁家都穷啊,人饿得没法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姜银祥很懂事,他坐在窑坑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从不到远处玩。不过,他也确实玩不动。吃不饱,哪来的力气玩。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全村人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这时候,姜银祥开始上学了。他印象最深的是开学时老师教的那首儿歌:“吃饭不要钱,幸福万万年,为什么男女老少笑开颜,嗨,幸福万万年!”
不过,还没吃上几顿饱饭,食堂就办不下去了。方圆十里八乡,下姜底子最薄,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就在这时,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了下姜人面前:1959年4月,为支持新安江水库建设,上级安排下姜村接收安置芮畈人民公社冯家墩大队的水库移民50户,共189人。
对于原本只有78户、330人的下姜村来说,新来居民数达到了原有人数的将近60%。
姜银祥家里新住进了两户人家:一户6口人,一户5口人。他家原本不足80平方米的3间破瓦房里,一下子要容纳14个人。屋里摆不开床,各家只能砍些树棍搭个上下铺挤着睡。
吃的问题,就更难解决了。1960年春节刚过,许多人家就断了顿。刚开始,集体还能给些接济,后来,附近的粮库全空了,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家庭。人们不得不放下日常活计,纷纷到附近的山上挖野菜和树根。
先是在村边的山上挖,可是不久,周边的塘丝坞、炭子坞、稻子尖……地就像被犁铧翻过一样,连枯草的断根都很难见到。小溪旁柳树的树皮一律被剥光,只剩下白花花的树干矗立着。
人们只好到深山里找吃的。往返二三十里路是很平常的事。
学校早就停课了,学生们随着家长往山里跑。这时候,学知识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到了1960年秋天,方圆几十里的山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挖的了,浮肿病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浮肿病?人体内,水分总是从浓度低的地方向浓度高的地方渗透。长期饥饿,血管里的蛋白质就很少,血液的浓度就很低。如果血管内液体的浓度低于血管外细胞间隙的液体浓度,那么,血管里的水分就会渗出,在细胞间隙流动,从上往下先在脚部形成积液,即形成水肿。积液越来越多,浮肿自下而上发展,最后全身浮肿。这种病无药可治,也无须用药治疗,只要有饭吃,血液里的蛋白质就会增加,浓度增加了,浮肿就消了。
可是,就算当时的人们明白这个道理,又能去哪里找吃的?
村里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人开始不管不顾地挖乌拉根(一种野生树根)吃。
老辈人都知道,这种树根,吃到嘴里甜甜的,可是吃下肚就麻烦了,像沉甸甸的石头堆在肠胃里,吃得越多,堆得越结实,排便也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再吃,就会要了命。
可人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暂时止住饿,管他明天怎么着。
讲到这里,姜银祥打住了,似乎不愿意回忆那段伤心的往事。过了许久许久,心情平复了,他才接着讲下去。
在姜银祥家住的那户移民人家,早就断了顿。姜银祥的母亲给他们送去了一点麸皮和野菜。
可老两口舍不得吃,把这些能活命的东西留给了孩子们。
老两口上山刨挖野乌拉根吃。几天之后,两个人的肠胃便出了问题,先是每天互相帮着用棍子从肛门里往外抠大便,后来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抠了,鼓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气无力地躺在院坝里“哼哼”。有一天早上,一阵急促的“哼哼”声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两个老人就这样先后去世了……
三年困难时期,下姜村一共饿死了30多口人。剩下的人,也大多得了浮肿病。严重的饥饿,还带来了生育率的严重下降。据村志记载:1960年到1962年,下姜村的人口出生率低得吓人,出生人数分别只有1人、4人、3人。
“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作答。
不等我回答,姜银祥自己回答了:“是土面。”
人民公社成立后,母亲在村上的磨坊为集体磨玉米面。
放学后,姜银祥会来磨坊玩。一次,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趁母亲不注意,从箩筐里抓了一把玉米粉就往嘴里塞。
谁知被母亲看到了,“啪”的就给了他一巴掌:“放下,这是公家的东西!”
母亲严厉的神色,把姜银祥吓住了。他怯怯地把面粉放回了箩筐。因为从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平时对他非常疼爱,别说打一巴掌,就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
姜银祥“哇哇”地哭了起来。
母亲也想不到自己会这样对待儿子。她先是一愣,然后,一把抱住儿子,抹起了眼泪:“儿,我知道你饿,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这句话,姜银祥记了一辈子。
母子俩相拥着哭了很久很久,突然,母亲想起了什么:“儿,别哭了。你瞧,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姜银祥疑惑地看着母亲。
母亲直起腰,拿起墙角的笤帚、撮箕,从土坯墙的缝隙里和窗框的角落里,一点点轻拂磨面时荡起的粉尘。扫遍了四面墙壁和窗框,收获显然不能使母亲满意。她又踩着凳子,将笤帚向房梁伸去,过了许久许久,终于使撮箕底部积了薄薄一层玉米粉和泥土的混合物。
母亲笑了,是那种寻到了无价之宝的开怀的笑。
她找来树枝、枯叶,生起火,把撮箕里的粉尘加点水和一下,捏成团,插在树棍上烤起来。不一会儿,一股奇异的香味便在空中弥漫开来。
说到这里,姜银祥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线条也柔和起来:“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呀。”
1969年,17岁的姜银祥通过虚报年龄当了兵。
因为从小吃不饱,体重不达标。为了体检能过关,他提前做了准备——很多天不洗澡,因为身上有点泥,多多少少可以增加点重量。体检当天他又喝了一大桶水,一直憋着不敢上厕所。
好悬啊,称体重时,勉勉强强达标。
到了部队,天天像过年,全班属姜银祥饭量最大。
肚子吃饱了,当年,姜银祥的身高就往上蹿了五六公分。
姜银祥坦言:“那时当兵,保家卫国的想法有没有?当然有。中苏关系正紧张,听说珍宝岛还干起来了。保家卫国,二话不说。不过,最主要还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个年代,因为饿长不高,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我的小姨子就只有一米多一点点。她的上一代、下一代的身高都挺正常,只有她的个子没有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