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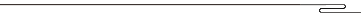
姜祖海年轻时,一定是个帅哥,鼻梁挺直,五官端正。1949年出生的他,正好70岁,可是背不弯、腰不塌,走起路来脚步轻捷。尤其是他的穿着,永远是那样得体、整洁,款式和做工也都很讲究。
一次聊天,我和他开玩笑:“老姜,总打扮得这么精神,老嫂子一定很能干!”
谁知老姜一点也不谦虚:“那是!那是!”
我正诧异间,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家那位,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关键是心眼儿也特别好。早年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人家一点也没有嫌弃我。”
接着,老姜给我讲了这段特殊年代“饿出来的爱情”。
“土改”时,姜祖海家有30亩地。这在下姜村,如同“羊群里钻出一头骆驼”,因此,工作队毫不犹豫地把他家定成了地主。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一旦成分不好,立马就被打入另册。姜祖海家在全村地位最低,动不动就要被贫下中农拉出来“过过筛子”。
姜祖海的父亲是读书人出身,知道读书的好处。尽管身份低微,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坚持让姜祖海读完了初中。姜祖海很争气,在学校,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村,初中毕业,算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了。如果成分好一点,吃“公家粮”应该问题不大。可姜祖海,一直没有单位敢录用。
天天在田里“戳牛屁股”不说,婚姻大事也亮了“红灯”——虽然一表人才,但一听他是地主出身,姑娘们扭头就走。
光阴荏苒,村里的同龄人都讨了媳妇,他20大几了,仍是单身。
见姜祖海老实本分,村里有个热心人,向几十里外的姜家镇下社村一户熟识的人家,帮姜祖海提亲。
这户人家姓洪,有个待字闺中的漂亮姑娘叫洪爱姣。
一听是下姜村的,洪爱姣的母亲首先反对:“下姜村?不行!不行!这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吗?人家不都这么说嘛,‘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
媒人来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劲儿夸姜祖海人品好、老实本分,并适时亮出了姜祖海是知识分子这块“招牌”。
看来,姑娘喜欢读书人。不管母亲怎么反对,姑娘还是红着脸答应赶集时远远见上一面。
这一见,姑娘芳心暗许:这不正是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嘛!
尽管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时节,爱情的芽儿还是从冰缝中冒了出来。几十里的山路,隔不断两颗火热的心,两个年轻人时不时会借口赶集见上一面。尽管见面时,也许羞赧得谁也不好意思说一句话。
不过,那位介绍人不该隐瞒一个重要事实——姜祖海的地主出身。
事有凑巧,正当进入谈婚论嫁的关键阶段时,又一场运动袭来,姜祖海的父母被捆起来,戴着高帽四邻八乡游斗。
这一下纸包不住火了。姑娘家里顿时炸了锅: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怎能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不光洪爱姣的母亲不干,亲戚朋友们也纷纷上门劝洪家退了这门亲。
姑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躲在房间里“嘤嘤”哭着不愿出门。
洪爱姣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家长,他问女儿:“你认为小伙子人怎么样?只要他人品好,你中意,这辈子你就有了靠山,日子就能过出滋味来。”
洪爱姣义无反顾地嫁到了下姜村。
过起日子,洪爱姣才领会到了“地主”两字的真正含义:那时候出义务工比较多,村上修水库、修渠、修大寨田这些最累的活儿都少不了姜祖海家;粮食年年歉收,家家常年吃不饱,每家每户都向集体借粮,唯独姜祖海家不行;过日子谁家都有缺个针头线脑的时候,可村里没人愿意借给姜祖海家……
“自嫁过来,我媳妇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为了多挣工分,在生产队,她像男劳力一样干活;回到家,她把家务活全抢了去,让我多歇一会儿;只要有一丁点好吃的,她就让着我,说自己不喜欢吃;就是做一碗粥,她也是把稠的捞给我,自己喝稀的……她不怎么会讲话,但是打心里疼我啊。这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太多!”念叨起妻子的好,姜祖海竟抹起了眼泪。
两个儿子落地后,添了两张嘴,日子就更难过了。怎样才能让妻儿吃饱肚子?姜祖海愁断了肠。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村里一些胆子大的,偷偷从山上砍伐一些盖房时能做檩条、椽子的树木,扛到衢州换粮。他心思一动,也想试试。
一根能做檩条的木材,至少百斤重。下姜到衢州近百里地。扛着百斤重的木材,连续不停地走近百里山路(为了躲避各种各样的检查,还要专拣人迹罕至的地方走),那简直是在搏命啊。
偷伐集体林木,等于偷盗。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偷盗意味着什么?一个地主的儿子偷盗又意味着什么?姜祖海心里清楚得很。但是,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他决定铤而走险。
趁着天黑,姜祖海上了山,循着白天做的标记,找到了自己要的树。放倒,去掉枝叶之后,已是后半夜。
当天出发已来不及。他把木材用柴草藏好,回到了家。连着两三天,他提心吊胆地在村里和山里晃悠,看看有没有惊动什么人。
太好了,一切如故。
第四天,是个阴雨天。姜祖海准备出发了。怕妻子担心,只说生产队里有公差,要出去几天。
出发时的情景,姜祖海记得清清楚楚:一大早,妻子就不见了,正疑惑间,她进来了,递给他一个能背在肩上的土布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冒着热气的玉米饼。
姜祖海一惊:“面缸已经快见底了,全烙成饼,你们吃什么?”
“家里还有吃的。”妻子头扭向别处,低声说。
姜祖海执意拿出一半的饼留给妻小。
洪爱姣把饼又塞回了包裹:“穷家富路。在家里,怎么着,都会有办法。”她的目光很坚定,不容姜祖海有任何的违拗。
就这样,姜祖海上路了。
他不敢走大路,只拣最偏僻的羊肠小道前行。一听到前面有动静,他就将木材迅速藏进草丛里,自己也找个树丛躲起来。确定四周安全了,再接着前行。
由于路不熟,他走走藏藏,藏藏走走,第三天才走到衢州地界。就在这时,他碰到了巡山的民兵小分队,而且是迎头碰上的,藏,已经来不及了。扔了木材跑?想一想妻儿面带菜色的脸,他又不甘心。那不是木材,是粮食,是一家人的命啊!
豁出去了,他扛着木材夺路而跑。后面四个年轻人奋力追赶。
“一定是‘四类分子’。站住!再不站住我们要开枪了。我们手里可有真家伙。”追的人煞有介事地咋呼着。
姜祖海什么也顾不得了,跑,跑,拼命地跑。只有跑赢了,妻儿才有饭吃!
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姜祖海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扛着百斤重的木材,最终竟跑赢了四个年轻人。
木材,扛到了衢州。更重要的事还在后头呢——寻找买主。
他把木材藏好,走进附近的村子,打探谁家正在盖房子或准备盖房子。
连续走了几个村子,都没有找到买主。
好不容易看到一户人家正在盖房子,他赶忙凑了上去,悄声说:“我有一根好檩条,想换点粮食……”
对方努了努嘴,让他看堆在当院的一堆木料:“来晚了。我备的料正愁用不完呢。”
干粮早就吃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响,双腿也像灌了铅。姜祖海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边上一个老汉插话了:“我准备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想备些料。不过,得先看看再说。”
姜祖海赶紧跑到村外,扛来了木材。
老汉踢了踢那根木材:“当不成主梁。算了。”
“叔,我扛了百里地。家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老汉心软了:“那就当辅料用吧。先说清楚了,换不了多少粮食。”
“您看着给,看着给。我不还价。”姜祖海鸡啄米般连连点头,生怕人家变卦了。
姜祖海终于换回了半袋大米。好像是两三年前的陈米,颜色已不那么鲜亮了。但他感激不尽,真想跪下来给老汉磕几个响头。
回到家中,姜祖海发现妻子躺在床上,已起不来床了。听大儿子说,妻子用扫缸底的面给他们熬了粥,而自己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这时他才知道,妻子那句“家里还有吃的”是让他放宽心的谎言……姜祖海的眼泪流了下来。
“家里还有吃的。”这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情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