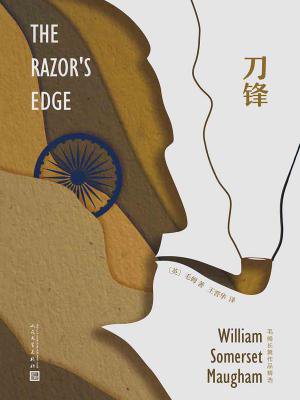第七章
在芝加哥逗留期间,有人介绍我加入了一家藏书较多的俱乐部,第二天早晨我去那里查阅一两本大学杂志,这种刊物如果不是长期订阅的话,一般很难碰到。时间还早,阅览室里只有一个人。他坐在一把很大的皮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是拉里。我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他。我走过时,他抬头看到了我,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不要动,”我说,接着几乎是很自然地问,“你在读什么?”
“一本书。”他笑着说。他的笑十分动人,以至于他这样的一个回答不会叫人觉得无礼或是唐突。
他阖上书,用他那双显得特别深邃的眼睛望着我,手遮着一些封面,让我看不清书名。
“你昨晚玩得好吗?”我问。
“好极了。早晨五点才回到家。”
“你可真勤奋啊,这么早就很精神地在这儿了。”
“我常常来这儿。一般情况下,这个点来,这个位置总是我的。”
“我不打搅你了。”
“你没有打搅我。”他说,又一次笑了,此刻我发现他的笑非常迷人、可爱,不是那种灿烂夺目的笑,而像是用内心的光照点亮的笑容。他坐在一个书架围成的角落里,旁边还放着一把椅子。他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你能坐一会儿吗?”
“好的。”
他把手中的书递给了我。
“这就是我读的书。”
我一看,是威廉·詹姆斯写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部名著,是心理学史上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而且写得极其晓畅。不过,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曾当过飞行员、跳舞跳到早晨五点钟的小伙子(只有二十岁)会读的那种书。
“你为什么要读这个?”我问。
“我懂的知识太少了。”
“可你还非常年轻呀。”我笑着说。
他好大一会儿没有说话,他的沉默开始让我觉得有些尴尬,我想起身去看我要找的那几本杂志。可是,我有一种感觉,他是想要说些什么。他的眼睛望着前面,脸上的表情严肃、专注,似乎在沉思。我等着他。我很想听听他要说什么。当他开口时,好像是在继续他的谈话,丝毫也没有察觉到之间的那段沉默。
“从法国回来后,他们都想叫我上大学。可我不能。经历了这场战争以后,我觉得我再也回不到学校去了。上中学时,我就什么也没有学到。我觉得我无法融入大学的生活。同学们不会喜欢我。我不愿勉强自己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我认为大学里的老师教不了我所想要的知识。”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可我不敢肯定你就是对的。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经历了两年的战争,再到大学里做个自命不凡的新生,实在有些腻味。我并不认为同学们会不喜欢你。我不太了解美国的大学,不过,我并不认为美国的大学生和英国的会有太大的不同,或许美国的大学生更外向一些,更喜欢喧闹的娱乐,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懂礼、懂事的男孩;我敢说,如果你不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只要你稍使手腕,他们也会乐意让你过你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像我兄弟那样,进入剑桥大学。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我放弃了。我想早一点儿到社会上去闯荡。后来,我一直为此感到后悔。要是我当时上了剑桥,我会少走许多弯路。有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你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没有人给你引路,你常常会走进死胡同,浪费掉你不少的时间。”
“你也许是对的。我并不在乎自己犯错误。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死胡同里,我会发现了一些与我的目的相合的东西。”
“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犹豫了片刻。
“问题就在这儿。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呢。”
我没有吭声,因为对此似乎没有必要去回答什么,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在脑子里,因此我有些不耐烦了,可我抑制住了自己。我有种感觉,不如说是直觉:有什么东西在搅扰着这个小伙子的心灵,到底是不成熟的想法还是模糊的情感,我不得而知,它们使他不得安宁、驱使着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驶向哪里。不知怎么的,他引起了我的同情。以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只是现在,我才意识到他的声音多么悦耳。它能令你陶醉,像是散发着香味的仙丹。想到这一点,想到他迷人的笑容、黑得发亮的富于表情的眼睛,我便完全理解伊莎贝尔为什么那么爱他了。他身上的确有些特别可爱的地方。他转过头来,眼睛很坦然、饶有兴味地审视着我。
“我想,昨晚我们都去跳舞以后,你们谈论我了,是吗?”
“是谈你来着。”
“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非要把鲍勃叔叔请来吃饭的原因。他顶讨厌出门了。”
“似乎有人给你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一份非常棒的工作。”
“你打算去吗?”
“不去。”
“为什么不呢?”
“我不想干。”
我在插手一件与我毫无关系的事情,不过,我也看出来了,正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所以拉里不抵触跟我谈谈这件事。
“哦,你知道的,当人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时候,他们便成了作家。”我说着笑出声来。
“我没有才能。”
“那么,你打算做什么呢?”
他朝我笑了,那种灿烂迷人的笑容。
“游荡。”他说。
听到这话我笑了起来。
“依我看,在这个世界上芝加哥可不是一个理想的逍遥地,”我说,“好吧,我不打搅你读书了。我去找找《耶鲁季刊》。”
我站起来离开阅览室后,拉里仍然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读着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我独自在俱乐部吃了中午饭,因为阅览室里比较安静,我又踅回到那里抽雪茄、看书写信,就这样消磨了一两个钟头。我惊讶地发现拉里还在埋头读着那本书。自我离开他以后,他似乎就没有动过地方。我四点钟离开阅览室时,他还在那里。他的这种非常强的专注精神令人难忘。他既没有注意到我来,也没有注意到我走。我下午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直到应该换衣服赴宴时,才往旅店赶。路上,受着好奇心的驱使,我又一次进到俱乐部的阅览室。有不少人在那里读着报纸杂志。拉里仍然坐在那把椅子上,专心地读那本书。好怪的一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