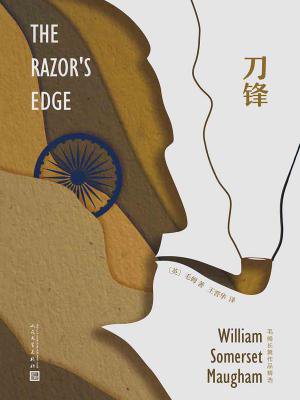第八章
第二天,艾略特邀我到芭玛大厦,与老马图林和他的儿子一起吃午饭。饭桌上只有我们四个人。亨利·马图林是个大块头的男人,几乎和他儿子一样魁梧,他有张肉乎乎的红脸庞,一个大下巴,同样有着挑衅性的又短又扁的鼻子,不过,他的眼睛比儿子的小一些,也没有那么蓝,可看上去非常非常精明。尽管他顶多五十岁,可看上去足有六十岁,已经变得稀稀疏疏的头发全白了。乍一看,毫无魅力可言。这许多年来他似乎生意兴隆,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十分冷酷、聪明、能干的人,在关乎生意的事情上绝不会有半点儿心慈手软。起初,他说话很少,我觉得他是在考量我。看得出来,艾略特在他眼中只是个可笑的人物。格雷温和恭敬,几乎一声没吭,要不是艾略特施展出他娴熟的社交本领,一直扯着一些轻松的话题,大家恐怕早僵在那儿了。我猜测过去艾略特常常跟中西部的商人做交易,一定积累了不少经验,否则的话,他就哄不得人家掏大价钱,买下已逝大师的名画了。不多一会儿,马图林先生渐渐变得自如了,也说了几句,表明他比看上去要活泼得多,而且他确实还有一种冷幽默呢。谈话有一会儿转到股票上。要不是我早先便知道艾略特这个人尽管有时荒唐,可一点儿也不傻,那么,我就会为他在这方面也讲得头头是道感到诧异了。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图林先生说话了:
“今天早晨,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的一封信。”
“你没有告诉我,爸爸。”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把身子转向了我。
“你认识拉里,是吗?”
我点了点头。
“格雷说服了我,让我把他弄进我的公司里。他们俩是好朋友。格雷觉得拉里非常优秀。”
“拉里怎么说的,爸爸?”
“他对我表示了感谢。他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我的提议,最终觉得他恐怕会让我失望的,认为他还是拒绝为好。”
“他这么做很愚蠢。”艾略特说。
“是的。”马图林先生说。
“很抱歉,爸爸,”格雷说,“要是我们能一起工作,那该有多好啊。”
“你可以把一匹马领到河边,可你无法硬让它饮水。”
在马图林先生这么说的时候,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儿子,他精明的眼神变得温和起来。这让我意识到这位冷酷的生意人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对这个大块头的儿子宠爱有加。有一次他面朝着我说:
“你知道吗,星期天这孩子在场子里跟我打了两盘让点赛,他分别赢了我七点和六点。我真想用球棒打破他的脑袋。又一想,是我亲手教会了他打高尔夫球。”
马图林先生的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神情。我开始喜欢他了。
“是我的运气好,爸爸。”
“与运气无关。你把球从洞里打出来,落下来离洞口只有十五厘米远,这难道是运气?一杆打出整整三十二米远,一寸不多,一寸不少。我想让他参加明年的业余锦标赛。”
“我抽不出时间来的。”
“我是你的老板,不是吗?”
“我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我晚来上班一分钟,你就会火冒三丈。”
马图林先生扑哧一声笑了。
“他快要把我说成是一个暴君了,”他对我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公司都是我在经营,我的几个合伙人都不行,而我又非常看重我的生意。我让儿子从最底层做起,我期望他像我公司里的别的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这样等将来他接班的时候就能胜任了。对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我的一些主顾的投资交给我经管已经有三十年了,他们对我十分信任。实话跟你说吧,我宁愿损失掉自己的钱,也不愿看到我的客户遭受损失。”
格雷此时笑了起来。
“那天有个老姑娘来公司,想拿一千美元投资一桩她的牧师推荐的投机生意,让我父亲拒绝了,她硬是坚持要做时,父亲一顿严厉的训斥,最后她无奈地哭着离开了。后来,他又去见那牧师,给他好一顿训。”
“人们对我们做经纪人的,有许多不好的议论,但是,经纪人和经纪人不一样。我不想让我的客户亏本,我想让他们赚钱,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行事方式会让你觉得,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赔掉自己手中的每一分钱。”
“呃,对马图林先生你怎么看?”在马图林父子去上班、我们也出来了以后,艾略特问我。
“我总喜欢接触不同类型的人。我觉得他们父子之间的那种亲情挺感人的。敢说在英国这种情形并不常见。”
“他很爱格雷。他的性格是个奇怪的混合体。他说他客户的话都是真的。他手里有上百个客户,包括女人、退了休的职员、牧师等,他经管着他们的积蓄。要我说,这些主顾所带来的麻烦远超过他们的价值,可是他却为他们对他的信任感到自豪。在搞到大生意、有大钱可赚时,没有谁会比他更心狠手辣。那个时候的他根本没有了怜悯之心。他非要把他的那一磅肉弄到手
 不可,什么也阻挡不了他去得到它。若是挡了他的道,他不仅会让你赔得一败涂地,而且会为此而喜不自胜。”
不可,什么也阻挡不了他去得到它。若是挡了他的道,他不仅会让你赔得一败涂地,而且会为此而喜不自胜。”
在回到他姐姐家后,艾略特告诉了布拉德雷太太,拉里拒绝了亨利·马图林给他的工作。伊莎贝尔出去跟她的女朋友们一起吃午饭了,她进来时,姐弟俩正在谈这件事。于是,便告诉了她。从后来艾略特对他们这场谈话的讲述中,我推测出当时艾略特用他滔滔的言辞充分表达了他的意见。尽管有十年他没做过任何事情,尽管他用以赚到他丰厚家资的工作远远谈不上艰辛,可他坚定地认为,工商业是人类得以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拉里是一个极普通的青年,毫无社会地位,他没有理由不去遵循本国的好的行为习惯。在像艾略特这样有洞见的人看来,美国显然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的繁盛期。拉里现在有个入门的机会,如若他抓住这个机会,埋头苦干下去,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到那个时候,如果他不想做了,想在巴黎像个上等人那样生活,在巴黎杜布瓦大街租上一套公寓,或是在卢瓦尔河谷的都兰置上所宅邸,他艾略特绝不会反对。而路易莎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更难以辩驳。
“如果拉里爱你,他就应该为你接受这份工作。”
对这些,我不知道伊莎贝尔是怎么回答的,不过,凭她的善解人意,她当然能看出母亲和舅舅的话自有他们的道理。她认识的小伙子们都在努力学习,准备参加工作,或是已经上了班。拉里几乎不可能靠着他在空军的杰出表现,来度过他的这一生。战争已经结束,人人都厌恶了战争,巴不得尽快将它忘记。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伊莎贝尔同意跟拉里摊牌,就这件事跟拉里最后谈一次。布拉德雷太太建议伊莎贝尔叫拉里开车带她去一趟麻汾。她正准备给老宅的客厅置办新窗帘,可她上次量好的尺寸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所以她想让伊莎贝尔再去量一下。
“鲍勃·纳尔逊会招待你们吃午饭的。”布拉德雷太太说。
“我有一个比这更好的计划,”艾略特说,“给他们带上一篮子食物,让他们在廊沿上吃,饭一吃完,他们就可以谈了。”
“这样会有趣得多。”伊莎贝尔说。
“很少有什么比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野餐更开心的了,”艾略特颇有意味地补充道,“老蒂泽公爵夫人常跟我说,最为桀骜不驯的男人在这种场合下也会变得易于说服。你计划给他们的午餐准备些什么呢?”
“酿馅鸡蛋和夹鸡肉的三明治。”
“瞎说。没有肥肝酱,怎能算得上一顿像样的野餐呢。你得给他们带上咖喱虾仁、鸡脯冻,搭配生菜心色拉,这都得由我亲自来做。在肥肝酱之后,作为对你们美国习俗的妥协,你可以上个苹果派。”
“我就给他们带酿馅鸡蛋和夹鸡肉的三明治,艾略特。”布拉德雷太太很坚决地说。
“哦,好吧,我有言在先,事情一定办不好,要怪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拉里吃得很少,艾略特舅舅,”伊莎贝尔说,“我觉得,他根本不在意他吃的是什么。”
“我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点,我可怜的外甥女。”她的舅舅回了她一句。
然而,他们最后带上的食物,还是布拉德雷太太说的那些。当后来艾略特告诉了我他们此行的结果时,他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
“我早说过,这样事情会搞砸的。我恳求路易莎给他们带上一瓶我送她的蒙特拉夕酒,是我在战前送给她的,可她就是不听。他们只拿了一暖水瓶咖啡。你还能期望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时的情形好像是路易莎·布拉德雷和艾略特正在客厅里坐着,突然听到汽车停在门口的声音,紧接着,伊莎贝尔走了进来。天刚黑,窗帘已拉了下来。艾略特坐在壁炉旁边的一把扶手椅子里,正读着一张报纸,布拉德雷太太在一块预备做遮火屏的东西上刺绣。伊莎贝尔没有来客厅,而是径直走回了她的房间。
艾略特从他眼镜的上面看着他的姐姐。
“我想,她去脱帽子了。很快就会下来。”她说。
可是伊莎贝尔没有下来。几分钟过去了。
“也许她累了。可能已经躺下了。”
“难道你脑子里没有想过拉里会一起进来吗?”
“不要再烦我了,艾略特。”
“好吧,这是你的事情,又不是我的。”
他又读起了他的书。布拉德雷太太继续做她的刺绣活儿。不过,半个小时后,布拉德雷太太突然站了起来。
“我想,或许我最好还是上去看看吧,如果她没事,休息了,我就不打扰她,自己下来。”
她出去不多一会儿,便又回来了。
“她在哭。拉里打算去巴黎。他要在那儿待两年。她答应等他。”
“为什么他要去巴黎?”
“你问我这些问题没有用,艾略特。我不知道。她什么也不跟我说。她说她能理解他,不愿干涉他的行为。我对她说,‘如若他想好了要离开你两年,他就不可能有多么爱你。’‘我没得选择,’她说,‘最重要的是我非常爱他。’‘甚至在今天的事发生之后吗?’我问。‘今天发生的事情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爱他,’她说,‘他的确是爱我的,妈妈。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艾略特思考了一会儿。
“到两年结束的时候,不知会怎么样?”
“我告诉过你了,艾略特,我不知道。”
“难道你不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很令人失望吗?”
“很令人失望。”
“唯一能给人一点儿慰藉的是,他们两个都还很年轻,等两年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在这两年中间,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姐弟俩商定最好还是不要问伊莎贝尔。因为晚上他们还要一起出去吃饭。
“我不想再去烦她了,”布拉德雷太太说,“如果她的眼睛哭得红肿了,人们会觉得奇怪,会问的。”
不过,第二天,当他们在家里吃过午饭后,布拉德雷太太又谈起这个话题。只是她很难从伊莎贝尔这里再得到什么。
“真的,妈妈,我没有保留,我已经都告诉你了。”她说。
“可他在巴黎想要做什么呢?”
伊莎贝尔笑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回答会让母亲觉得有多么荒唐。
“游荡。”
“游荡?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他告诉我的话。”
“我真的对你失去耐心了。如果你还有点儿骨气的话,你当时在那里就该跟他断了关系。他这是在耍你。”
伊莎贝尔望着她左手指上戴着的戒指。
“我有什么法子?谁让我爱他呢。”
这个时候,艾略特插话了。他拿出他高明的手腕谈及这件事情,“我不是作为她的舅舅,老兄,而是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跟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女孩说话。”然而,他做得并不比她母亲的效果好。我从他的话里得到的印象是,伊莎贝尔叫他别管闲事,尽管她会说得很有礼貌,可意思明确无误。这些都是艾略特在那天较晚的时候,在我住的黑石旅店的小起居间告诉我的。
“当然,路易莎是对的。”他又说道,“出现这种情况,让人感到非常不愉快,可让年轻人们只是靠彼此间的爱慕之情——别的什么也不问——去安排他们的婚姻时,碰到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我劝路易莎不要着急,我想事情将来的结果也许比她预想的要好。拉里远在巴黎,而格雷却活生生地就在眼前——哦,如果说我对我的同胞还是了解的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在十八岁时,情感会很强烈,但很难持久。”
“你真是个精于世故的人,艾略特。”我笑着说。
“我读拉罗什福科
 可不是白读的。你知道芝加哥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常常见面、在一起玩。一个女孩有个小伙子这么全身心地爱她,心里面一定美滋滋的。当她知道在她认识的女孩里没有一个不愿意高兴地嫁给他时,哦,我问你,从人易受诱惑的本性上看,她会不会去把别的女孩都挤掉呢?这就像参加一个聚会,你明明知道很无趣,而且所有的吃喝也只有柠檬汁和饼干,可你还是会去,因为你打听到你最好的朋友都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参加,却没有被邀请。”
可不是白读的。你知道芝加哥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常常见面、在一起玩。一个女孩有个小伙子这么全身心地爱她,心里面一定美滋滋的。当她知道在她认识的女孩里没有一个不愿意高兴地嫁给他时,哦,我问你,从人易受诱惑的本性上看,她会不会去把别的女孩都挤掉呢?这就像参加一个聚会,你明明知道很无趣,而且所有的吃喝也只有柠檬汁和饼干,可你还是会去,因为你打听到你最好的朋友都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参加,却没有被邀请。”
“拉里什么时候走?”
“我不清楚。我认为,这该还不是最后的决定。”艾略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金和黄金合镶的又长又薄的烟盒子,从里面抽出一支埃及烟。法蒂玛、吉士、骆驼、好运道
 等牌子他是不抽的。他颇有意味地笑着看着我。“当然啦,我不会跟路易莎这么说的,不过,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其实私下里我对这位年轻人还是很同情的。我知道他在战争期间曾去过巴黎,如果他被这座世界上唯一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给迷住了,我一点儿也不会怪他。他这么年轻,我以为他是想趁结婚之前,让自己放纵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会关照他的。我会把他介绍给巴黎的知名人士,他举止优雅,经我稍加点拨,他便会出落得不错的;我敢担保,我能让他看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的法国生活的另一面。信我的话,老兄,一般美国人进天国都要比他们进日耳曼大街容易得多。他二十岁,又很有魅力。我想,我也许能帮他跟一个贵夫人搭上关系。这会成就他。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能成为一个年龄较大的女人的情人,会给予他最好的教育,当然啦,这个女人必须是我所赞赏的那种女人,是一位妇女界的名流,这会使他很快在巴黎有一定的地位。”
等牌子他是不抽的。他颇有意味地笑着看着我。“当然啦,我不会跟路易莎这么说的,不过,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其实私下里我对这位年轻人还是很同情的。我知道他在战争期间曾去过巴黎,如果他被这座世界上唯一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给迷住了,我一点儿也不会怪他。他这么年轻,我以为他是想趁结婚之前,让自己放纵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会关照他的。我会把他介绍给巴黎的知名人士,他举止优雅,经我稍加点拨,他便会出落得不错的;我敢担保,我能让他看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的法国生活的另一面。信我的话,老兄,一般美国人进天国都要比他们进日耳曼大街容易得多。他二十岁,又很有魅力。我想,我也许能帮他跟一个贵夫人搭上关系。这会成就他。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能成为一个年龄较大的女人的情人,会给予他最好的教育,当然啦,这个女人必须是我所赞赏的那种女人,是一位妇女界的名流,这会使他很快在巴黎有一定的地位。”
“你把这话告诉过布拉德雷太太吗?”我笑着问。
艾略特哈哈地笑了。
“老兄,如果我身上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待人处事的技巧。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懂的,可怜的女人。在有些事情上,我永远搞不懂路易莎,比如说这一件:虽说她一半的生涯是在外交界度过,另一半是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度过,可她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