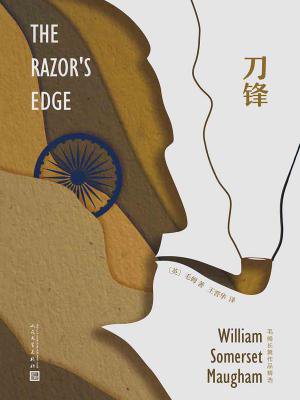第一章
每开始写一部小说,我都会疑惑,却从未像现在这么疑惑过。如果我仍然将其称为小说,那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我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也没有以主人公的死亡或是结婚收尾。死是一切的了结,因此是一个故事的总收场,以美满姻缘作为结束也挺恰当的,那些老于世故的人大可不必对传统上称作大团圆的结局嗤之以鼻。普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宁愿故事这样结尾,觉得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当一对男女历尽沧桑、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便完成了生理上的功能,将把香火延续下去。可我写到终章也没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结局。我这本书写的是对一个人的回忆,我只与这个人有过十来次较为亲密的接触,而且每次之间都隔着很长的时间,对我们不在一起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几乎毫无所知。我想,凭借杜撰,我蛮可以填补起这之间的空白,使我的讲述更为紧凑、连贯;不过,我并不想这么做。我只打算记下自己知道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写过一部叫《月亮和六便士》的小说。在那部描写著名画家高更的作品中,我运用小说家的权利,编造了一些事件,以揭示主人公的性格。对这位法国艺术家的事迹我了解得不多,用这不多的事实在我脑中形成的联想和启迪,我创作了这个人物。然而,在这部书里,我丝毫也没有想过要那么做。我没有杜撰任何东西。为了不叫现在依然活着的人感到尴尬,我给这部书中的原型人物们起了新的名字,在故事编排等方面我也做了努力,不会让任何读者认出这些人来。我所写的这个人并不出名。或许他这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人。也许在他生命最终结束的时候,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印迹,就犹如一块石子扔进河里后水面浮现的涟漪。到那个时候,如果我的这本书还有人读的话,那也将只是为了读出它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不过,也许他为自己所选定的生活道路以及他性格中所具有的美善和那种特别的力量,会对他周边的朋友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以至于在他死了很长时间以后,人们会逐渐地意识到,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那时人们就会清楚我写的这个人是谁了,那些想要多少了解他早期生活的人们也许会在这部书里找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想,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我那些想要写他传记的朋友,我的这部作品也将是一个可资征引的信息来源。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书中人物的对话并非是如实的逐字逐句的记载。我对在这一场合或是那一场合的谈话从来没有做过记录。不过,我对自己关心的事物还是有个好记性的,尽管我是用自己的词语写出了这些对话,可我还是相信,自己忠实地传达出了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在前面一点儿的地方说过,我没有杜撰任何东西;现在,我想修正一下我的这一说法。就像自希罗多德
 以来的历史学家们一样,我给书中人物的口中擅自添加了一些我不曾听到或者说没有可能听到的话语。和历史学家们一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作品中的场景显得生动、真切,如若只是简单地记述,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我想让我的书被人们阅读,我认为我有理由尽可能地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聪明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我在哪些地方运用了这一技巧,他有完全的自由跳过这些地方不读。
以来的历史学家们一样,我给书中人物的口中擅自添加了一些我不曾听到或者说没有可能听到的话语。和历史学家们一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作品中的场景显得生动、真切,如若只是简单地记述,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我想让我的书被人们阅读,我认为我有理由尽可能地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聪明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我在哪些地方运用了这一技巧,他有完全的自由跳过这些地方不读。
写这部作品,还有一个让我放心不下的地方是,我描述的人物大多是美国人。了解人是非常难的,我以为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外国人,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无论男女,人都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出生的那一地域,他们在其间学步的农场或是城市的公寓,他们儿时玩耍的游戏,他们听来的老奶奶的故事,他们所吃的食物、所上的学校、所参加的运动、平日里所读的诗歌,还有他们信仰的上帝……所有这一切把他们造就成了他们现在的样子。而这些都不是凭借道听途说就能知晓的事物,唯有你自己经历过,你才能了解。你唯有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你才能懂他们。
由于对外国人的了解只是凭借观察,所以很难在书中把他们刻画得真切。甚至像亨利·詹姆斯
 那样敏锐那样细心的观察家,尽管他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也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拿我自己来说,除了几个短篇小说外,我写的都是本国人。如果说我敢于在一些短篇中写外国人,那也是因为在这种体裁中我能较为笼统地处置人物。你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个大略的轮廓,留待读者去填补细节。你也许会问,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我把主人公的原型法国画家高更设定成了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这部作品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要说的是,我书中的这些人物并非是从他们本国人眼中见出的美国人;而是从一个英国人眼中见出的美国人。我并没有尝试着再现他们讲话的特点。英国作家在这样做时会闯出乱子,恰如美国作家在再现本土英国人讲话时所出现的情况。俚语是个很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描述英国人的作品中常常使用俚语,但是他从未能像英国人那样来使用它们,因此他非但没能达到他所追求的效果,反倒常常给英国读者一种不舒服的突兀感。
那样敏锐那样细心的观察家,尽管他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也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拿我自己来说,除了几个短篇小说外,我写的都是本国人。如果说我敢于在一些短篇中写外国人,那也是因为在这种体裁中我能较为笼统地处置人物。你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个大略的轮廓,留待读者去填补细节。你也许会问,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我把主人公的原型法国画家高更设定成了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这部作品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要说的是,我书中的这些人物并非是从他们本国人眼中见出的美国人;而是从一个英国人眼中见出的美国人。我并没有尝试着再现他们讲话的特点。英国作家在这样做时会闯出乱子,恰如美国作家在再现本土英国人讲话时所出现的情况。俚语是个很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描述英国人的作品中常常使用俚语,但是他从未能像英国人那样来使用它们,因此他非但没能达到他所追求的效果,反倒常常给英国读者一种不舒服的突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