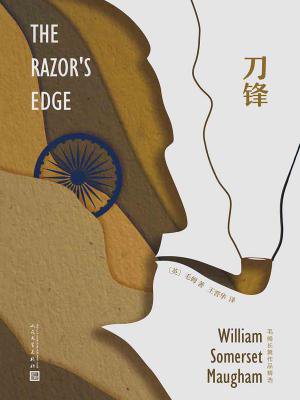第六章
第二天傍晚,我谢绝了艾略特在电话中要过来接我的请求,独自安全地抵达了布拉德雷太太的家。有个人到旅店来看我,让我耽搁了一会儿,所以到得晚了点儿。上楼时,我听到客厅里传出的喧嚷声,以为来的人一定不少,进去后才发现,连我自己,一共只有十二个人。布拉德雷太太穿一身绿缎子衣服,脖上戴一串细珠项链,非常富丽;艾略特的晚礼服样式时尚,他那副潇洒倜傥,唯他独有。在他跟我握手时,一股阿拉伯香水的气味直扑我的鼻孔。艾略特把一个身材高大、红脸膛的男子介绍给我,他身上穿的晚礼服似乎叫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他就是纳尔逊医生。不过,这个名字当时对我没有任何意味。其他的客人都是伊莎贝尔的朋友,在介绍给我时,他们的名字都是刚刚到了我的耳朵里便被我忘掉了。姑娘们个个清纯、漂亮,男士们个个年轻、强健。他们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其中的一个男孩,因为他有十分高大的身材和健壮的体魄。他一副宽宽的肩膀,一定有一米九高。伊莎贝尔今天显得格外好看,她穿着白丝绸衣服和膝以下狭窄的长裙,正好遮住了她稍显粗的腿;领口较低的上衣烘托出她丰满的乳房;她裸着的胳膊也略微显胖,可她的脖颈很美。她兴高采烈,动人的眸子里闪着光芒。毋庸置疑,她是个非常漂亮、年轻和可爱的女子,可看得出来,如果不当心,她就会胖得过了头。
吃晚饭时,我发现自己坐在了布拉德雷太太和一个腼腆、不爱说话的女孩中间,她看上去似乎比别的女孩年纪更轻。为彼此显得融洽些,布拉德雷太太向我介绍说,这位姑娘的祖父母就住在麻汾,她和伊莎贝尔从前是同学。她的名字(我只听到人们这么称呼她)叫索菲。饭桌上打趣笑噱不断,每个人都亮着嗓门说话。他们之间似乎相当熟悉。在布拉德雷太太不同我说话时,我试着跟邻座的这位姑娘搭讪,可不甚成功。她比其他在座的女孩都更为沉静。她人并不漂亮,可脸长得很有趣,鼻尖那里有点儿上翘,嘴挺大的,一双蓝绿色的眼睛,黄褐色的头发被简单地束在一起。她长得很瘦,胸脯和男孩子的一样扁平。听到别人开的玩笑,她也在笑,不过却显得有点儿勉强,让你觉得她并不像她装出来的那么感兴趣。我猜测,她也是想尽量表现得好一些。我弄不明白她是有点儿笨,还是太害羞了。我试着谈了几个话题,都不成,因为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于是我请她给我介绍介绍在座的客人。
“哦,你知道纳尔逊医生的,”她说,指着坐在布拉德雷太太正对面的那位中年男子,“他是拉里的监护人。是麻汾的医生。他脑子很聪明,发明了不少飞机上的零件,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使用。不做事的时候,他就喝酒。”
在她讲话时,她淡蓝色的眸子里闪着光,这让我觉得,她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么呆板。她继续给我介绍着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亲是谁,说到男士,还会顺便提到他们所上的大学、所从事的工作。有些话平淡得很,比如说:
“她很温柔可爱啦。”或者,“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啦。”等等。
“那个长着浓浓眉毛的大个子是谁?”
“哦,他叫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麻汾的湖滨道上买下一座豪宅,是我们这一带的百万富翁。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他叫我们的脸上也觉得有光。马图林、霍布斯、雷纳、斯密斯等,都是芝加哥的富人,马图林是芝加哥最有钱的商人之一,格雷是他唯一的儿子。”
她说出这一串名字时,用的是一种愉悦嘲弄的口吻,我不由得用诘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她察觉到了,脸红起来。
“多跟我说说马图林先生。”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很富有。到处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给麻汾人新建了一座教堂,为芝加哥大学捐助了一百万。”
“他的儿子长得不错。”
“是挺好看的。你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祖父曾是爱尔兰的一个水手,祖母是瑞典人,曾在饭店里做服务员。”
其实,格雷·马图林谈不上英俊,只能说长得不普通罢了。他一副粗犷的面容,一个短而扁的鼻子,富于肉欲感的嘴唇,一张爱尔兰人的红红的脸膛;浓密乌黑的头发又光亮又柔顺,两道浓眉下面是一双格外清澈、湛蓝的眼睛。虽然长得人高马大,但肢体、五官的比例却很匀称,脱掉衣服,一定是个阳刚健美的男性胴体。他看上去浑身都是力量。他的男子气概给人印象深刻。他使坐在他旁边的拉里——尽管只比格雷矮八九厘米——显得文弱多了。
“许多人都喜欢他,”我腼腆的邻座说,“我认识的好几个女孩都在拼死拼活地追他。只是她们都没有机会。”
“为什么没有?”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深深地迷恋上了伊莎贝尔,以至于不能自拔,而伊莎贝尔爱的是拉里。”
“有什么能阻止他插进来、把拉里挤出去呢?”
“拉里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就不好办啦。”
“是的,如果你也像格雷那么重朋友情谊的话。”
我拿不准她在告诉我这些话时是郑重其事的,还是在调侃。她的言谈举止显得彬彬有礼,一点儿也不冒失或莽撞,然而,我有个印象:她既不缺乏幽默,也不缺乏精明。我猜不出在跟我说话时,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我是永远探不出来的。她显然不太自信,我估摸着她可能是家里的独生女,平常总是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在一起。她身上有种谦恭、素静的品质,让人挺喜欢的;不过,如果我对她过的是一种孤寂生活的猜测是正确的话,我想她一定静静地观察过跟她生活在一起的长者,对他们都形成了自己既定的看法。我们这些成年人很少能够察觉到,年轻人给我们的评断会有多么犀利、多么深刻。我又一次望进她绿蓝色的眼睛里。
“你今年多大了?”我问。
“十七。”
“你平时爱看书吗?”我贸然地问。
可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布拉德雷太太为尽女主人的职责,跟我搭话了,等我回过神来,晚饭已经结束。年轻人一溜烟地走光了,我们剩下的四个人上楼来到客厅。
我很诧异自己今天也被邀请过来,因为在闲聊了一会儿后,他们开始谈起一件我觉得本该是他们私下里说的事情。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该出于谨慎起身离开呢,还是作为一个旁听者,也许会对他们有点儿用呢。他们讨论的问题是,拉里为什么会有不愿意工作的这种奇怪想法,由于马图林先生(刚才在这里吃饭的那个叫格雷的男孩的父亲)愿给拉里提供一个职位,这个议题就变得迫切起来。对拉里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人能干勤快,一段时间以后,拉里就可望挣到不少的钱。小格雷·马图林急切地想让他接受这份工作。
我记不起当时所有的谈话内容了,但要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拉里从法国回来后,纳尔逊医生,拉里的监护人,便建议他去大学读书,可他拒绝了。他刚参战归来,想休息一下,这很自然;他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曾两次负伤,尽管伤势不重。纳尔逊医生认为,他还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休养一段时间让他得以完全恢复,也好。可是,自从他退伍以后,他休息的日子开始是以星期计,后来就是以月计了,现在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他在部队上似乎表现不错,归来后在芝加哥也小有名气,所以好几个商界人士都愿意把他纳入麾下。他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可没有接受他们的美意。他并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他还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干什么。他跟伊莎贝尔订了婚。对此布拉德雷太太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从儿时起他们俩就形影不离,她知道伊莎贝尔爱着拉里。她也喜欢他,认为他能给伊莎贝尔幸福。
“伊莎贝尔的个性比拉里的强,她能给予他所缺少的东西。”
尽管他们两人都还非常年轻,布拉德雷太太却十分愿意让他们马上结婚,只要在婚前拉里能有份工作就行。拉里有一份自己的收入,可即使他的收入是现在的十倍,布拉德雷太太还是要坚持这一点。就我推测,她和艾略特从纳尔逊医生那里就是想要知道,究竟什么是拉里想要做的事。他们想让他利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拉里接受马图林先生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们也知道,拉里从来不怎么听我的话,”纳尔逊医生说,“就是在小的时候,他也是独断独行的。”
“我知道。都是你把他给惯坏了。他能有他现在的出息,也算是个奇迹了。”
酒喝得已经有点儿多了的纳尔逊医生,有点儿不悦地看了布拉德雷太太一眼。他已发红的面庞变得更红了。
“我一直很忙。我有自己的事情需要照料。我收留他,是因为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的父亲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小就不好管教。”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布拉德雷太太有些生气地说,“拉里的性情是那么温和。”
“拿一个这样的孩子你能有什么办法?他从不跟你争辩,可一味地我行我素,等你气急了的时候,他只会跟你说声对不起,叫你火冒三丈。如若他是我的儿子,我可以揍他。对世上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的孩子——而且他的父亲之所以将他留给了我,也是因为他相信我会对他好——我怎能下得了手打他。”
“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艾略特有些焦躁地说,“目前的情况是:他游荡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现在便有个机会,他能获得一个职位,眼看可以赚很多钱,如果他还想娶伊莎贝尔的话,他就必须接受这个位置。”
“他要懂得,在当今这个世界,”布拉德雷太太插进来说,“一个人必须要工作。他现在已恢复得很好,十分强壮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些从战场上回来的人一蹶不振,再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他们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社区的累赘。”
这时,我说了一句。
“他拒绝那些人给他找的事时,可给出了什么理由?”
“没有。只是说这些工作他都不喜欢。”
“他自己有想要做的事吗?”
“明摆着没有。”
纳尔逊医生又端起一杯柠檬威士忌。他满满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他的两个朋友。
“你们想听听我的看法吗?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评断人性的行家,不过,不管怎么说,通过三十多年的行医实践,我对人性还是有些了解的。战争对拉里造成了影响。从战争中归来的他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不仅仅是他增长了几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了他。”
“什么事情?”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对其战争的经历只字不提。”纳尔逊医生转过身来问布拉德雷太太,“他跟你说过什么吗,路易莎?”
她摇了摇头。
“没有。他刚回来时,我们也曾试着想让他讲些他作战的经历,可他总是那样笑一笑,说实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他甚至也没有告诉过伊莎贝尔。她左缠右磨,也没有从他那里套出一个字。”
谈话就这样没有什么结果地进行着,少顷,纳尔逊医生看了一下手表说,他得走了。我准备和他一起离开,可艾略特执意让我再待一会儿。纳尔逊医生走后,布拉德雷太太对我抱歉地说,不该用他们的家事来叨扰我,她担心我早就觉得烦了。
“可你也看到了,这件事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她结束道。
“毛姆先生是那种做事十分谨慎的人,路易莎;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我觉得纳尔逊和拉里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路易莎和我都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告诉他。”
“艾略特!”
“你已经跟毛姆先生讲了不少,不妨把其余的也告诉他吧。我不知道刚才在饭桌上你是否留意到了格雷·马图林?”
“他那么大的块头,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他。”
“他是伊莎贝尔的一个追求者。拉里在国外参战的这段时间,他对伊莎贝尔殷勤有加。她也喜欢他。如果仗再打上几年,她很可能就嫁给他了。他向她求婚。她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想,她是在等拉里回来,再作定夺。”
“他为什么没有去参战?”
“他踢足球时跑得过猛,影响到了心脏。损伤并不要紧,可陆军没有要他。等拉里一回来,他就没有了机会。伊莎贝尔毅然甩掉了他。”
对此,我不知道艾略特想让我表明什么样的态度,于是我没有吱声。艾略特继续说着。他一表的人才,纯正的牛津口音,再没有谁能比他更像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了。
“当然啦,拉里是个不错的男孩,他偷着去参加空军这件事也足够有戏剧性,不过,我看人还是很准的……”他做出一个颇有意味的笑容,在我面前唯一一次隐约提到他是靠做古董生意挣到的钱。“不然的话,我此刻哪能有一笔数额可观的金边股票呢
 。我对拉里的看法是,他这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没有钱,没有地位。而格雷·马图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是爱尔兰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的后代。他祖上有一位做主教的,有一个剧作家和几位著名的学者和军人。”
。我对拉里的看法是,他这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没有钱,没有地位。而格雷·马图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是爱尔兰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的后代。他祖上有一位做主教的,有一个剧作家和几位著名的学者和军人。”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它们并不难,”他不经意地回答说,“我有天在俱乐部里翻阅《美国名人字典》,碰巧看到了这个姓氏。”
刚才吃饭时,我的邻座告诉我格雷的祖父是爱尔兰水手,祖母是一家瑞典饭店里跑堂的,不过,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把刚才听到的话讲出来。艾略特继续说着。
“我们认识亨利·马图林好多年了。他人好,而且非常富有。他的儿子格雷已进入芝加哥最好的一家经纪人商号。他胜利在望。他想娶伊莎贝尔,不能否认,站在伊莎贝尔的立场上看,这将是一桩十分般配的婚姻。我是十二分地赞同,我知道路易莎也赞成。”
“你离开美国的时间太长啦,艾略特,”布拉德雷太太干涩地笑了笑说,“你已经忘记了,在这个国家,姑娘们结婚,可不管她们的母亲和舅舅是否赞同。”
“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路易莎,”艾略特尖刻地说,“以我三十年的经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凡是适当考虑到地位、财富和双方境况的婚姻,都优于只为爱情的婚姻。在法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度,伊莎贝尔会毫不犹豫地嫁给格雷;然后,过上一年半载,如若她想,她可以将拉里作为她的情人,而格雷则可以置上一所豪华的寓所,养上一个漂亮的女明星,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
布拉德雷太太并不傻,她用狡黠和饶有兴味的神情看着她的兄弟。
“有一个对此不利的因素,艾略特,纽约的剧团在芝加哥演出的时间并不长,格雷只能指望他的情人在他豪华的寓所里稍作停留。这肯定对大家都不是很方便。”
艾略特笑了一笑。
“格雷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上一个经纪人的位置。毕竟,如果你必须在美国生活,除了纽约,住在其他的任何地方,我都觉得没有意义。”
之后,我很快就离开了,不过,在我临走前,也不知为什么,艾略特又邀我跟他和马图林父子一起吃顿午饭。
“亨利是美国最为典型的生意人,”他说,“我想你应该认识他。许多年来,他一直替我们经管着我们的投资。”
我并不是特别地想去,可又没有理由拒绝,于是说我乐意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