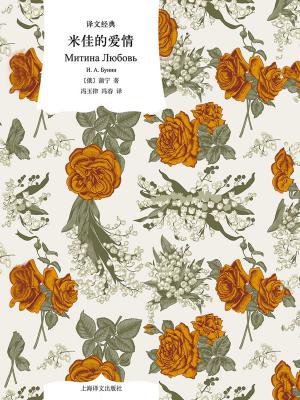在庄园里


天空中久久地燃烧着胭脂色的晚霞。一大片平坦的庄稼地上空交织着难以捉摸的光亮和难以捉摸的昏暗。村子里也渐渐变黑了,只有牧场上几所农舍的小窗户还闪耀着古铜色的反光。夜晚安宁而又谧静。人们赶着牲口从田头回来,在农舍前的石头上进了晚餐,渐渐静息了……没有歌声,也没有孩子的叫嚷……
一切都沉浸在傍晚的思绪之中。卡皮通·伊凡内奇坐在打开的窗户边,也陷入了沉思。
他的庄园坐落在山上;长着洋槐和丁香树的小花园已经荒芜,丛生着牛蒡和艾草,一直延伸到下方的谷地。从窗内透过灌木丛可以望得很远,很远。
田野缄默无声,躺在一片模模糊糊的昏暗里。空气干燥而又温暖。天空中的繁星幽幽地闪烁着神秘的光。只有纺织娘在窗外的艾草丛里不知疲倦地嘶噪着,而从草原上不时还传来一两声鹌鹑清晰的鸣叫。
卡皮通·伊凡内奇像通常那样,总是一个人。
他似乎命定要单身一人过日子。他的母亲和父亲是非常贫穷的小地主,投靠在诺盖斯基公爵的门下,在他不到一岁时便双双过世。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精神失常的姑妈——一个老姑娘的家里,以及世袭兵学校里度过的。在青年时代,他写过诗歌,模仿杰利维格和柯尔卓夫
 的风格。他在所写的爱情诗里把心中的“她”称为瓦莲金娜,而实际上,她叫阿纽塔,是一位在军需机关任职的官员的女儿,但他并没有赢得姑娘的芳心。
的风格。他在所写的爱情诗里把心中的“她”称为瓦莲金娜,而实际上,她叫阿纽塔,是一位在军需机关任职的官员的女儿,但他并没有赢得姑娘的芳心。
他的名字听起来像个“管家”,长得貌不惊人;皮肤黝黑,身材又高又瘦,照朋友们的说法,他活像一个神学校的学生,尽管在那时候,他靠着公爵的说情已经当上了军官(难怪人们说,公爵是卡皮通·伊凡内奇的生父)。后来,他继承了姑妈的领地,便退了役。他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马尔林斯基
 的某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是毕巧林,把头发理成最时髦的“波尔卡式
的某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是毕巧林,把头发理成最时髦的“波尔卡式
 ”……可是,这一切全不管用。“瓦莲金娜”到女伴家去做客,随后便嫁了人。而他则把诗作锁在小柜里,“至死”也不去开启。
”……可是,这一切全不管用。“瓦莲金娜”到女伴家去做客,随后便嫁了人。而他则把诗作锁在小柜里,“至死”也不去开启。
他当起家来,还想到刚刚开始办公的地方自治局去谋差使,可是他在自治局里不走运:有一次,首席贵族在贵族俱乐部茶点部边吃东西边说,卡皮通·伊凡内奇“心地挺好,不过是个幻想家……一个老派的幻想家……一个有点过时的角色”。卡皮通·伊凡内奇同邻村的小地主们广有交往,并且迷恋起打猎来,把猎犬贾尔梅当成不可替代的朋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年岁渐渐增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地主,穿起了“短上衣”,留着长长的黑胡须;他甚至忘了考虑自己的外表,并且看来也不知道,他那黝黑而略带麻斑的脸显得沉静而又和善,看上去还是挺动人的……
今天,他的心情很忧郁。曾在卡皮通·伊凡内奇这里当过女仆的信徒阿加菲娅一清早就拐过来,顺便对他说:
“老爷,您还记得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吗?”
吗?”
“记得。”卡皮通·伊凡内奇说。
“她去世啦。在大斋期下葬的。”
此后,有整整一天,卡皮通·伊凡内奇都在莫名其妙地微笑。而晚上……晚上是多么寂静和忧伤啊!
卡皮通·伊凡内奇没有吃晚饭,也不像平常那样早早地上床睡觉。他用很冲的黑色烟叶卷了一支粗大的卷烟,盘起一条腿,一直坐在窗边。
他真想到什么地方去走走。作为一个惯于平心静气地进行周密思考的人,他自问了一下:“到什么地方去呢?”难道去捉鹌鹑?可是晚霞已经消失,再说也无人做伴。谢苗今天去值夜了……何况,抓来鹌鹑又有什么用处!
他连声叹气,一边轻轻地挠着好久没有刮过胡子的下巴。
真的,人生是多么短促和可怜!他还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伙子的时候离现在才多久呢?世袭兵学校,幸好现在再也不会有了!忍饥,受冻,一次次地往姑妈那儿跑……那也算是个亲人!他牢记着姑妈的模样,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姑娘,长着干枯的黑头发,外加一双精神错乱的眼睛;据说,她是由于不幸的爱情而发了疯的。他还记得,她总是按照贵族女子中学的老习惯,反反复复地背诵法国的寓言,翻起白眼,一本正经地做出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还记得那首奥金斯基
 的“波洛涅兹”舞曲……这首曲子听起来热情洋溢,非同一般,因为老姑娘是怀着疯狂的激情来弹奏它的……唉,这首“波洛涅兹”啊!还有心目中的那个“她”也弹奏过……
的“波洛涅兹”舞曲……这首曲子听起来热情洋溢,非同一般,因为老姑娘是怀着疯狂的激情来弹奏它的……唉,这首“波洛涅兹”啊!还有心目中的那个“她”也弹奏过……
天空中的繁星幽幽地闪着光,显得那么神秘;纺织娘单调地嘶噪着,这种絮絮低语既令人烦躁,又催人入眠……大厅里有一架古老的钢琴。那里的窗子打开着……要是此时她像幽灵一般轻盈地走进来,弹起钢琴,触动那些反响强烈的琴键,那该有多好啊!然后,他们一起出了屋子,肩并肩地走在田间小路上,在黑麦田之间,一直向西,朝向远处透出亮光的地方……
卡皮通·伊凡内奇回过神来,笑了一笑。
“真是——想入——非非……”他拖着长音大声说。
纺织娘的嘶噪声响彻寂静的夜空,从花园里飘来了一股牛蒡草、高大的苍白色“圆叶当归”草和荨麻的气息。这种气息使他想起当年他从城里回家时心里甜蜜地思念着她,用幸福的憧憬欺骗自己的那些夜晚。
他慢慢地登上山去,村子里已不见一点灯火。辽阔的星空下,一切都在沉睡。四月的夜晚昏暗而又暖和;花园里的稠李树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池塘里隐约响起一阵阵蛙鸣,令人昏昏欲睡,这种音乐同早春的氛围是多么协调啊……那时,他在花园的窝棚里,躺在干草上,好长时间都无法入睡!连续几个小时看着一盏盏灯火在远处谷地的乳白色雾气中闪耀明灭;若是从那边被人遗忘的池塘里偶尔传来一声鹭鸟的啼鸣,这叫声会使人觉得神秘莫测,黑糊糊的林荫道也是神秘莫测……而在朝霞将升之际,花园里一阵湿润的清风扑面吹来,他张开眼睛,透过半已敞开的窝棚顶,发现一颗颗清纯的晨星正在朝他眨眼……
卡皮通·伊凡内奇站起身来,往屋子那边走去。他在各个房间里转悠着,脚步引起了回声,有几处地板下陷,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屋子造了有八十年啦!”卡皮通·伊凡内奇想,“今秋该叫木匠来修一修,要不,到冬天会冷得叫人受不了的!”
他在大厅里踱着方步,心里似乎感到不大自在。个子又高又瘦,稍稍有点佝偻,足蹬一双长筒旧皮靴,敞开的短外衣露出细棉布竖领衬衫,他就这副样子在大厅里打转,扬起眉毛摇着头,嘴里哼着“波洛涅兹”舞曲。他仿佛在观察自己的步态和体形,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孤零零地游逛着,那个人满怀着忧愁,那个人可怜得要命……他拿起便帽,便走出了家门。
户外要明亮一点。村子那头渐渐熄灭的霞光在院子里留下了些许余晖。
“米哈伊尔!”卡皮通·伊凡内奇轻声召唤着老牧人,但没有人回应。米哈伊尔“进屋去换衣服”了。
他想找点事干干,便穿过院子往牲口棚走去,看看米季卡是不是给母牛割了足够的草。不过,卡皮通·伊凡内奇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别的事情,他只是在牲口棚边站了片刻。
“米季卡!”他招呼了一声。
又是谁也没有回应。只听到大门后边有头母牛沉重地喘了口气,几只母鸡在栖木上扑打着翅膀,忙乱了起来。
“我要找他们干什么?”卡皮通·伊凡内奇想了一想,便不慌不忙地走到马车棚的后边,从那里的斜坡上延伸着黑麦田。他窸窸窣窣地穿过茂密的荨麻丛,点了支烟,坐了下来。
下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横亘在朦朦胧胧的昏暗之中。从斜坡上可以远远地望见四周的土地,它们静悄悄地沉浸在夜色里。
“我就像一只鹰鸮似的坐在土墩上,”卡皮通·伊凡内奇暗自思忖,“人家会说,这老头儿没事干啦!”
“难道是真的吗?我成了个老头儿?”他继续思忖着,“不久就要死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已经死了……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往事都到哪儿去了呢?”
他久久地眺望着远方的田野,久久地倾听着晚间寂静中传来的声响……
“怎么会这样呢?”他大声地说道,“一切都是照常,太阳照常落山,庄稼汉们照常犁头朝天地背着木犁从田头回来……第二天干活时照常满天霞光,而我却什么也看不到了,不光是看不到,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啦!即使再过一千年,我也永远不会在这个世上出现,永远不会再来到这里,坐到这个土墩上!我会在哪里呢?”
他弓起背,闭上双眼,用左手轻轻地拉着已经变得花白的黑胡须,坐着,摇晃着身子……
多少年来总以为在将来,在前边会有什么重大的、首要的事情……他曾经是个小男孩,曾经年轻过……后来……在一个大热天驾起轻便马车沿着大路疾驰,去参加选举!——卡皮通·伊凡内奇对自己的联翩浮想禁不住笑了起来……
但是,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一切均已了结;七十岁,八十岁……再往后连计算也没了必要!那么,生命到底是漫长还是短促的呢?
“漫长的!”卡皮通·伊凡内奇想,“对,毕竟还是漫长的!”
在黑沉沉的天空中,有一颗星星闪烁了一下,陨落下来。他抬起老年人忧愁的双眼,久久地仰望着天空。面对深邃、广阔、缀满繁星的苍穹,心头似乎轻松了一点。“好吧,那有什么大不了的!静静地度过一生,又静静地死去,就像这棵树上的叶子,到时候便要枯萎、脱落……”此刻,透过朦胧的暮霭已经很难看清田野的轮廓。夜色渐浓,天空中闪耀的星星也似乎升高了。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鹌鹑的啼叫也显得格外清晰。草地上送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他轻松、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气。心里深切地感到,他自己同这个无声的大自然是有着多么紧密的血肉联系啊!
一八九二年
冯玉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