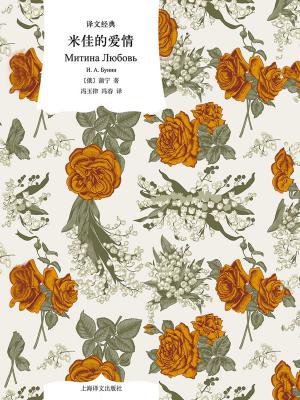在异乡

车站上不像平时那样忙乱,因为正逢复活节
 前夕。当九点钟那趟快车过去之后,所有人都急急忙忙地把刻不容缓的事情办完,以便早一点赶回住所,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轻轻松松地待在家里过节,即便在短时间里摆脱一下琐事,休息一下也好。
前夕。当九点钟那趟快车过去之后,所有人都急急忙忙地把刻不容缓的事情办完,以便早一点赶回住所,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轻轻松松地待在家里过节,即便在短时间里摆脱一下琐事,休息一下也好。
半明不暗的三等候车室里平时拥挤不堪,人声嘈杂,空气浑浊闷热,但此时却显得空荡荡的,还经过了一番收拾。从敞开的窗户和门洞里透进一股南方夜晚清新的气息。屋角有几支蜡烛稍稍照亮了读经台和金灿灿的圣像,圣像中央显露出了救世主那张忧郁发暗的面容。用红色玻璃罩起的长明灯在圣像面前摇晃着,一道道或明或暗的光线在圣像的金箔衣饰上游移不定……
从闹饥荒的省份路过此地的庄稼汉们无处可走,也无心过节。他们聚坐在长长的月台一端的暗处。
他们觉得自己远离故乡,落到陌生的人群中,处在陌生的天空下。有生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被迫到社会“底层”,到远方去挣钱糊口。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害怕,甚至面对搬运工们都不好意思地急忙把皱巴巴的帽子摘下来。在苦恼不堪地等了两天之后,那个身体虚弱、神态高傲的车站副站长总算走到他们跟前(此人已经在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个外号——“小公鸡”),并且声色俱厉地宣布,什么时候,由哪一列货车把他们拉到哈尔齐斯克省。现在,他们百无聊赖,只好整天躺着睡觉。
飘来了一大片乌云。时而吹来一阵和风,送来了清香,那是萌发新芽的白杨树的香气。从附近的池塘里传来呱呱蛙鸣,犹如幸灾乐祸的笑声,分秒不停。这种鸣叫就像所有持续不断的声音一样,不会打破寂静。右边还稍稍闪现出落日的余晖,铁轨便是朝那儿延伸而去的。左边却已经笼罩着一片深蓝色的暮霭。一盏圆盘形的灯挂在空中,好像一颗苍白泛绿的孤独的星星。从那边,从陌生的草原地带,夜色正渐渐逼近……
“唉,看来火车是不会马上来的!”有个人轻声说道,他半躺在车站的水桶边,拖着长音打了个哈欠。
“办公事呗,”另一个人接茬儿说,“总是不会快的。现在还不到七点呢。”
“说不定快到八点啦。”第三个人插了一句。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只有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哎,真无聊?哎——呀——呀……”他打着哈欠,模仿第一个说话的人,“伙计们,注意着,说不定汽笛就叫起来了!”
“基里尔,你叫大家留点神,”第一个人郑重地说,还一本正经地吩咐坐在身边的那一个:“帕尔梅内奇,去看看钟吧,你是识字的。”
帕尔梅内奇用温和的口吻有气无力地回答:
“伙计,我认不清这儿的钟,老是要搞错。有整整三根针哩。”
“哎呀,难道不是一码事吗?”基里尔嘲笑地说,“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都一样……”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乌云聚积在天空,暖和的夜晚用黑沉沉的帘幕把一切都悄悄地裹了起来。老头儿点起烟斗,用手指按了下燃红的烟草,一时间贪婪地吸着,只见火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他那士兵式的白胡子和粗呢大衣的领口。刹那间,还可以在黑暗中看到盖在基里尔腹部的那件白衬衫,以及其他两位老农身穿的粗糙破旧的短皮袄。然后,他把烟斗弄熄了,喘了几口气,朝左边他的侄子那儿瞟了一眼。那人正在打盹,细长的双脚裹在白色的粗呢包脚布里,一动不动地搁在地上。从他瘦骨嶙峋的身材来看,这还完全是一个孩子,却已经过早地忙于干活,弄得劳累不堪。
“费奥多尔,在睡觉吗?”老头儿悄悄地叫了他一声。
“没——有。”那人用嘶哑的嗓音回答。
老头儿亲切地朝他俯下身去,轻声笑着问道:
“是不是感到烦闷啦?”
隔了一会儿,才听到答话:
“我有什么可烦闷的?”
“哎呀,你说出来吧,别害怕。”
“我本来就不害怕。”
“这就对啦。我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费奥多尔不吭声。老头儿朝他瘦削的双肩瞅了一眼,然后默默地转过脸去。
日落时分天色已经变黑了。衬着夜空的背景,勉强才能分辨出车站屋顶的轮廓。在天空和黑茫茫的大地相接的地方,可以看到许多绿色、蓝色和红色的灯光在交相辉映,闪烁不停。一列蒸汽机车小心翼翼地从月台边驶过,轮子咔嚓咔嚓地响着,烧旺的炉子那红色的反光把月台也照亮了。炉子边,犹如在地狱的一个狭小角落里一般,有一些黑魆魆的人在蠕动。接着,一切又都沉浸在黑暗之中。庄稼汉们好长时间都听到蒸汽机车在旁边的什么地方咝咝地喷着热气。
随后,从远处传来一阵汽笛声,好像有谁在带着鼻音号叫一般。从黑暗里,从五颜六色的灯光中分离出了一个长着火眼金睛的三角形的东西。它变得越来越亮,慢慢地靠近过来,后面拖着长长的,长得不见尽头的一列货车;它越走越慢,终于停了下来,没了声息。过了一分钟,不知是什么东西尖叫了一声,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车厢一抖动,往后退了一下,又停了下来。有谁在高声喊叫,但又住了口。看不清楚是什么人手提着一盏灯,一圈光环摇摇晃晃地在车厢壁下方的地面上移动。
“三十四。”有个庄稼汉说。
“是谁?是车厢吗?看来还要多一点。”
“也许,还要多……”
费奥多尔用臂肘支撑着身子,久久地观察着蒸汽机车那巨大的,里面给隐约照亮的黑色形体,听到机车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作响,又渐渐静息下来。然后,机车脱离了后面的货车车厢,轻松地猛喘了一口气,驶到黑暗中去,用断断续续的汽笛声要人们给它让路……这里没有节日的迹象,一点也没有!
“我以为,火车在节日是不开的哩。”费奥多尔说。
“哪能不开哩!它们是不能不开的……”
有人不大有把握地推测说,大概就是这一趟车要把他们运走。在这样的夜晚,坐在黑洞洞的货车里可真难受。不过反正都一样,但求能把他们运走就好!
老头儿讲起哈尔齐斯克省的情况。但是,今后会怎么样,大家一无所知:哈尔齐斯克省在哪里?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到达目的地;在那边干什么活;再说,到底还有没有活干?要是碰到几个老乡,他们给你谋个好差使那才行呢!否则,大概又要坐在什么地方,叫人等得心烦意乱,只好喝着车站木桶里的温水啃啃面包干。大家心里再次充溢着忧郁、惶惑。甚至连基里尔也翻动身子,不安地挠着痒,坐了起来,低着头……
“干吗老是待在这里呢?”有人迟疑不决地说,“去城里走走也好嘛。离这里一共才四俄里路……”
“要是他们突然吩咐上车,那怎么办?”基里尔阴沉沉地回答,“错过了这趟车,你就得在这儿再坐上十天。”
“该去问问吧……”
“去问问?问谁?”
“去问站长呗……”
“真的,好像该去问问……”
“可是,站长此刻好像不在车站上……”
“那么,总有人替代他的……”
“办公事呗,在这里也是那副样子。”基里尔依然阴沉沉地说。
“人们都说,办公事是快不起来的……就连开斋都没有东西吃啦……”
“那就索性去要饭吧?”
大家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站周围的建筑物,那里的窗户内灯火通明,那里的每个家庭都在准备过节。
“唉,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老头儿叹了口气,坦诚地轻声说道,“我们简直成了那些鞑靼人啦。连教堂都没有去过一次!”
“老爷子,那你现在就像在唱诗班里那样吟唱吧……”
但老头儿没有听到这些温和而又忧伤的话语。他坐着,只管一门心思地嘟哝:
“愿天使降临人间,带着一切权柄……护佑众生,高唱赞歌,哈利路亚……”
他暂停片刻,两眼紧盯住前方,更自信地补充说:
“吾主复活,审判世人,如你监护万方百姓……”
大家都默不作声。
大家想的是同样的心思,怀着同样的忧愁,回忆起同样的往事。往年的此时,夜晚将临,教堂里也沉着而又繁忙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套上了马,庄稼汉们穿起了新靴子和松着腰带的衬衫,梳理好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稍作打扮的少女们和娘儿们不时地在农舍和板棚之间奔走。她们在房间里把甜面包和奶渣糕包到手帕中……然后,村子里便空无一人,变得静悄悄的……在黑茫茫的地平线上方,衬着日落时的天空,可以看到许多步行或者乘车到小镇去的人们的身影……小镇上,在教堂的附近,摸黑驶来的大车在吱吱呀呀地作响;教堂里点起了灯火……里面已经开始诵经,显得地方太小,有点拥挤,闻到一股蜡烛、新皮袄和印花布衣服的气味……而在教堂另一边的门前台阶和墓地上黑压压地聚集了一大堆人,听到七嘴八舌的谈话声……
突然,不知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响起了钟声。庄稼汉们顿时忙乱起来,一下子站起身子,光着脑袋画十字,朝东方鞠躬到地。
“费奥多尔!快起来!”老头儿焦急地嘟哝着说。
男孩一跃而起,用痉挛的动作快速地画了个十字。其他人也在忙碌着,急匆匆地把背包搭上肩头。
在车站的窗子里已经闪耀着蜡烛的火光。金灿灿的圣像同金灿灿的烛光亮成一片。三等候车室里渐渐挤满了职员、工人。庄稼汉们站在月台上,拥在门口,不敢走进去。
一位年轻的神父带着其他神职人员迅速进了屋子,穿起亮闪闪的圣衣,锦缎做的圣衣窸窣作响。他不知在说些什么,一边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挤满人群的半明不暗的大厅。已经点燃的蜡烛在轻轻地发出噼啪的声音,微风把烛火吹得摇曳不定。而从远处,从黑沉沉的夜空中传来了雄浑的钟声。
“救世主基督今已复活,天使凯歌响彻天宇……”神父用清脆响亮的男高音急急忙忙地诵道。
他刚说完这些话,人群便活跃起来,挪动身子,画起十字鞠着躬。大厅里也变得明亮一点,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每个人的脸上都闪耀着烛火温暖的反光。
只有那些庄稼汉们站在黑暗里。他们赶快跪倒在地,急匆匆地画着十字,一会儿久久地把额头贴住门槛,一会儿又抬起瘦削的脸,带着饥饿的眼神,忧郁而又贪婪地朝明亮的大厅深处,朝灯火和圣像张望。
“吾主复活,审判世人!”
一八九三年
冯玉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