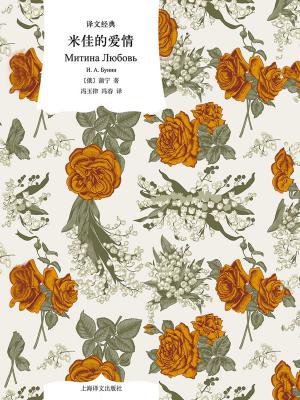祭文


草原上有个小村子,村子最靠边的农舍后面便是我们原先通往城里的道路,它渐渐淹没在一片黑麦田里。路边,在庄稼田那一片延伸到地平线的滚滚麦浪的起端,耸立着一棵树干洁白、枝叶繁茂的白桦树。路面上深深的车辙印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和黄白色的小花;白桦树在草原疾风的劲吹下变弯曲了,而在其疏落暗淡的树荫下,很早很早之前,便已经竖起一个式样古旧的灰白色十字架,带着三角形木顶,用以保护钉在下面的苏兹达尔圣母像。
一棵树耸立在金色的庄稼田里,树干洁白,树叶翠绿欲滴!当初,来到这个地方的第一个人,在他自己这十俄亩
 土地上竖起了带三角形木顶的十字架,召来神父,举行祓除仪式,祈求“至圣的圣母保佑”。自此之后,古老的圣像便日夜护卫着草原上这条古老的道路,并且不露形迹地赐福给辛勤劳动的农民。我们小时候对这个灰白色的十字架总是很害怕,从来不敢往它的木顶下方张望一下。只有那些燕子大胆地飞到那里,甚至就地筑起窝来。不过,我们对十字架还怀着崇敬之情,因为经常听到母亲在幽暗的秋夜悄声祈祷:
土地上竖起了带三角形木顶的十字架,召来神父,举行祓除仪式,祈求“至圣的圣母保佑”。自此之后,古老的圣像便日夜护卫着草原上这条古老的道路,并且不露形迹地赐福给辛勤劳动的农民。我们小时候对这个灰白色的十字架总是很害怕,从来不敢往它的木顶下方张望一下。只有那些燕子大胆地飞到那里,甚至就地筑起窝来。不过,我们对十字架还怀着崇敬之情,因为经常听到母亲在幽暗的秋夜悄声祈祷:
“至圣的圣母啊,保佑我们平安吧!”
我们那儿的秋天是明亮和静谧的,它来得那么平和而又安宁,似乎晴好的日子不会再有尽头。远处的景象变成柔和的蔚蓝色一片,天空也变得分外清朗,一碧如洗。那时候,可以看得清在草原上,在开阔无际的已收割的黄色原野上最远处的丘冈。秋天渐渐给白桦树换上了金色的衣装。白桦树挺高兴,却没有发觉,穿戴这身衣装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叶子一片片脱落,衣装也给卸了下来。最后,白桦树不得不光着身子站在金色的地毯上。她被秋天的魅力迷住了,感到很幸福,对其百依百顺,并且由于脚下枯叶的映衬而显得容光焕发。在阳光下泛着虹彩的蛛网在她的身旁飘飞,又悄悄地落到干燥、刺人的已收割过的田地里……人们深情地为其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圣母的纺线”。
然而,一当秋天撕下温和可亲的面具时,日日夜夜便变得如此可怕。那时候,狂风无情地摇撼着白桦树赤裸的枝丫!农舍变得无精打采,就像雨天的母鸡一般。暮霭低低地弥漫在光秃秃的原野上。到了夜里,一双双狼眼睛会闪现在冷僻的地方。狼眼睛的后面常常隐藏着妖魔鬼怪;在这样的夜里,如果村外没有那个古老的带三角形木顶的十字架,那真是叫人胆战心寒。从十一月初到第二年四月,暴风雪持续不断,把田野、村庄、白桦树以及十字架通通埋进雪堆。有时,从穿堂往外朝田野望去,只见猛烈的旋风夹着飞雪在十字架的上方呼啸,从尖尖的雪堆上腾起阵阵烟雾,然后呻吟着掠过原野,在奔驰中把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的足迹全部掩盖起来。此时,迷路的行人在狂风暴雪中看到从雪堆中露出的十字架,便会满怀希望地画起了十字,因为知道天上的圣母正在看顾白雪皑皑的荒原,护佑着村庄,护佑着这一片过早地死寂的田野。
田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死寂,但草原上的人们是有耐心的。终于有一天,十字架开始从下沉的灰白色积雪中探身出来。高低不平,撒满牲口粪的道路渐渐解冻,飘来了三月暖和的浓雾。由于渗进雾气和雨水,农舍的屋顶变得黑乎乎的,并且在阴沉晦暗的天气冒出一阵阵轻烟……很快,浓雾就被阳光明媚的日子所取代了。整个雪原浸透了水,好像在融解似的,化成无数条颤动的小溪,在阳光下熠熠闪亮。草原在一两天里便换了新貌:田野的颜色变深,透出春天的气息,而在远处则环绕着一抹淡青。人们把已经关得有点麻木的牲口从厩棚里放出来;一个冬天下来变得有气无力的马儿和母牛在牧场溜达着,躺着,而寒鸦则飞到它们瘦瘦的背脊上,用喙揪下毛去筑巢。不过,迅速转暖的新春会提供丰富的饲料,牲口踩着暖和的露珠很快便养肥了!在晴朗的正午,已经有云雀在引吭高歌;由于风吹日晒,牧童的皮肤已经变得黝黑起来,土地也给烤干了。当春雨滋润大地,当第一声春雷将大地惊醒之后,上帝在满天繁星的宁静的夜里祝福庄稼和牧草茁壮生长,而对田野感到放心的古老的圣像则满怀柔情地从十字架的木顶下看顾着一切。在夜晚洁净的空气中洋溢着一股草木发出的淡淡的清香,草原上一片安宁,幽暗的村子里也是十分静谧,那里从报喜节
 起便不把灯火吹旺。晚霞时分,姑娘们同已经订婚的女伴告别的歌声也静息了下来。
起便不把灯火吹旺。晚霞时分,姑娘们同已经订婚的女伴告别的歌声也静息了下来。
然后,一切都迅速地发生变化。牧场变绿了,农舍前的柳树变绿了,白桦树也变绿了……在阴雨连绵中度过炎热的六月之后,花儿一齐开放,喜气洋洋的割草期开始了……我记得,夏日的风无忧无虑地轻扰着如丝一般发亮的白桦树叶,激起阵阵喧哗,并把纤细柔软的树枝吹得弯向一边,触到了麦穗;我记得,圣三节
 早晨的阳光是多么灿烂,那时甚至满脸胡子的庄稼汉,作为真正的俄罗斯人的子孙,也从硕大的白桦树冠底下探出脑袋,咧开嘴笑着;我记得圣灵降临节
早晨的阳光是多么灿烂,那时甚至满脸胡子的庄稼汉,作为真正的俄罗斯人的子孙,也从硕大的白桦树冠底下探出脑袋,咧开嘴笑着;我记得圣灵降临节
 那粗犷有力的歌声,那时我们在夕阳西沉之后赶往近处的橡树林里,熬起粥,将粥倒在瓦片上,安放到各个土丘,然后“祈求布谷鸟”充当仁慈的预言家;我记得彼得节
那粗犷有力的歌声,那时我们在夕阳西沉之后赶往近处的橡树林里,熬起粥,将粥倒在瓦片上,安放到各个土丘,然后“祈求布谷鸟”充当仁慈的预言家;我记得彼得节
 前“太阳的闪耀”,记得喜庆的颂歌和热闹的婚礼,记得在田野,在露天下面对庇护一切受苦受难者的仁慈圣母所做的感人祈祷……
前“太阳的闪耀”,记得喜庆的颂歌和热闹的婚礼,记得在田野,在露天下面对庇护一切受苦受难者的仁慈圣母所做的感人祈祷……
生活不会止步不前,旧事物渐渐消失,我们常常会怀着巨大的悲痛同其告别。不过,生活难道不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更新而变得美好的吗?童年时代过去了。我们禁不住要看一看比村子周围更远的地方。这种愿望非常强烈,因为乡村显得越来越凋敝,白桦树的叶子在春天已不再是那样翠绿和茂密,路边的十字架开始朽烂,人们耗尽了为圣母所庇护的土地的肥力;因为祸不单行,上天本身似乎也在对人动怒。燥热的狂风驱散了乌云,沿着道路盘旋,太阳无情地灼烤着庄稼和草地。干瘪的黑麦和燕麦还没有成熟便已经枯萎。看到它们令人心疼,因为没有比干瘪的黑麦田更凄凉、更可怜的画面。又轻又空的穗头在热风的吹拂下无可奈何地摇曳着,孤零零地簌簌细语!透过它们的细茎可以看到干裂的耕地,看到干枯的矢车菊……于是,银光闪闪的野生滨藜取代茂盛的庄稼,占据了古老的村际道路边的地盘,这是饥荒的征兆。乞丐和盲人越来越频繁地在村子里徘徊,唱着悲哀的歌。而村子在阳光的照耀下缄默无言,显得多么冷漠而又忧伤。
此时,圣母那温柔的面容被蒙上风沙,像是由于痛苦而变得黯然失色。岁月流逝,她似乎对这片土地的命运再也不加关切。于是,人们一个个地离开这里,沿着道路奔向城市,奔向遥远的西伯利亚。他们卖掉菲薄的家什,用木板钉死农舍的窗户,把马匹套在大车上,永远地离开家乡,去寻找幸福。村子里变得空荡荡的。
“无——人!”风刮遍全村,在道路上漫无目的地使劲卷起尘土,说道。
但是,白桦树像以往一样,没有搭腔。她轻轻地摇曳着树枝,又在打盹了。她已经知道,村里的牧场上已经长满高高的野草,家家户户的门槛边丛生着野芝麻,半已圮塌的屋顶上露出了银光闪闪的艾蒿。草原四周一片死寂,仅剩的十来间完整的农舍,从远处看去,就像游牧民族经过战斗或者瘟疫之后抛弃在原野上的帐篷。白桦树的树顶上竖着几根干枯的白色树枝,在她下方的带木顶的十字架也已经倾斜了。现在,在黄昏时分,当落日在黑茫茫的田野那头泛出些许红光时,只有饱经世故的白嘴鸦和乌鸦还在白桦树的枝头栖息……
于是,草原上出现了一批新人。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沿着道路从城里来到此地,并在村子边安置了下来。夜里,他们燃起篝火,驱走黑暗。他们的影子远远地落在村路上。拂晓时,他们走到田野,并用长长的钻孔器钻探土地。村子周围堆满了黑土,好像一个个坟丘。人们毫不怜悯地践踏未经耕种而自行长出的稀稀落落的黑麦,毫不怜悯地将它们掩在土里,因为他们要寻找新的幸福源泉,在地下的深处寻找,那里埋藏着与未来攸关的财宝……
矿石!也许,过不久烟囱将在这里吐出浓烟,旧的村路上将铺设起刚劲有力的铁道,在原是荒村的地方矗立起一座城市。而曾经在此庇护过昔日生活的东西——那个已经倒在地下的灰白色十字架将会被所有人遗忘……不过,新来的人们将依靠什么来庇护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在热火朝天的、喧腾的劳动中祈求的是谁的祝福呢?
一九○○年
冯玉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