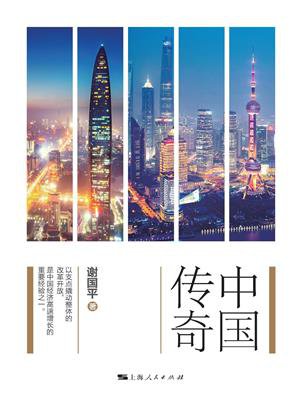第一章
“大逃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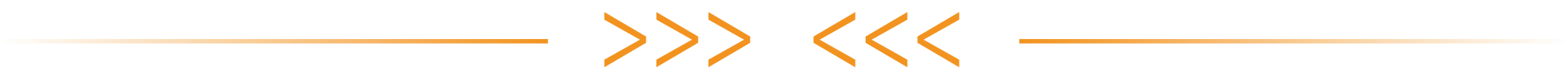
1984年6月30日,时为中国政局的掌舵人邓小平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大白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今天理解这句名言的内涵不难,但理解这句名言的背景并不容易。为什么邓小平要说这样一句话,并在日后反复强调?
1979年5月6日,发生在中国南方边陲小镇的“大逃港”事件是理解这一背景最生动、鲜活的故事。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偷渡逃港始终是一个让国人羞辱的话题,令人心酸。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全境解放,人们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欢迎解放军。深圳镇长陈虹激动地说:“深圳人民数十年来在国民党铁蹄下过的是苦难生活,每一个人都在期望早日得到光明。……深圳新生了,我们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建设新的深圳。”
次日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这样描述:“深圳已卷在狂欢的气氛中。”

确实,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动乱,中国人极度渴望和平的新生活。
可是没有多久,守卫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许多老百姓却要离开新生的深圳,逃向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51年1月21日,深港两地同时封锁边界,边界线上每50米建起一个8米高的岗亭。可是再严密的封锁也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在此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深圳边境出现过四次大规模偷渡。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边的水沟”,深圳顾名思义有水深的意思,广东人有以水为财的说法,有水就有财。据说,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下发将宝安县升格为市的通知,在市委常委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撤县改市后是叫宝安市还是叫深圳市,最后确定叫深圳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深圳带水。

但是那时的深圳,有水却没财!
对于广东地方领导来说,偷渡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偷渡。
1977年11月17日下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广州南湖宾馆,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的工作。
广东省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所面临的难题: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一个叫深圳的边境小镇,一波又一波的偷渡让地方领导和边防部队苦于应付。
汇报者一脸严肃地叹苦:宝安人逃港,连命都不要了,当地干部管不住,公安管不住,连边防部队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打断对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话让与会者震惊,不解地望着邓小平那深邃的目光,沉默了片刻,邓小平又补充道:“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

在场的都明白,偷渡的根本原因是两地贫富差距太大了。
1979年,宝安县领导带队下去调查,得到的数据让人无颜面对“社会主义好”:
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多元港币(折合人民币4300多元),两者差距悬殊!

这边穷,比不过香港,作为广东人刘波自然多少也知道一点,但是5年后,他去深圳的梧桐山,亲眼见到的场景让他震惊:山上不时可见到偷渡者的尸骨和骷髅!刘波长叹道:“广东再也找不出更荒凉的地方了!”
但那时没有谁敢怀疑政策上有问题。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如果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如果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听完汇报,邓小平离开广州,但留下了谜。
后来,广东的党史学者研究后发现:这次邓小平来,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之后发表了谈话,谈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策问题。他反复说到政策是关键,而且一再强调,政策不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在讲到农民养一口猪,需要奖励多少粮食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政策问题嘛,应该交给农民来讨论。……他还说逃港也是个政策问题,不是军队能不能管得了的问题。他谈的这些政策问题,跟此后他所谈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等,是一脉相承的。

其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深深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的政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同年,在安徽,刚刚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走访了农村后,也为中国农民如此贫穷而感到难过。
他来到了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在县内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拖儿带女的农民们乞讨外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寒风中冻得哆嗦。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还不以为然地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习惯。”
万里听了动怒了,用手敲打着桌子,高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那时,能够公开指责中央的政策有误,同样让人震惊。
作家张宏杰在解释安徽凤阳穷和尚、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造反的原因时写道:“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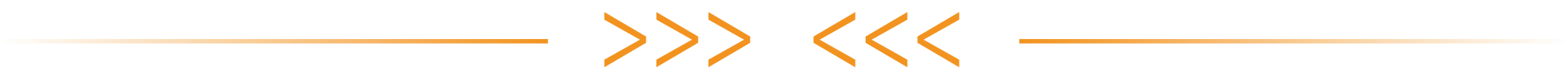
那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词组。尤其是到了60年代,整个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有了一种恐慌症。因为“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那么单干户、个体贩卖、包产到户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集市贸易、讲求利润、自主经营也属于“资本主义”。
比如当年在中国农村,农民养几只鸡,自留地里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在山区,让土特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让农民运进城里去销售是资本主义。更荒唐的是在广东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

那时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继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荒唐的“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理论达到顶峰。
曾有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老头,到深圳中英街对面中方辖区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老头得意地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这下子让革命群众警惕起来,把他抓起来,大会批斗。有人怒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老头老实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话音刚落,全场大笑。

荒谬在笑声中,但荒谬也在人们内心深处,人们说话行事时总是有着一根警戒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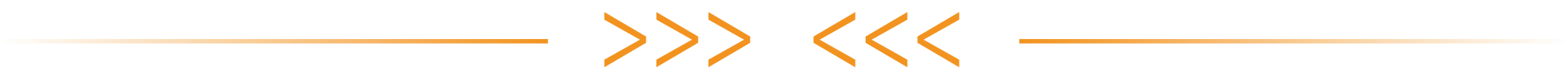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江西是中共革命根据地。1933年,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他被下浱到乐安县,之后又指定他到宁都的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监督劳动。那是一个贫困山村,年轻的邓小平开荒种地,但总是吃不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危秀英,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她在《女英自述》一书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而在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

30多年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发配”到江西。还好,在狂热的政治喧嚣中,邓小平远离政治中心,有了片刻的安宁。
在那里,65岁的邓小平,拖地板、生炉子、做饭,还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他每天与妻子一起往返于一条3里长的小路上下班,风雨无阻,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真切和直感地体会到了中国最底层人们的苦难生活,开始有了充裕的时间思考中国的贫穷问题。
女儿邓榕来看父亲,告诉他:“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什么生产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或许他又想起了当年“吃不饱,肚子好饿”的痛苦感受?
时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车间主任的陶端缙回忆,1971年6月,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到了江西,为了让瘫痪在床的邓朴方解闷,有一天,邓小平问他家里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学物理出身的高材生邓朴方帮助修理一下。
陶端缙面有难色地告诉邓小平:“不瞒你说,我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收入,要供养四个小孩,有的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有闲钱买收音机啊。”邓小平听后沉默了,久久不发一言。

邓小平习惯散步,在散步中思考。每天黄昏时分,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那栋灰色的小楼院子里,邓小平一圈圈地走着,夕阳将他的身影投在大地上,就像他脑中思索着的一个个问号和惊叹号,带着问号和惊叹号的思考沉重而深邃,穿透了历史和理论。
邓榕常常看到这一场景,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描述道:“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

邓小平妻子卓琳说,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认为:“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性质以及如何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一九七七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要进行的改革大方向。”

愤怒出诗人,危难出真知,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有这样的说法:“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而司马迁自己也正是遭受宫刑后,含垢忍辱发奋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邓小平本人也不否认是“文化大革命”促使他进行深深的反思。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在北京中南海采访了邓小平。《60分钟》是一档著名的访谈节目,迈克·华莱士曾经采访过世界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各界名流,并以其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于“审讯”的采访方式被观众所熟知。
华莱士问:“邓主任刚才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您和您家人的遭遇如何?”
邓小平回答:“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就是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说,“文革”最终彻底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借用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怎样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通衢大道,成为邓小平复出后所面临的难题。
这一年7月30日晚,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距开赛还有几分钟,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邓小平走上主席台,全场八万观众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体育场里的掌声,也是全中国人的掌声。
主席台上的邓小平神采奕奕,丝毫看不出三落三起的坎坷在他身上的烙印,苦难与折磨没有摧垮他的信念和意志。曾有一次,女儿邓榕问:“您在历史上受过几次‘左’的迫害呀?”老人家提高了声音:“三次啊!”还伸出三个指头晃动着。

其实,中国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邓小平起落的经历,这种经历也就更让人多一种敬佩和希望,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后能够给他们带来美好生活。
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中国,没有度过多少安宁时光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不断地被打乱,老百姓始终是那样贫穷,肚子吃不饱。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而据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多年调查采访得出的数据:
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
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这其中最悲惨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
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这场灾难时痛苦地写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显然,邓小平对于这一教训的反思,已经不是技术操作层面,而是从制度上的反思。复出后不久,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追问:
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而在一个个沉重的问号下更多的是职业革命家的历史责任,1978年,他曾在北方视察时向沿途省市党政军负责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这些话发自肺腑,那是他晚年最深沉的思考。
德国工运活动家、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在其所著《马克思传》中这样描述马克思:“正如他有一次率直的说过,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

邓小平也因为“文革”灾难,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百姓的苦难,可以说这也是他力推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动力。
在“打不倒的小个子”痛苦思考的同时,中华大地芸芸众生也在思考。此时,“文革”结束,冰雪开始融化,噩梦刚刚苏醒,人们心有余悸,但内心深处开始怀疑过去,怀疑“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那些荒唐的理论和概念,进而开始认真而务实地思索着怎样突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底线。
春天的故事就在怀疑和探索中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