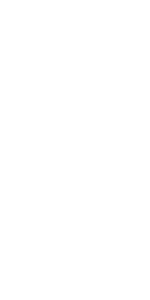
|
二、思想要求:肃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毕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犯重大错误也属正常。毛泽东对党在建党以来所犯的重大错误,都从哲学角度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毛泽东看来,右倾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这就是他们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们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就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主观主义。所以,从直接目的看,《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是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走过了一条十分艰难和曲折的道路,其中,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既源于敌强我弱的外因,而其内因,与党内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密不可分。《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在《实践论》的题解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也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写作。
《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也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写作。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毛泽东从理论根基、思想路线、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彻底清算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毛泽东从理论根基、思想路线、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彻底清算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什么是教条主义呢?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可见,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不会或不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一切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
可见,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不会或不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一切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倾向由来已久。按照周恩来1943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和陈独秀的土教条。到了王明时候的教条,则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加完备,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王明的教条主义时间最长,危害最大。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二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制定“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导致制定革命政策的主观化。
,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二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制定“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导致制定革命政策的主观化。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于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并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会议的几个决议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批评。”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立场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认为要同这种狭义的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会议的几个决议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批评。”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立场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认为要同这种狭义的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此后,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其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逐步加强。
此后,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其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逐步加强。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搬迁到中央苏区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这一年的9月,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也开始了。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围攻中央苏区。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虽然已发展到8万多人,但同国民党军队围攻的兵力相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相当严峻,但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两者兵力相比的一比十几来,还是稍稍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幻想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1934年5月12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6月13日,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其实,博古并不懂军事,他完全依靠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前线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中共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采纳,他本人也受到排斥。他在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那一套‘左’的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

历史已经证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排斥。李德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的:“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
 李德、博古等人对洋教条的迷信和对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和探索的排斥,由此可见一斑。他们的这种作派,在党内也长期有很大的市场。
李德、博古等人对洋教条的迷信和对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和探索的排斥,由此可见一斑。他们的这种作派,在党内也长期有很大的市场。
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相关人物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张闻天说,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博古也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国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豫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而陷于失败。
血的教训表明,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往往有更大的迷惑性、危害性。毛泽东曾经感叹:“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自我检讨,也承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就提出的。我那时(1931年)的感觉,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入偏向、离开原则,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今天才感到这句话是真理。就是说只凭原则、不详究实际情形去决定问题,将不会正确,将成为主观的东西,成为教条式的解决问题。”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自我检讨,也承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就提出的。我那时(1931年)的感觉,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入偏向、离开原则,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今天才感到这句话是真理。就是说只凭原则、不详究实际情形去决定问题,将不会正确,将成为主观的东西,成为教条式的解决问题。”
 实践出真知,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前行的路。
实践出真知,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前行的路。
中央红军历经重重险阻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也进入了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当时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高度加以解决的话,中国革命就不能顺利地前进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陕北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章能传递到那里,这就也使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事实上,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还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等重要论断。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稍后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军事路线。《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旨在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实质,从哲学上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抓住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范畴,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分析,从而深刻揭示和批判了教条主义所犯的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认识论错误,科学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育全党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而为共产党从根本上扭转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实,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之后,共产国际也逐步改变了教条主义式的领导方法。这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政策。会议决议指出,要由各国党的领导者“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用呆板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这一决议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在长征结束后又独立展开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也独立地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向开展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创造。《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这种独立研究条件下创造的成果。
这一决议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在长征结束后又独立展开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也独立地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向开展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创造。《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这种独立研究条件下创造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