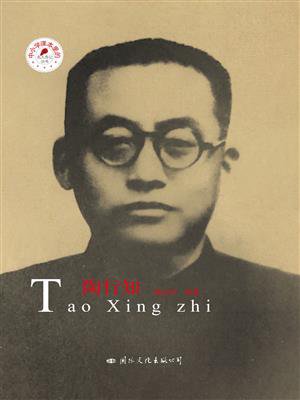以教育为终生事业
经过一年苦读,陶行知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他不想继续学政治了。美国教育发达、人才济济,给他深刻的感受。他认为美国科学发达、经济繁荣,原因在于教育发达。他想起教育落后的祖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更趋浓厚,最终决定以教育为救国、富国的终生事业。于是,陶行知开始改学教育学。
1915年9月,陶行知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科学。若将伊利诺伊大学比作一只大船,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一艘航母。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老牌的私立名校之一,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大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西面。
哥伦比亚建校时间比伊利诺伊大学早113年,最初取名为“纽约学院”,后被英王查理二世钦定校名为“王家学院”。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校名改作“哥伦比亚学院”。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学校已由哥伦比亚一所学院增为10所,校董事会遂将校名改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但直到1912年,新校名才经纽约州政府批准后正式付诸使用。
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胡适与陶行知同乡、同庚。胡适是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绩溪是歙县的邻县,本是从歙县划分出来的。陶行知母亲的故乡即是绩溪。
万里之外,两个老家只隔几十千米的有志青年成了同窗。虽然一个出身官宦,一个来自蓬门,但二人成了好友。他们俩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乃是以后的事了。
胡适是庚款第二届官费留学生,当陶行知还在南京汇文书院中学部读第二年的时候,胡适便漂洋过海了,他比陶行知早4年到的美国。他先进入纽约州伊萨卡市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农科,3个学期后忽然觉得所学近于屠龙之技,自己也毫无兴趣,于是转入该校文学院。
除了文学课程外,胡适还修习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和经济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而后又读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因平常四处演讲,耽误功课太多,校方停了他的奖学金。他便离开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投在杜威门下,而正好与陶行知同时进入哥大。
哥大的男生宿舍有两幢旧楼和一幢新楼。陶行知住在旧楼之一的哈特莱大楼1010室,胡适因为在康奈尔大学参加社会活动多,经济上比较宽裕,所以住在那幢新的佛纳大楼内。当时住在新楼里的还有宋子文和张奚若。旧楼里则有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和未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在陶行知修习的科目中,只有一门“教育史”贯穿了4个学期始终,指导教师为保罗·孟禄教授。是课程本需要这么长的学时,还是学生喜欢导师而对他的课爱不释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旷日持久的教与学当中,两人建立了友谊。
陶行知在海外除了得自费完成学业外,还得承担国内家中生活所必需的开支,经济非常困难。而且,陶行知虽然事先对哥大的生活费用有些思想准备,但入哥大之后发现,费用的高昂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才半年过去,入不敷出的窘况就出现了。
无奈之下,陶行知向当时的老师孟禄教授求助。孟禄教授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对这位刻苦的中国留学生也青睐有加,他及时地伸出援手,亲自出面帮助陶行知申请美国利文斯顿奖学金。在孟禄教授的指导下,陶行知写下申请书,递交给了院长罗素。最后,陶行知顺利地拿到了奖学金。
利文斯顿奖学金的顺利获得,不仅使陶行知得以从为生活来源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对他的学习自然也是一种鼓励,还有老师在他申请奖学金中的假以援手,也使他感到照照暖意。陶行知在这一学期内的课程突然升至6门,是他在哥大修课最多的一学期,看来其原因似乎并不难解释。
此前的陶行知,自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就一直是拮据的。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在一次中国学生夏令会上,与缪云台一见如故。其实他俩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同学,只是缪云台读的是矿冶学。可能是专业相差得远的缘故,两人同校却不相识。
陶行知与缪云台之所以相交,除了志趣相投外,还可能与彼此出身有关,因为两个家庭太相似了。小陶行知3岁的缪云台,生在云南昆明,祖父经营酱园,生产和销售酱油、酪、麻泊、各种酱菜等。与陶行知的祖父一样,其父亲也是长子,同样继承父业。
不同的是,缪父经营有方,因此家道较之陶家要殷实。缪云台就读于云南高等学堂,因辛亥革命的影响,未毕业学堂就解散了,转入留学预备班,由省以公费出国留学。先进入美国中部康萨斯州西南大学,一年后入伊利诺伊大学,又一年后入明尼苏达大学。
陶行知与缪云台相识时,缪云台已入明尼苏达学校,所以两人用书信保持友谊。缪云台见陶行知自费留学辛苦,便每月从自己80元生活费中,抽出10元寄给陶行知,前后长达一两年之久。
1917年的上半年,陶行知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毕业论文上,写到7月时,竟因为资料不足几乎搁笔了。因为论文一部分内容要以中国教育现状的数据作为论证,而需采用的数据有许多并未形成现成的文献,甚至数据根本未形成,尚需前往收集整理。
定论文选题时,陶行知不是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可一直以为总有办法解决,也曾托人在国内代为搜集,不料均未能奏效。时间已到了这个时候,他有点儿骑虎难下了。
恩师孟禄又一次出面帮忙,他想好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给时任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评审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哲学专业科学部部长伍德伯里奇博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道:
我建议为授予陶文濬博士学位安排一场考试,这是特殊情况。陶文濬已经完成了学术研究工作,正撰写题目已被认可的毕业论文,但须回中国搜集资料,因为论文主体的注释部分有赖于这些资料,否则论文无法完成。
鉴于陶文濬将从事中国政府教育工作,而难以返回美国,我建议,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先进行考试,待论文提交后,再行审定。建议考试日期定为8月2日星期四。
孟禄的意思是,让陶行知先参加答辩,等论文完成后,再授予学位。就这样,陶行知回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了一条尾巴。
有意思的是,已于6月份毕业回国的胡适离校时也留了这样一条尾巴;2年后毕业的陈鹤军在此也留了同样的一条尾巴。当然其中缘由各不相同,只说明在当时毕业而未获学位的情况并非个别。
留美3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没有波及美国,对小国也没有什么直接影响。这3年,陶行知很少过问政治,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头读书,以图学成报国。
1917年秋,陶行知终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了。太平洋的海景如故,他伫立在甲板上沐浴着海风,临海远眺,海上的颠簸并没有让他有丝毫的慌乱。他决心回国后与其他教育家合作,为祖国人民组织一个高效的公众教育体系,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