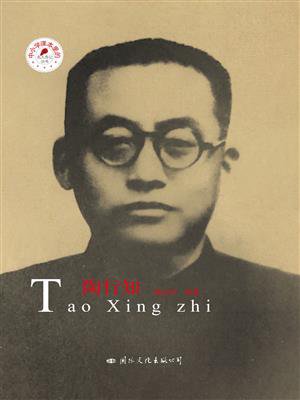从金陵大学毕业
陶行知与崇一同学章文美一起考入杭州的广济医学堂,学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晚清以来,一大批接受了西学的有志青年抱着“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愿,学习西医,以救苍黎。孙中山、鲁迅、陶行知走的都是这条路。尔后,他们又走了一条相同的路:
从医人到医国。
不同的只是各人选择的医国手段不同:
孙中山以政治,鲁迅以文学,陶行知以教育。
不过,和孙中山等有别的是,陶行知“弃”医并非是自觉的,而是由于校方的原因和自身倔强的个性。
广济医学堂也是教会学校。陶行知在校一直很用功,成绩优异,诸事顺遂。可面临实习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原来,校方有一条规定:
只有成为基督教徒的学生,才能享受免费实习两年的待遇。
陶行知对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反感,还笃信博爱精神,但却不愿入教。因此,他自然是无钱缴纳实习费的。校方的这条不合理规定,令他愤慨。为向这条傲慢的、有辱中国人的规定抗议,他愤而离开了广济医学堂。
陶行知离开广济医学堂,固然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傲骨,显示出民族自尊心,但他却因此失学,走投无路。由于在杭州举目无亲,他只得到苏州投靠表兄。但是,表兄自身都难以维持生活,两人只能靠典当衣物来维持半饱。
为寻找生路,陶行知来到上海。正当穷愁潦倒的时候,他在街头与恩师唐进贤邂逅。唐进贤在徽州任满后,辞去崇一校长之职。此刻,他向弟子再次伸出援助之手:介绍陶行知到南京投靠金陵大学。
六朝古都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秦淮河、夫子庙表面一片繁荣,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大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各种政治势力正在相互角逐,全国各地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和暴动,读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都是变法图强的新思潮。
对此,陶行知并没有置身事外,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书生。相反,他十分关注时局,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新知识,并广泛涉猎西学,探索和思考着救国救民的良方。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于1907年由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它分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在学制上,它分预科与本科:预科2年,本科4年。陶行知不负师望,当即考中预科。
1909年秋,陶行知进了金陵大学预科。他根底扎实,被免修了一些科目,提前一年结束了预科学习。1910年秋,他升入金大文科本科。他在学习上极为勤奋,进入本科后,以成绩优异而闻名全校。他的国文、法文成绩特优。对于数学,他具有天赋和浓厚的兴趣,攻读不懈,并且经常帮助同学解决数学难题。
在金陵大学的学习奠定了陶行知坚实的数学根底,训练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他一生的事业裨益匪浅。在以后的治学、工作中,他每每佐以数学方法,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在论文和演说方面的成功,和他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分不开的。
进入金大不久后,陶行知开始研究起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学以反传统面目出现,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对积极进取的青年学子陶行知发生影响,自然不难理解。
陶行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都是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被锻造出来的。他既博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醉心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哲学等。
同时,陶行知还对当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论著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总是把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考虑。他曾经大声疾呼:
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勠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陶行知跨入金大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惊涛骇浪已澎湃于全国。在政治上,他越来越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在数千年黑暗专制统治结束的前夜,在清廷垂死挣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的血腥屠刀面前,陶行知以方刚的血气、救国的激情,组织演说会,宣传民主共和,为革命造舆论。
两年后,武昌首义成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陶行知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和进步的社会活动中去,发起、组织了各种演说会、运动会、展览会。每次他都去卖门票,以门票收入或充爱国捐,或用作爱国活动的经费。
清廷虽然被推翻了,但辛亥革命却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当时,国人在思想上十分混乱。思想混乱时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期。作为教会学校,言论一向自由,如今更是纷呈复杂。许多师生依然认为中国无法建立共和国,只宜行君主立宪。
在金大的文艺会上,师生们围绕着“中国能否建立民国”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和”与“君主”之争,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的命运。陶行知就“中国必能建立民国,中国只能建立民国”而慷慨陈词。
在论战中,陶行知以革命的学说、缜密的逻辑、雄辩的口才和热烈的感情,多次驳倒论战的对手。陶行知的演说才能也由此崭露头角。
作为教会学校的金大,文艺会只用英语演说。陶行知从民族自尊心出发,倡议增设汉语演说。他的倡议在校内得到广泛响应,连校方也给予了支持。于是,金大的文艺会出现了汉语演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临时政府确定了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
“共和万岁!民主万岁!”这石破天惊的呼声犹在耳边。然而没过多久,政局突变,孙中山辞职,将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在位时出台种种举措,妄图恢复帝制。
国内的形势动荡不安,变幻无常。革命党不仅在政治上受压,在经济上也受刁难。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机关便面临着财政困难。陶行知既迷茫又失落,然而他并没有消极避世,相反,他热情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陶行知在和金大学生骨干商议后,邀请苏州东吴大学到南京与金大联合举行学生运动会。
在运动会期间,陶行知率领金大同学维持秩序,带头卖门票。这次运动会的门票收入全部赠给留守机关,以帮助黄兴解决困难。门票收入虽然很少,对于黄兴的经济困难只是杯水车薪,但青年学子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给黄兴和他的同志以政治上莫大的支持、鼓舞。
随着对王学研究的深入,在哲学上,陶行知越来越笃信王阳明的学说,并以“知行”作为自己的笔名。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主张“知行并进”:
要把“行”与“知”结合起来,注重实践。
陶行知对此深表认同,从此以后,他以王阳明的思想为标尺,来完善个体人格的修养,寻求救国之道,并干脆改名为“陶行知”。
“陶行知”作为笔名首次出现,是在《金陵光》学报上。《金陵光》是金陵大学学生办的学报,创刊于1909年12月。它所采用的文字是英文。到1912年底,已出刊3卷。陶行知认为,学校办在中国,撰稿人是中国人,它应该有中文版。在这里,祖国的语言、祖国的文字,代表着祖国的独立、中华的国格。他倡议增设《金陵光》中文版,并为之积极努力。1913年新年开始,《金陵光》中文版问世。
毕业时,陶行知写的一篇论文《共和精义》,说理透彻,论据充分,居全校之冠。从创刊宣言到毕业论文,他在《金陵光》中文版上一共发表了12篇文章。
1913年9月,他任《金陵光》中文主笔。中文版《金陵光》为金大带来了一股春风。不过,金大时期的陶行知,虽有一腔救国的热血和爱国的激情,但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单纯、幼稚、天真的青年。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后,反革命面貌已暴露无遗。轰动全国的“宋案”引起了当年夏天讨袁的“二次革命”。
但是,在1914年元月的《民国三年之希望》一文中,陶行知仍把革命党与反革命党的生死搏斗视为“萁豆相煎”,将窃国大盗袁世凯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并称,谓之“两贤交扼”。
在这篇充满书卷气的政论文中,年轻的大学生面对“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的现实,认真地发表了四点希望:
第一,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勠力以襄国事;第二,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第三,希望内乱永平……第四,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
陶行知天真地以为:
有此四点,则外患不作,内乱不兴……可以富,可以强,可以比骋列国,可以雄视寰球。
这真是书生空议论。虽是书生之论,却也不乏独到之见。
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将“共和险象”归结为四点:
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
这种剖析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如何消除“共和险象”呢?陶行知所用的方法是教育,他写道: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把教育的作用看成兴邦立国的根本手段是不妥当的,不过,这篇文章表达的关于教育的定义是广义的:
罗比尔曾说:“吾英国人第一责任,即教育为国家主人翁之众庶是已。”
陶行知毕生奋斗的教育事业也正是如罗比尔所说的广义的教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他的教育宗旨、目标是教育人民做主人,教育人民爱国、救国、报国。他不是几百、几千个入门弟子的老师,而是几千万、几亿被压迫、被愚弄人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