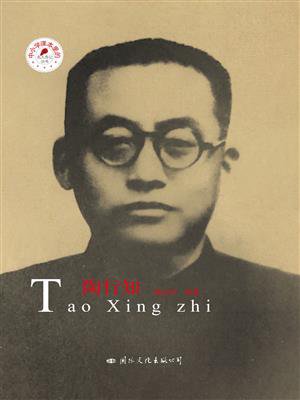毅然赴美留学之路
1914年夏天,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毕业。
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美籍校长包文授予陶行知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文科学士学位,因为金陵大学是在美国纽约州政府注册的。
时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应邀参加了这一年的金大毕业典礼,他为陶行知赞叹:“真乃秀绝金陵之学子!”陶行知向黄炎培当面敬赠了自己所编的《金陵光》。
毕业典礼结束后,黄炎培关切地问道:“陶君毕业后有何打算哪?”陶行知踌躇满志地回答:“我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
这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上研习教育学的最佳学府,那里汇聚着一批教育成果丰硕的老师。他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
我将以“教育救国”为我一生的理想。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处处民不聊生,靠军事革命哪里能创立真正的民主呢?我坚信,革新教育方法是改变中国的必由之路。
黄炎培对志存高远的陶行知赞许地点了点头。
只是,陶行知并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实现他的志愿。
陶行知的父亲对他说:
孩子,我们的家境你不是不知道。我没有能力挑起家庭的重担,已经很愧对你们了。你是家中的独子,承蒙一路上有好心的先生们无条件地赞助你的学业,好不容易才勉强维持到你毕业。家里的田太薄,你祖母也老了,你得体谅父母的难处呀!你念了这么多年书,要知书达理,懂得成家方能立业的道理。你妹妹文渼的同学小汪是个不错的孩子,性情也好,你们挑个日子把婚事办了吧,出国深造的事咱们不敢想啊!
父亲的话让陶行知很是揪心,可是他不忍心违背父母的意愿,毕业后就回乡成亲了。虽然妻子汪纯宜的温和贤淑让他深感欣慰,但是新婚的他并未陷入温柔乡里,去海外求学的念头一天强过一天。
是啊,那可是他的“强国梦”啊!陶行知很快打听到,国外有奖学金制。他想,自己只要努力,一定不难获得,只要凑足路费就可以迈出国门了。接着,陶行知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南京和徽州之间,开始积极筹措赴美留学的经费。
最后,在金陵大学校长包文的支持下,加上同学、亲戚、朋友的鼓励与帮助,陶行知勉强凑足了基本的费用。
买好了船票,去异国他乡的日子越来越近。烛影重重,陶行知欲言又止,终于,他有些愧疚地对新婚妻子话别:
纯宜,我真是有些说不出口……咱们成亲时日不多,可我这就要动身去美国求学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次排除万难去求学,不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前途光明,而是为国家的富强寻求良方,只有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哪!这些道理你可能一时之间不会明白,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体谅。
汪纯宜强忍着离愁,安慰陶行知:“你放心去学习吧,家里有我呢,我会照料好爹爹和妈妈的。”
陶行知握住妻子的手,感激地说:“你和文渼既是同学又是好友,今后家里就拜托你俩来主持了,凡事商量着办,家和万事兴。”
第二天,陶行知夫妇和陶文渼一同去照相馆合了影。姑嫂二人并排坐着,手里拿着花束,却并没有笑靥如花。离别之际,自然是无比惆怅。而陶行知站在她们身后,气宇轩昂,神色坚定。从此,这张照片在国外陪伴了陶行知3年。
1914年秋,陶行知赴美留学。他终于如愿以偿,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国外。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能走到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这一步对于他的人生的意义,不逊于鲤鱼跳龙门。
也许是角色转换的差异太大,给陶行知的刺激太深,所以他在成为天之骄子、社会精英之后,仍然对下层普通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与切实的关心。
在这一点上,陶行知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一生充满了浓厚的平民意识,他的大众情结持续了一生。这一点,与他学历相近的,更鲜有可比之人。陶行知一生的跌宕起伏,也与此不无关联。
轮船从吴淞口出发,越过万里汪洋。同舟共济的有清华毕业生,后来与陶行知在事业上同舟共济的教育家陈鹤琴。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随着轮船与岸边距离的增大,人们手中的彩带一根根地挣断了。
大家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再会”,同时又拿出白手绢来举过头顶不停地舞动着。由岸上望过去,船身像是被匝了几条雪白的带子;由船上望过去,岸上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那天到码头去送别陈鹤琴的有他的未婚妻、岳父、哥哥、姐夫、同学等十几位亲友,陶行知有谁送行则不得而知。不管有无人送别,对于每一位漂洋远渡的学子来说,兴奋与伤感大概是他们当时共同的感受。
这是陶行知第一次乘海船远航,他喜欢站在船舷,看着船体如利剑般劈波斩浪,不觉自言自语地赞叹:“海船走得这么快,好极了!”
陶行知忽然想起课本上说的,轮船是由蒸汽机推动的,便想去看看那蒸汽机,于是到机器轰鸣的机房去看了一会儿。心里又想:“蒸汽是水烧滚了变的,我得去看一看这水是用什么东西烧的,怎样的烧法?”
于是,陶行知又一路问到火舱门口,朝里一看,瞬时惊呆了:只见几个打着赤膊的工人像烤鸭一般在炉前烤着,他们的身上、脸上、手上一片乌黑,跟他们烧的煤炭没什么两样,浑身上下甚至被炉火烤得冒出了一层黑油!
这情景与甲板上尽情吃喝玩乐的天之骄子们形成强烈的反差,陶行知自感如同硝镪水刻到他的心窝里,他瞬时明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和血,甲板上的悠闲生活代价是火舱的人间地狱。陶行知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留学生就看不起下层工人,而对他们的生活寄予深深的同情。
8月底,轮船抵达檀香山,有华侨代表前往欢迎。陶行知等人上岛作短暂停留。他们在华侨的带领下,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水族馆,而后登船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
9月7日,他们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第二大城市、美国西部金融中心及对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旧金山结束了水上旅程。中国驻美领事、华侨代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中西干事都前往迎接。
宴会之后,一行人到斯坦福大学参观,次日全体师生乘火车一直往东,去芝加哥。他们中途在盐湖城下车,改乘汽车去游览美国著名的大盐湖,参观了马尔门教堂,而后回到火车上继续前行。行程横贯了大半个美国。
9月13日,他们抵达密执安湖畔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大家在此各奔东西:大部分同学继续往东去纽约,或是去东北的新英格兰,另一部分人往东南去。陶行知的学校大概是最近的,芝加哥就在伊利诺伊州内,他再向南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本来,陶行知想直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是因为那里学费高昂,负担不起,只有先在为外国学生免除学费并提供奖学金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政治学。
9月15日,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给父亲发了一封信,报告行程。伊利诺伊州是林肯的故乡,在林肯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年,他签署了一个《土地赠与法案》,内容是联邦政府对各州无偿赠与土地以建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就是在此政策下建立的34个州立大学之一。
伊利诺伊大学有两个校区,分校区就在芝加哥,主要是医学院所在地,主校区则设在芝加哥以南约200多千米外的两个紧邻的小城。伊利诺伊大学既不依山,也不傍水,景色乏善可陈,但它的教学科研实力却非同一般。
早在20世纪初,伊利诺伊大学就已成为全美国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建校不久,它就有几项“全美之最”,比如,1870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工程实验站;1876年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农业试验站,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陶行知到校时,正赶上佛林格大礼堂建成开放,詹姆斯在揭幕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
在不久以前,还只有医生、律师、牧师和教师才能上大学,就是说,高等教育是被这些所谓“博学”的专业占据着。而现在,我们认为,一个工程师如果想要在他工作的社区取得最大成就,首先需要受过良好的基本训练和足够广泛的教育,其次是能够成功地将所学的科学技术加以运用。
这是陶行知入校上的第一堂课,这场演讲给他留下了印象深刻。陶行知是有心人,校长的这段话可能会在两方面使他受到启发或产生共鸣:
一是教育在走向普及,教育对象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二是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受教育者拥有知识,而且注重学以致用。
这不仅与陶行知曾经在《共和精义》中表述的思想相合,也与他将来实行大众教育的行为一致。
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陶行知作为研究生专心学习。期间,他对西方流行的各派教育新思潮均有广泛涉猎与钻研,这更加坚定了他要为祖国教育事业投入毕生精力和心血的信念。同时,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也深深影响了陶行知。
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行动和实用,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等,要求教育应当与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杜威还指出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要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发展学生的个性。
这种批判精神、实验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早就不满中国旧教育,亟欲建立一种新教育来维护和发展共和体制的陶行知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0世纪20年代前后,虽然陶行知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学说与约翰·杜威的学说一衣带水,但是陶行知从不盲从地全盘照搬别人的理论,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总结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发展。
陶行知靠课余时间打工来维持生活、赚取学费。每天下课后,他就到车站、码头、饭店打工,晚上回到学校又一头钻进图书馆里看书学习,而且常常在图书馆要关门时才最后一个出来。
美国的生活成本很高,他所赚的那一点儿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偏偏这时,在寒冷的1月,国内又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24岁的陶行知悲痛万分,他是家中独子,一时之间恨不得马上回国。然而,他按捺住了回国的冲动,决意学成后以报效国家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陶行知掏出长期珍藏在上衣口袋里父亲寄给他的信,看了又看,直到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曾经,父亲为了支持他在国外学习,硬生生地戒掉了抽大烟的积习,尽量为儿子出一份力。戒大烟,这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做得到啊!
3个月后,长子陶宏出生的消息从祖国传来,这让陶行知在心生欢喜的同时,又平添了对父亲的缅怀之情。一生操劳的老父亲居然等不到抱孙子,等不到儿子回国尽孝,这是何等的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