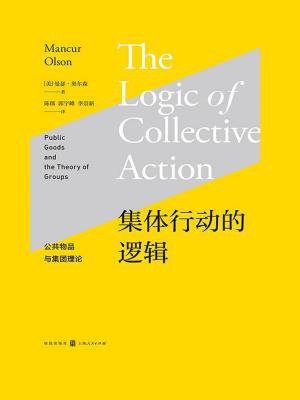公共物品和大集团
在一个组织中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情况与竞争性市场类似。例如,在一个完全竞争产业中的企业对产品更高的价格有共同利益。由于在这样的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肯定是一个统一的价格,因此除非这个产业中的其他企业也提高价格,否则一个企业不可能获得一个更高的价格。但是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同样也希望卖出尽可能多的产品,直到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超出其价格为止。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共同利益;每个企业的利益与其他任何一个企业的利益都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其他企业卖出得越多,这一企业的价格和收入就越低。简单些说,所有企业对更高的价格有共同的利益,而对产出有相对抗的利益。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供求模型来说明。为了简化论证,假设一个完全竞争产业暂时出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价格超过了所有企业在当前产出下的边际成本。同时假设,所有的调整将由产业中已有的企业而非新加入的企业作出,而且这一产业处于需求曲线无弹性部分上。由于价格高于所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产出因此而增加。但当所有企业都增加生产,价格就会下跌;实际上,由于假设了产业的需求曲线是无弹性的,因此产业的总收益将会减少。显然,每一个企业都发现当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时,增加产出是有利可图的,但结果是每个企业的利润都减少了。早期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一结果抱有怀疑, [1] 但今天在一个完全竞争产业中的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采取与它们的集团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这一事实已被广泛地理解并接受了。 [2] 一个由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组成的集团会采取行动减少它们总的利润,因为根据定义,在完全竞争中的每个企业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忽略它的产出对价格的影响。每个企业都发现,增加产出直到边际成本同价格相等并忽略它额外的产出对产业状况的影响,这些都是对其有利的。确实,最终结果是所有的企业都受到了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都没有使其利润最大化。如果一个企业预见到了产业产出的增加会导致价格的下跌而限制自己的产出,它受到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不管怎样它的价格都同样下跌而它的产出却更小。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只能得到收益的一小部分(或者产业额外收益的一小部分),因为企业产出减少了。
由于这些原因,现在人们一般已经懂得,如果一个产业中的企业都寻求使其利润最大化,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润会比它们不那样做时少。 [3] 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理论结论符合具有纯粹竞争特点的市场中的事实。这一结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尽管所有企业对产业产品更高的价格有共同的利益,但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承担获得一个较高的价格所需的成本——这里为产出必须减少。这一点相当重要。
防止价格在刚才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过程中下跌的几乎唯一的方法就是外部干预。政府价格支持、关税、卡特尔协议和诸如此类的措施可以防止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采取与它们利益相悖的行为。这样的帮助或干预是很常见的。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们是怎样产生的。一个竞争产业是如何获得政府帮助以维持其产品价格的呢?
假设有一个竞争产业,其中大多数的生产者希望通过关税、价格支持计划或其他政府干预来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为了从政府获得此类帮助,这一产业的生产者大概不得不成立一个游说组织;他们不得不成为一个积极的压力集团。 [4] 这一游说组织将开展一个相当规模的活动。如果遇到很大阻力的话,还需要一大笔钱。 [5] 需要公共关系专家来影响报纸舆论,并且还要进行广告宣传。也许还需要职业组织者组织忧心忡忡的产业中的生产者召开“自发的基层”会议,并让产业中的人士写信给他们的国会议员。 [6] 这一争取政府帮助的活动不仅要花费某些产业生产者的时间,还要花费他们的金钱。
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在争取政府帮助中遇到的问题与它在市场中遇到的问题——企业增加产量而引起价格下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如某一生产者为提高其产品价格而限制其产量是不合情理的一样
,
要他牺牲时间和金钱来资助其产业的游说集团获得政府帮助同样是不合情理的
。
在两例中
,
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
。
一个游说集团
,
或一个工会
,
或其他任何组织
,
尽管它为某一产业中的企业或工人的一个大集团的利益服务
,
但它从那一产业中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不到任何资助
。即使这一产业中的每个人都确信提出的计划将有利于他们(事实上可能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这将使组织的任务更加艰巨),情况还是这样。

尽管游说组织只是组织和市场之间关系逻辑类比的一个例子,它仍然具有现实的重要性。现在存在着许多深受群众支持的强大而且资金雄厚的游说组织,但这些游说组织并不是靠它们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而赢得支持的。现在最强大的游说组织是由于其他原因而获得资金和支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
一些评论家也许会争辩说,理性的人确实会支持一个为其利益服务的大组织,如游说组织,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支持的话,其他人也不会这样做,这样组织就会失败,他也就得不到组织应该可以提供的利益。这一论点,需要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来进行类比。因为用同样的理由可以辩称,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价格永远不会低于垄断集团制定的水平,因为如果一家企业增加产量,其他企业也会同样这么做,价格就会下跌;但每家企业都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就不会引起产量增加以致价格剧跌的连锁反应。事实上,在一个竞争市场中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大集团中情况也不是这样的。当涉及的企业的数量很大时,没有人会注意到因一家企业的产量增加而对价格产生的影响,所以没有人会因此而改变计划。与之类似,在一个大组织中,少了一个资助者并不会显著地增加其他任一资助者的负担,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相信如果他从一个组织中退出的话,他能够驱使其他人也这么做。
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通过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前面的论点至少与经济组织有着一些联系。例如,工人依靠工会组织获得他们通过个人努力在市场中得到的同样东西——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工人在工会中没有遇到他们在市场中遇到的同样问题的话,那实在将会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在两处的努力多少带有相同的意图。
不管意图有多么相似,评论家可能会反驳说,在组织中的态度与在市场中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组织中经常还牵涉到感情或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一点是否就使这里提出的论点与实际不同呢?
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可以用来检验这一反对意见。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一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是所有文明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需要的是税款,照定义就是 强制 的付款。实际上正如老话所说,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国家,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 [7] 尽管它试图增进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
国家不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而生存下去,其原因是一个国家提供的最根本的服务,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
 就如同一个竞争市场中较高的价格:只要有人能够得到它,那实际上每个人都能获得它。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物品和服务,如国防和治安,以及法律和规则系统,实际上是服务于国家中的每个人的。要想剥夺那些没有自愿承担政府开支的人受军队、警察和法庭保护的权利,即便可能,也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收税。政府提供的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作“公共物品”,而且公共物品的概念是公共财政研究中一个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此定义一个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
1
,……,X
i
,……,X
n
中的任何个人X
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
[8]
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团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就如同一个竞争市场中较高的价格:只要有人能够得到它,那实际上每个人都能获得它。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物品和服务,如国防和治安,以及法律和规则系统,实际上是服务于国家中的每个人的。要想剥夺那些没有自愿承担政府开支的人受军队、警察和法庭保护的权利,即便可能,也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收税。政府提供的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作“公共物品”,而且公共物品的概念是公共财政研究中一个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此定义一个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
1
,……,X
i
,……,X
n
中的任何个人X
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
[8]
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团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然而公共财政研究者却忽视了以下事实,
即实现了任一公共目标或满足了任一公共利益就意味着已经向那一集团提供了一件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
。
 一个目标或意图对一个集团来说是
公共的
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个集团中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之外。正如本章开头几段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集团和组织都服务于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如R.M.麦基弗所述:“人们……有共同利益,并把此视为他们的事业。……这一事业不可分割地包含他们每一个人。”
[9]
组织的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一般说来,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其他类型的组织也类似地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
一个目标或意图对一个集团来说是
公共的
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个集团中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之外。正如本章开头几段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集团和组织都服务于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如R.M.麦基弗所述:“人们……有共同利益,并把此视为他们的事业。……这一事业不可分割地包含他们每一个人。”
[9]
组织的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一般说来,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其他类型的组织也类似地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
正如国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场上出售其基本服务来维持一样,其他大型集团也不能以此为生。它们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约束力或吸引力,使个体成员帮助承担起维持组织的重担。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这里并没有说国家或其他组织只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政府经常提供集体物品,像电力,而且它们通常像私人企业一样在市场上出售这类物品。进一步说,像本书后面将要表明的,那些不能强制个人加入的大型集团也必须提供一些非集体物品,以吸引潜在的成员加入。然而,集体物品仍然是典型的组织物品,因为一般的非集体物品总可以通过个人的行动获得,而且只有当涉及公共意图或集体物品时,组织或集团的行动才是不可或缺的。 [10]
[1] 参阅J.M.Clark, The 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3),p.417;Frank H.Knight, Risk ,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1),p.193。
[2] Edward H.Chamberli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6th e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4.
[3] 对这一问题更全面的论述,见Mancur Olson, Jr.,and David McFarland,“The Restoration of Pure Monopoly and the Concept of the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LXXVI(November 1962),613—631。
[4] Robert Michels在他经典的研究中坚信,“没有组织,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组织的原则是群众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其 Political Parties , trans.Eden and Cedar Paul(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9),pp.21—22。也参见Robert A.Brady, 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3),p.193。
[5] Alexander Heard, The Costs of Democrac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特别请看注1,pp.95—96。例如,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1947年花费了460多万美元,而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花费了同样数目的金钱用以开展一个反对强制健康保险的活动。
[6] “如果真相大白的话……游说,包括其所有的支脉,将会是一个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产业。”U.S.Congres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Lobbying Activities, Report ,81st Cong.,2nd Sess.(1950),引自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81st Cong.,2nd Sess.,VI,764—765。
[7]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马克斯·韦伯(Weber,1947,pp.319—320)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
“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个人为了其理想的或物质的利益而进行并完成的。当经济活动是根据集团的秩序方式而调整时,这自然也是正确的……”
“即使一个经济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利益的结构和相关的情况会有所改变;会有其他追求利益的手段,但这一根本的因素仍将与以前一样。当然确实存在只建筑在单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但更为肯定的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而且从经验可以归纳出他们不能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在市场经济中使收入最大化无疑是所有经济行为的动力。”
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更进一步假设,整个社会的“业绩”与“奖励”和“处罚”是成比例的。参阅他们的著作
Economy and Society
(Glencoe, Ill.:Free Press,1954),pp.50—69。
[8] 关于这一简单的定义,在此请注意很重要的两点。第一点为,大多数集体物品只有在某一特定集团中才能被确定。一种集体物品为一个集团的人所有,另一集体物品为另一集团的人所有;一种集体物品可能有益于整个世界,而另一集体物品只关系到两个特定的人。进一步而言,某些物品对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而同时对另一个集团中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因为有些人不能享用它而其他人能够享用。举例来说,游行对住在高楼里,能够俯看游行队伍的人来说是集体物品,但对那些只能买票在路边观众席观看的人来说又是私人物品。第二点为,一旦确定了相关的集团,这里采用的定义和马斯格雷夫的定义一样,强调了排除集体物品潜在消费者的不可行是其最大特点。运用这一方法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组织所生产的集体物品通常使排外不可行。肯定地讲,对一些集体物品来说,排外是可能的。但是正如约翰·黑德(John Head)所揭示的,排外在技术上并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样做是不可行、不经济的。黑德还清楚地表明,非排外性只是对共同物品传统理解的两个基本元素中的一个。他指出,另一个为“供给的相联性”(jointness of supply)。如果一个人能获得一样物品意味着这样物品也能容易、免费地提供给其他人,那么这一物品就具有“相联性”。与相联性相对的例子是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纯公共物品,一个人对它的额外消费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份额。根据这里的定义,相联性并不是公共物品的一个必备的属性。正如本章后面将要表明的那样,至少有一种在这里考虑的集体物品没有表现出任何相联性,而且几乎没有一种集体物品其相联性能使其有资格成为纯公共物品。然而,这里研究的大多数集体物品确实都表现出了适度的相联性。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和重要性,请参阅John G.Head,“Public Goods and Public Policy,” Public Finance , vol.XVII, no.3(1962),197—219;Richard Musgrave,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McGraw-Hill,1959);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and“Asp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ories,”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XXXVI(November 1954),387—390,XXXVII(November 1955),350—356,and XL(November 1958),332—338。关于对公共物品概念是否有用的不同意见,请参阅Julius Margolis,“A Comment 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XXXVII(November 1955),347—349;and Gerhard Colm,“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CLXXXIII(January 1936),1—11。
[9] R.M.MacIver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VII,147.
[10] 然而组织好或协调好的集团行动并非 总是 为了获得集体物品。参阅本章第4节“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