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理论视域的开启:审美现代性视域中读解美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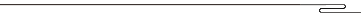
现代性问题直指理性统摄社会秩序,形成对现实的人的思维范式、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与人本身相异化的基本研判。这就意味着反抗现代性的努力,必然参与着反抗理性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学或者审美的感性力量可能蕴含着释放理性统治力量的基因,传承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仍然保有超越性追求的可能力量。审美现代性视域的开启,必须追溯到康德在形而上层面对美在意识体系中地位和功能的重塑,以及席勒将这一功能从形而上层面推进到历史现实的层面,推动着在美学历史中审视现代性,以及在审美实践中消解现代性的基本理论视域的逐渐开显。此后,现代西方美学始终在这一美的范畴中展开思考,这一基本思路在马尔库塞寄托审美实现现实的人的救赎,解答现代性危机的理论思路中逐渐形成。美在艺术的自律世界中超验于现实世界存在,表达着人性的追求,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保留着反抗理性对人的思想统治和精神统治,实现人性突围、实现救赎、实现生存的可能因素,不仅推动着西方美学思想研究的复苏,同时推动着许多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产生走向生存美学、审美救赎等价值趋向。

在西方哲学和西方思维的传统中,理性认识和理性逻辑总是决定着感性认识和感性形式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为什么是理性和理性逻辑,而不是感性和感性逻辑呢?自古希腊哲学肇始之初,巴门尼德所确定的真理之路中就奠定了西方哲学理性逻辑的统摄地位。而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经验与真理的关系,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却往往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在近代唯理论中,理性走向压倒性胜利,确定着理性逻辑在“真善美”的价值体系中的研判标准的地位。直至康德哲学为理性划定了经验的界限,为实践预留了道德的底线,为审美澄明了沟通二者的功能,从而引发了现代美学对美的重新审视;现代哲学在反思理性权威的压制性弊端时,才充满着重新思考人的意识中感性与理性关系的维度,感性就充满着改造理性权威这一形而上根基的解放力量,进一步产生了审美现代性视域。
马尔库塞明确康德是其美学产生可以追溯的导师。康德的美学“思想,仍为理解审美之维的完满范围,提供出最好的向导。……在《判断力批判》中,审美之维以及与之相应的快感,并不仅仅作为心灵的第三层次和能力,而是作为它的核心,作为自然借以与自由产生感应,与自律具有必然联系的媒介”
 。审美作为提供美的能力,他首先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审美知觉既是感性的又不完全是感性的(它是第三种基本能力):它给予快感,因而它在根本上是主观的”。其次,审美表现出组织人的感性所提取的个体经验,与理性所提取的普遍真理的形式。美所传达的“快感是由对象本身的纯形式构成,它又伴随着必然的和普遍的审美知觉——对每一个感受主体都适用。审美想象力虽然是感性的并因而是被动的,但它确是创造性的;在其自身的自由综合中,它建构起美”
。审美作为提供美的能力,他首先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审美知觉既是感性的又不完全是感性的(它是第三种基本能力):它给予快感,因而它在根本上是主观的”。其次,审美表现出组织人的感性所提取的个体经验,与理性所提取的普遍真理的形式。美所传达的“快感是由对象本身的纯形式构成,它又伴随着必然的和普遍的审美知觉——对每一个感受主体都适用。审美想象力虽然是感性的并因而是被动的,但它确是创造性的;在其自身的自由综合中,它建构起美”
 。最终,审美的想象力,将感性转变为具有普遍适用的客观秩序。因此,“审美之维是一中介,在这里感性和理智结合起来”。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审美之维可以使现实世界受制于自然规律的真理权威与受制于人类追求的自由取向相结合,从而创造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基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需求与精神文化发展需求的共同方向。最终,消解“文明的进步所创造的人的低级能力和高级能力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
。最终,审美的想象力,将感性转变为具有普遍适用的客观秩序。因此,“审美之维是一中介,在这里感性和理智结合起来”。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审美之维可以使现实世界受制于自然规律的真理权威与受制于人类追求的自由取向相结合,从而创造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基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需求与精神文化发展需求的共同方向。最终,消解“文明的进步所创造的人的低级能力和高级能力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冲突的化解仍然不是通过和谐的方式,而是“通过将人的感性能力置于理性的统治之下,是通过为了社会需要,对它们的压抑性作用”来实现的。在人类社会存在合理性的话语建构中,仍然通过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结构产生。在康德哲学中,第一次发现了“审美之维”,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进行哲学调解的努力,在现实层面就表现为去调和被压抑性的感性原则的实践。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冲突的化解仍然不是通过和谐的方式,而是“通过将人的感性能力置于理性的统治之下,是通过为了社会需要,对它们的压抑性作用”来实现的。在人类社会存在合理性的话语建构中,仍然通过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结构产生。在康德哲学中,第一次发现了“审美之维”,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进行哲学调解的努力,在现实层面就表现为去调和被压抑性的感性原则的实践。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意味着在探讨人类存在方式深层根基的形而上层面提出了审美的革命性意义。“审美之维”则意味着反抗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理性对感性的压制和统摄,同时在现实世界则可能产生着呼唤把现实的人的感性冲动从现实世界的理性权威中释放出来的革命声音。这就在康德以后的西方美学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种革命性意义,美学从形而上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建构新的西方美学,从而在转换现实世界的基本原则方面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审美现代性视域。最终,席勒将“审美之维”从理论逻辑带出,转换为剖解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审美现代性视域。在现代文明的症状诊断中,席勒明确指出:“就在于人类的两种基本冲动(感性的冲动与形式的冲动)之间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残暴‘解决’:以理性压抑的既存专制体制去压倒感性。”
 在解决现代文明症状的实践中,席勒再一次“想借助于审美功用的解放力量,达到重建文明的目的:审美功用被认为具有包含着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的可能性”
在解决现代文明症状的实践中,席勒再一次“想借助于审美功用的解放力量,达到重建文明的目的:审美功用被认为具有包含着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的可能性”
 。席勒把“审美之维”中的现实原则和感性原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验和新的秩序界定为“审美”。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一理论基石和理论思路。
。席勒把“审美之维”中的现实原则和感性原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验和新的秩序界定为“审美”。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一理论基石和理论思路。
席勒确认审美被重新认识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其表达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建构自身所使用的抽象原则,并且在现实世界拥有至高权威的理性原则的感性原则。直至“18世纪中叶,美学被当作一门新的哲学学科,作为艺术和美的理论:亚历山大·鲍姆加登创造了这个词的现代用法。这种从与感官有关系到与美和艺术有关系的意义变化,其意味着已远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更新”
 。因为,这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建构自身和建构现实的深层根基的新的原则,首先意味着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的话语秩序的可能诞生,席勒“所强调的是审美功用的冲动、本能的性质。这些思想,为崭新的美学理论,提供了基本材料”
。因为,这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建构自身和建构现实的深层根基的新的原则,首先意味着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的话语秩序的可能诞生,席勒“所强调的是审美功用的冲动、本能的性质。这些思想,为崭新的美学理论,提供了基本材料”
 。同时,这也意味着超越现实世界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可能变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学基础,抵御着理性的压抑规则。它努力去展示美学功用的中心地位以及把它作为存在的范畴建立起来,它激发出感性的内在真理的价值,使它们不再落入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原则之下。审美的学科具有一种与理性的秩序相对立的感性的秩序”
。同时,这也意味着超越现实世界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可能变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学基础,抵御着理性的压抑规则。它努力去展示美学功用的中心地位以及把它作为存在的范畴建立起来,它激发出感性的内在真理的价值,使它们不再落入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原则之下。审美的学科具有一种与理性的秩序相对立的感性的秩序”
 。从理性压抑乃至理性世界中获得人性解放,就必须恢复人的意识中感性的权利和人的需求中感性的冲动。既是感性在人的意识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关乎感性冲动在人的追求和社会价值研判中的标尺,感性实践在人类追求实现过程中的功用。
。从理性压抑乃至理性世界中获得人性解放,就必须恢复人的意识中感性的权利和人的需求中感性的冲动。既是感性在人的意识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关乎感性冲动在人的追求和社会价值研判中的标尺,感性实践在人类追求实现过程中的功用。
可见,审美现代性对美的内涵与功用的新阐释,直接影响着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美学热”,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美学要素的热潮,或坚持美的批判视域,或走向美的救赎实践,或参与美的理论要素。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美的内涵和力量不仅是理论层面上的重要视域和重要因素,还进一步提取出现代性理性权威,从而寻找反抗理性权威的实践逻辑。可以说,“美学热”正是在反思现代性根源这一深层问题时,确认意识要素是形成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又是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逐渐凸显着现代性批判中美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现实的指引和理论的发展,共同形成了审美现代性视域的必然影响乃至理论与现实的实践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批判与意识领导权等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寻找到感性这一反抗理性意识的解放力量,回归人的超越性精神、反抗现实理性统治的精神力量,而这一力量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审美的特性、形式和力量。马尔库塞从大众文化批判揭示大众文化的政治内蕴,到回归审美救赎揭示审美的政治实践。这就要求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必须审视马尔库塞美学的基本定义的阐释与理解,必须追问马尔库塞的审美实践何以可能、何以呈现、何以发展等问题。这不仅要求马尔库塞对西方美学的研究回到哲学诞生之初,哲学与美学尚未分野的古希腊时期,也必须在西方文明进程的重要转折——塑造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直至在颠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论变革中追问审美功用的深层根据,回答审美是否具有改造理性统治的现实力量。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代表,力图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重释审美或美的存在方式勾勒审美实践的解放路径,却仍然在理论的逻辑递进中陷入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困境。
马尔库塞强调审美的感性原则和现实基础是人性真实表达的形式来源,但仍然强调审美必须达到形式的普遍性才能获得真理性和实践力量。这决定着审美实践不仅带有实践的乌托邦色彩,在理论逻辑中也产生了审美现代性视域的内在悖论。正如埃克伯特·法阿斯在《美学谱系学》中勾勒美学通过审美形成自身谱系的过程中,其合理性内容和可行性实践并非通过感性经验取得,“如果美学通过反面,即通过过度强调它对于身体、性欲、生物学、遗传学和进化论,试图取代在传统上对它的过度知性化的话,那么任何未来的美学就不会取得成功”
 。未来的美学显然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无本质的、身体性的、消费性的形而下美学,而是仍然保有形而上精神的现代美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审美要成为一种反抗理性统治的力量,就必须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逻辑,又必须保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呈现人们爱智慧、关切自身的表达。现代美学必须成为现实的人探讨美在现实世界的样式及其应然样式的学科,既呈现现实的人对美的追求和建构,又体现着美的实现的历史性和有限性限制。美学必须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又同时反对纯粹经验主义的形而下,从而使审美成为勾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力量,使美学成为未来形而上学和现实世界秩序重建的一种重要因素。
。未来的美学显然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无本质的、身体性的、消费性的形而下美学,而是仍然保有形而上精神的现代美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审美要成为一种反抗理性统治的力量,就必须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逻辑,又必须保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呈现人们爱智慧、关切自身的表达。现代美学必须成为现实的人探讨美在现实世界的样式及其应然样式的学科,既呈现现实的人对美的追求和建构,又体现着美的实现的历史性和有限性限制。美学必须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又同时反对纯粹经验主义的形而下,从而使审美成为勾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力量,使美学成为未来形而上学和现实世界秩序重建的一种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