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理论基调的奠定:观照人的存在境遇的存在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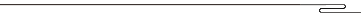
马尔库塞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美学思想,事实上源自其承续西方美学思想的理论脉络,必须回到西方美学史上来寻找其产生的根源。
柏拉图是第一个对美的本质以及美的规定性做出基本区分的哲学家,他区分出在对现实世界的美的判断中存在着美的事物与美的本质。同时,根据古希腊本体论的基本阐释,将现实世界的流变的具体的事物的美阐释为美的事物,认为在美的事物之上仍然存在着一个赋予美的事物以美的规定和感受的“美”,在这一基本阐释中可以得见,美是作为现实世界事物的本体存在的重要特征之一。“本质的大美的范式,是绝对的大美,它不是供眼睛去看,而是‘只被心灵’在概念上把握。”
 (《斐多篇》65,75d)柏拉图对美的本体论理解范式,形成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美的基本理解,这一思路直接影响到康德的审美判断力阐释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美既是心灵才能把握,又是本质的,因而美不能通过模拟,而是必须经过个体感受。因而,现实世界的艺术作品勾画心灵直观和领悟的真理的美的特性,艺术作品表面所表现的具体事物和具体对象,是作者内在精神对其本质的描绘。在柏拉图这里,美是理性的极致比例和完善的形式秩序,美闪耀着理性的光芒,绝对的大美就闪耀着绝对真理的光芒。在古希腊古典朴素美学中,本体亦即美的形象,本体是人们对智慧的终极目标,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也是象征美的女神,美与智慧形成了一致性的朴素表达。追求本体,乃是爱智慧的终极追求,也是对美的终极追求。在中世纪神的形而上学中,神是形而上的对象,而现实世界的美则是对神的奇迹的表达,适用于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之中,如赞美诗的美妙在于其是神的声音通达人的心灵的重要途径,如教堂的美在于其传播神在现世的力量,宗教人员的美在于圣洁,而这一圣洁来自服从、服务、谦卑于神的面前,是最接近神的奴仆。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中,知识、规律、秩序、理性则代表着美的基本特征;而在现代哲学反抗传统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对建构艺术中感性要素的推崇。
(《斐多篇》65,75d)柏拉图对美的本体论理解范式,形成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美的基本理解,这一思路直接影响到康德的审美判断力阐释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美既是心灵才能把握,又是本质的,因而美不能通过模拟,而是必须经过个体感受。因而,现实世界的艺术作品勾画心灵直观和领悟的真理的美的特性,艺术作品表面所表现的具体事物和具体对象,是作者内在精神对其本质的描绘。在柏拉图这里,美是理性的极致比例和完善的形式秩序,美闪耀着理性的光芒,绝对的大美就闪耀着绝对真理的光芒。在古希腊古典朴素美学中,本体亦即美的形象,本体是人们对智慧的终极目标,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也是象征美的女神,美与智慧形成了一致性的朴素表达。追求本体,乃是爱智慧的终极追求,也是对美的终极追求。在中世纪神的形而上学中,神是形而上的对象,而现实世界的美则是对神的奇迹的表达,适用于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之中,如赞美诗的美妙在于其是神的声音通达人的心灵的重要途径,如教堂的美在于其传播神在现世的力量,宗教人员的美在于圣洁,而这一圣洁来自服从、服务、谦卑于神的面前,是最接近神的奴仆。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中,知识、规律、秩序、理性则代表着美的基本特征;而在现代哲学反抗传统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对建构艺术中感性要素的推崇。
康德是“第一位使审美理论变成一个哲学体系整体的组成部分的现代哲学家”。康德肯定了美作为一种人的感受性体验,其对象区别于经验力判断,是向神圣本体存在形式的感受性。审美是一种通过直观的体验,而非感性经验,纯粹、唯一、绝对、完满,是通过个人感受对本体、存在进行终极感知,而非通过经验总结概括。审美判断力是个体直观的能力,而非理性逻辑能力。康德把美规定为在个体精神历练中,超越经验思维本身,通往先验世界的桥梁。可见,审美判断力是人的主观感性能力,而它的对象是抽象形式。美作为人的感受,必然被作为感性内容,必须接受理性形式的规范,才能够获得其所谓通达本真意义。可见,在形而上学中,美的真实性依赖于超验或先验的形式,而美恰好是一定流变内容整合在这一形式中,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而决定着获得美的仍然是形式本身。康德的这一基本判断,为现代美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做了一个基本的界定。美学从而获得了既是直观感性,又是以终极关怀为对象,从而既区别于理性形式,又区别于普遍经验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地位的判断,使得美学在现代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努力中具有特殊的力量。一方面,美学以自我关切的生存美学实现观照现代社会终极关怀的可能,提供给形塑现实世界的另一通路。另一方面,美学在现实世界,通过现实的人的个人直观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个体感受,提供了现实的人无须依附于话语权威而同样可以获得本真意义的理解的另一条通路。可以判断,近代以来,对美的形而上追问的发展,是审美救赎理论或生存美学理论产生的重要资源。在美的感受性中,反抗理性逻辑,反抗以理性为核心的话语秩序,反抗理性话语对人的思维的统治,从而形成了以感性直观形式对抗理性逻辑形式的可能性。
黑格尔运用无所不能的理性逻辑将美的理念、美的形式与美的感受性统一起来。在黑格尔这里,马尔库塞基本完成并且确认了其关于美学的形而上思考。美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形式,而艺术则是探索美的物化领域。黑格尔指出:“艺术美既不是逻辑的理念,即自发展为思维的单纯因素的那种绝对观念,也不是自然的理念,而是属于心灵领域的,同时却又不停留在有限心灵的知识和行动上。美的艺术的领域就是绝对心灵的领域。”
 这指明艺术的对象和艺术的领域乃是在绝对心灵的领域,因而可以从现实世界和客观限制中解脱出来,而实现在短暂的绝对心灵实践中的无限空间存在。而现实世界的心灵本身是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同现实世界的统治之中的。“意识、意志和思考就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情况,在无限和真实里去找它的真正的普遍性、统一和满足,这种统一和满足,这种由心灵推动的理性转化有限物质所达到的统一和满足,才能真正揭示现象世界的本质。心灵认识到它的有限性,这本身就是对它自身的否定,因此就获得它自身的无限。有限心灵的这种真实就是无限心灵。但是在这种形式里,心灵只有作为绝对否定,才变成实在的;心灵在它本身中设立了它的有限性然后把它取消掉。因此心灵在它的这个最高的领域里把自己变成自己的知识和意志的对象。绝对本身变成了心灵的对象,因为心灵上升到了意识的阶段,就在它本身中分辨出知识主体以及与此对立的知识的绝对对象。”
这指明艺术的对象和艺术的领域乃是在绝对心灵的领域,因而可以从现实世界和客观限制中解脱出来,而实现在短暂的绝对心灵实践中的无限空间存在。而现实世界的心灵本身是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同现实世界的统治之中的。“意识、意志和思考就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情况,在无限和真实里去找它的真正的普遍性、统一和满足,这种统一和满足,这种由心灵推动的理性转化有限物质所达到的统一和满足,才能真正揭示现象世界的本质。心灵认识到它的有限性,这本身就是对它自身的否定,因此就获得它自身的无限。有限心灵的这种真实就是无限心灵。但是在这种形式里,心灵只有作为绝对否定,才变成实在的;心灵在它本身中设立了它的有限性然后把它取消掉。因此心灵在它的这个最高的领域里把自己变成自己的知识和意志的对象。绝对本身变成了心灵的对象,因为心灵上升到了意识的阶段,就在它本身中分辨出知识主体以及与此对立的知识的绝对对象。”
 可以看到,黑格尔使用辩证法的逻辑推演使美的理念与现实心灵通过不断的对立统一而直接勾连起来。由此可见,“艺术就它的最高的真实价值来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艺术是和宗教与哲学属于同一领域。在绝对心灵的一切范围里,心灵都解脱了它客观存在的狭窄局限,抛开它的尘世存在的偶然关系和它的目的与旨趣的有限意蕴,以便转到省察和实现它的自在自为的存在”
可以看到,黑格尔使用辩证法的逻辑推演使美的理念与现实心灵通过不断的对立统一而直接勾连起来。由此可见,“艺术就它的最高的真实价值来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艺术是和宗教与哲学属于同一领域。在绝对心灵的一切范围里,心灵都解脱了它客观存在的狭窄局限,抛开它的尘世存在的偶然关系和它的目的与旨趣的有限意蕴,以便转到省察和实现它的自在自为的存在”
 。艺术作品采取一种对立于思想形成概念的抽象方式,却仍然是“概念从它自身出发的发展,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外化,但是这里面还是显出能思考的心灵的威力,不仅以它所特有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它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或异体)中再认识到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东西转化为思想,这就是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灵本身”
。艺术作品采取一种对立于思想形成概念的抽象方式,却仍然是“概念从它自身出发的发展,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外化,但是这里面还是显出能思考的心灵的威力,不仅以它所特有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它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或异体)中再认识到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东西转化为思想,这就是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灵本身”
 。必须看到,黑格尔再次确认艺术和审美是观照人自身,甚至是从概念这一外化了的东西之中再还原到观照人的心灵本身的东西。艺术和审美的对象是人的心灵,同时通过人的心灵,达到心灵对自我的直观。美和艺术的科学研究方式,一种是围绕实际艺术作品形成的艺术史、艺术评论等普泛性观点,是科学认识在艺术作品中的应用;另一种则是“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
。必须看到,黑格尔再次确认艺术和审美是观照人自身,甚至是从概念这一外化了的东西之中再还原到观照人的心灵本身的东西。艺术和审美的对象是人的心灵,同时通过人的心灵,达到心灵对自我的直观。美和艺术的科学研究方式,一种是围绕实际艺术作品形成的艺术史、艺术评论等普泛性观点,是科学认识在艺术作品中的应用;另一种则是“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
 。美的哲学是抽象艺术的特质,而呈现其普遍性的一般原则的哲学思维。美学正是以美的理念、美的本体、美的存在作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之思。
。美的哲学是抽象艺术的特质,而呈现其普遍性的一般原则的哲学思维。美学正是以美的理念、美的本体、美的存在作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之思。
可见,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层面探讨美,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区别于理性逻辑和理性范式的美的话语,乃是现实的人通过个体感受观照理念、存在或本体的可能路径。在现实层面,美学就通过人在审美过程中对象化的艺术作品,呈现出沟通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可能性。审美是现实的人的本真表达,通过直观、领悟、体验的方式,描绘着现实的人存在的本质、范式、形式等本体理念。传统形而上学发展至近代理性范式时,知识、真理、理性秩序乃至理性逻辑塑造着绝对的美的概念、美的特征、美的标准等美的话语。可以看出,美始终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在现实层面表征形而上特征的范畴。从而,现实世界的美的话语,直接影响着现实的人在现实世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实践。美,乃是形而上对本质追问的基本路径,它形成关于本质的终极思考,始终与其表征的理性形而上学有着对照式的回应逻辑。而现实世界的流变的事物的美,都不过是因为其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或者代表着终极、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世界的美的概念,是直接对接近、表征那种现实的人无法实现的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的美好描绘。因而,美的标准在现实世界的历史演进,必然始终与当时代的形而上学对绝对存在的相关规定有着同构性的基本特征和阐释逻辑。简言之,美是在现实世界描绘绝对存在的惊奇而感慨的词汇。而理性美的话语权,在现实世界成为现实的人心灵感受的表达标准,在现实层面表现为特定利益对自身利益合理化形成的价值逻辑的美的话语辩护。美是绝对存在的描绘性和感受性范畴,而美的基本特征又与绝对、完满、至高、善等绝对存在的基本特征具有同一性。美是完善的、和谐的、善的,大美是至高的、绝对的、终极的,美源自一定秩序,按照一定秩序,形成一定秩序,从而产生具有形式上的规范性和秩序上的和谐性内容和组织,这就意味着美的感受性的诞生。而美作为一种感受性活动,其对象决定着现实世界的美的本质。这一对象就是美的感受性诞生的客观实体,而美的感受性就是这一客观实体的基本特征的描绘性。因而,美与客观实体乃是同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受到海德格尔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旨趣影响,在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认知中诉诸审美救赎理论或生存美学理论。这种方式事实上是将审美作为治愈现代性问题的救赎稻草,审美既是现实的人在有限能力与生存境遇中追求具有超越性、无限性、至上性的生存根据的唯一途径,因此就可能形成在现实世界反抗理性话语秩序及其对人的主体性塑造的解放力量和革命力量。审美在形而上之中有着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是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的重要结论。审美可能是一种通过感性直观并具有直通存在根据的能力;生存美学那里可以获得审美通向存在根据的意义,具有在现实生存中获得生存本真意义的可能性;在身体美学那里可获得审美在现实的人的经验活动中获得美的感受的可能性;在政治美学那里获得审美通过改造现实的人,从而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可能性。将美学理解为第一哲学,无外乎首先要将美学理解为形而上学、存在主义生存论、现象学或政治学的意义,或将其理解为重建未来形而上学的根基质料时,间接确认其具有第一哲学的属性。
马尔库塞晚年通过审美力量实现解放实践的理论,可概纳为“审美救赎”,其思想也有着特定内涵。“救赎”(Redemption)概念产生于宗教教义之中,是指人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极度贫穷,最终致使人们出卖财产乃至自身成为奴隶,在经历这一基本过程之后,在某种神圣力量的帮助下获得上帝的原谅而重新具有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位置。在这一基本概念中,可以得见“救赎”一般指形而上层面的灵魂与现实层面的心灵。同时,“救赎”的过程是通过特定超验的精神力量实现对已有罪行的灵魂或心灵的解救。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思想,意在通过审美的个体观照拥有超越性追求的心灵体验,将自身从现实的人的异化劳动和大众文化造成的异化意识中解脱出来,将现实的人从理性思维和理性秩序形成的人的异化了的本质中解救出来。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实践又区别于宗教面向超验世界的心灵活动,要救赎的不是人的原罪,而是现实世界的存在根据和绝对权威形成的现实性上人的异化的本质,以恢复人实现自身的力量为归依。同时,审美救赎实践区别于宗教通过超验世界作为外在于人的绝对根据,实现外在力量通达现实的人的方式以给予人赎罪的根据与帮助,通过现实的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本身,在艺术领域仍然存在某种超越理性甚至是不涉及理性的领域。从灵魂的救赎,到心灵的拯救,显现审美救赎理论的基本路径,乃是人的精神层面的内容。这一过程,从单向度性向双向度性的拯救过程,无一不是对人的超越性精神的维护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似乎社会批判理论从现实批判开始,重新又回到了哲学精神的形而上原点,与其理论发凡的基本点有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审美救赎着力于人的灵魂的解放,发端于现实的人的灵魂的禁锢,这使得必须首先打破这一现实权力的禁锢,才能够推动心灵救赎的实现。另一方面,审美救赎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归宿,着眼于承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而其救赎实践又诉诸现实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追求,重又陷入存在主义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审美救赎理论一旦进入实践层面,就必然陷入乌托邦主义。
审美现代性视域在反抗传统形而上学的努力中,为推动美学从形而上学中分野出来,往往将美学命名为感性学,认为美是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的完善。故而,在其理论归宿中往往会产生一种依托于美学,以美学为理论资源的理论范式,如福柯、阿甘本等的生命政治理论。后现代哲学在反抗形而上学的努力中诞生,它们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知识及其真理性的权力内蕴,将知识、话语与权力的等同关系揭露出来,明确指出现实的人乃是知识与话语的秩序生产出来的行为和思维,并且通过生存美学、身体美学、意义美学等美学话语,通过日常生活话语的审美化,将人的精神重新拉回观照自身的维度,从而解构着现实世界的话语秩序,并力图用美学弥补这一秩序中人的思维的理性范式。若要在美的领域中寻找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答案,就必须审视现实世界的美与人追求的美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对现实世界所倡导的美的话语的反叛,又必须与重释何为美这一形而上论断紧密结合。这就是说,要重释何为美,就必须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为现实世界的美提供的基本特征。这一关于美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性意义的理论,必须观照美的标准产生的形而上维度,对美的话语做出新的规范和秩序。可见,审美实践在得出美与形而上学,审美与形而上追求之间的关系之后,常陷入存在主义美学无法自拔,在心灵、意识、精神的境遇中形成与现实秩序的一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