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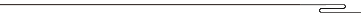
随着马尔库塞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关于战争、技术、极权主义、艺术、文学的许多手稿通过世界各种语言的整理和相继出版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国外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这些著作主要包括由美国新批判理论家、著名的马尔库塞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编辑的英文版的《技术、战争和法西斯》(1998)、《社会批判理论》(2001)、《新左派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2004)、《艺术与解放》(2006)以及由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和威廉姆·莱兹(Wi11iam Leiss)编辑的《本质的马尔库塞:哲学和社会批判文稿选辑》(2007)等。
这些成果的分歧也主要集中于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是否具有政治性和实践性方面。许多当代学者也倾向强调审美救赎思想的政治意含,本·阿格尔(Ben Agger)称之为“审美政治学”,道格拉斯·凯尔纳则在专著《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危机》中将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思想称为“革命政治学”,约翰·波克纳(John Bokina)和蒂莫西·鲁克斯(Timothy Lukes)在他们编著的《马尔库塞:从新左派到下一个左派》以及《马尔库塞:新视角》中全面集中论述了马尔库塞文化批判理论,并从中发现了美学的革命作用;斯坦福大学的巴里·卡特(Barry Kate)在《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解放的艺术》 (He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一书中,明确地指出了他认为审美救赎思想才是贯穿马尔库塞理论体系的线索,详细阐述了艺术所具有的革命性质,以及美学在马尔库塞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认为美学对于人类世界的解放的革命作用是马尔库塞的思想的起点和归结点。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如M.斯库尔曼(Morton Schoolman)则将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割裂开来,认为前者是对其后者的替代,这样就造成了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乌托邦式的认识。
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还深刻影响了其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重要代表哈贝马斯就深受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的影响,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肯定了马尔库塞对审美重要性的关注,指出,美学是理性与感性的中介,肯定美学对于改造工具理性具有的作用,认为“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
 。但是同时,他也分析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是没有实践路径的乌托邦,从这一点出发指责审美救赎思想。在这种影响下,他致力于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理性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也受到审美救赎思想的影响,其理论基于对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希望通过解构这种理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在理论旨趣上与审美救赎理论殊途同归。奥康纳就认为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需要从文化和自然两个维度进行,认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
。但是同时,他也分析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是没有实践路径的乌托邦,从这一点出发指责审美救赎思想。在这种影响下,他致力于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理性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也受到审美救赎思想的影响,其理论基于对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希望通过解构这种理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在理论旨趣上与审美救赎理论殊途同归。奥康纳就认为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需要从文化和自然两个维度进行,认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
 ,因而将实现生态解放的路径归结为文化实践。
,因而将实现生态解放的路径归结为文化实践。
从整体来看,国外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将审美救赎思想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探索,割裂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革命理论与审美救赎思想,最终只能走入乌托邦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