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意思维与休闲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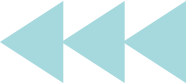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论述中国思维特点时,曾以庄子的《知北游》为例指出:“庄子在论述事物起源的时候,经过了一个物者非物的循环论之后,其结果,则是得出了‘犹其有物也,无已’这一对于处在人的思维世界之外的‘物的世界’的独立性、自足性的慨叹。”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庄子并不进行对于物质的原始状态的个别性追究,而是把物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世界来把握。”
 的确,在庄子对思维的认识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要求思维活动不受任何内外在的束缚而能获得对认识对象的整体把握。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说道:
的确,在庄子对思维的认识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要求思维活动不受任何内外在的束缚而能获得对认识对象的整体把握。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说道: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闻之,以黄帝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从庄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创意思维与休闲活动具有内在关联的精辟观点,即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思维之道,让思维深入事物本质之中,获得对事物的本质把握、穿透、超越和新的创造,也即产生“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创意审美效应。
何谓休闲?它与创意思维究竟又有什么关系?这需要从认识休闲的内涵说起。休闲,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休息、娱乐的含义,而是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属于生命哲学或人生哲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将休闲归为生命哲学或人生哲学范畴。《辞源》对“休”和“闲”的诠释,分别表述为:“休”除了人们所说的“倚木而休”的“休息”“休假”的意思之外,还包括“美善”“喜庆”的含义,表现作为人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或生活的感受。“闲”除了“安静”“闲暇”的意思之外,还具有“中间”“中规中矩”的含义,并引申为“法度”“中道”的意思,指的也是生命、生活的一种价值尺度,它展示出生命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尽管在古汉语里,“休”与“闲”是两个词,与现代汉语作为一个词的构词法不同,但词的基本含义则是相通的。中国文化、哲学对休闲的认识和把握,其特点是始终将休闲看作生命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与生命活动的其他形式一道构成生命活动的一个部分。同样,西方哲学也基本如此。亚里士多德就曾将“休闲”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absence of the necessity of being occupied)”。
 他着重从建构人生幸福目标的角度阐述了休闲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幸福就是人生的自足,它不是身外之目的,而是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是“人类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
他着重从建构人生幸福目标的角度阐述了休闲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幸福就是人生的自足,它不是身外之目的,而是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是“人类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
 。所以,休闲就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幸福的生命实践,让肉体和灵魂都处在良好的状态之中。
。所以,休闲就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幸福的生命实践,让肉体和灵魂都处在良好的状态之中。
不言而喻,休闲对于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言,就不仅仅只在于它的实用价值,而在于它的文化意义和美学意义,也即能够呈现出一种生命的状态,使生命能够在有限的生涯中获得无限的生命意义,获得无限的生命的创意,从而让生命更具活力,更具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休闲的哲学含义是谋求建立人与对象之间良性的互动和对应,特别是获得创意人生的互动和对应,那么,现代休闲文化理论认为,休闲绝对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游戏人生,消费人生,除了具有解除体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休整、调适功能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人的一种高层次的生存需要,是赢得精神的自由和营造心灵空间的需要,也是获得创意人生的需要。林语堂在谈到现代人应追求怎样的人生时曾指出:“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在这种观念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
 显然,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是创意人生的一种表现,是享受人生的重要方式。以休闲的方式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所突出的是给予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的人生意义的支持,获得对有限的个体生命的无限创意和无限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追求现代人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现代休闲文化将休闲看作世俗生活的一种生命超越形式,一种人生理想的实现方式,一种创造人生、创意人生的重要思维活动,其本质特征在于要让生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充实”和“丰盈”。因此,如果说创意思维活动是展现人的思想、情感、精神风采的一种审美表现,那么,它也可以说是人生休闲的一种展现方式,是休闲文化的一种实践方式,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创意思维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着的,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在他看来,创意思维和生命的活动,也就是人生宇宙、心灵宇宙的创意再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休闲文化思想内涵和审美内涵。
显然,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是创意人生的一种表现,是享受人生的重要方式。以休闲的方式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所突出的是给予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的人生意义的支持,获得对有限的个体生命的无限创意和无限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追求现代人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现代休闲文化将休闲看作世俗生活的一种生命超越形式,一种人生理想的实现方式,一种创造人生、创意人生的重要思维活动,其本质特征在于要让生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充实”和“丰盈”。因此,如果说创意思维活动是展现人的思想、情感、精神风采的一种审美表现,那么,它也可以说是人生休闲的一种展现方式,是休闲文化的一种实践方式,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创意思维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着的,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在他看来,创意思维和生命的活动,也就是人生宇宙、心灵宇宙的创意再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休闲文化思想内涵和审美内涵。
以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为例,从中就可以看到创意思维是有着深厚的休闲与审美的基础的。如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就常以“幽默小品”和“闲适小品”著称,除了大力提倡“幽默”是一种美学追求之外,他更提倡将它看作一种人生的姿态,一种写作立场。在他看来,幽默、闲适,最终都是为解脱性灵而获得人生的旷达自喜,潇洒自在,展现优雅人生,从而使他的文学创作也总是充满无限的创意。在《论躺在床上》一文中,他说:“我相信躺在床上是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我觉得那些像我这样躺在床上是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我觉得那些像我这样相信的人是诚实者。”他接着详细描绘出休闲与审美和创意思维的特点与妙处:
人们很少知道寂静和沉思的价值,这是可怪的。在你经过了一天劳苦工作之后,在你和许多人见面,和许多人谈话之后,在你的朋友们向你说无意义的笑话之后,在你的哥哥姐姐想规劝你的行为,使你可以上天堂之后,在这一切使你郁然不快之后,躺在床上的艺术不但可以给你身体上的休息,而且可以给你完全的舒畅。我承认躺在床上有这一些功效,可是其功效尚不止此。躺在床上的艺术如果有着适当的培养,应该有清净心灵的功效。许多商业中人每以事业繁忙自豪,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席不暇暖,案上三架电话机拨个不停。殊不知他们若肯每天上午一点钟或七点钟醒在床上静躺一小时,牟利一定可以加倍。就使躺到上午八点钟才起来,那又何妨?如果他放了一盒上等香烟在床边的小桌上,费了充足的时间离床起身,在刷牙之前把当天的一切问题全都解决完毕,那可就更好了。在床上,当他穿了睡衣,舒服地伸直着腰或盘身卧着,不受那可恶的羊毛内衣,或讨厌的腰带或吊带,令人窒息的衣领,和笨重的皮鞋所束缚时,当他的脚趾自由开放了,恢复他们白天失掉了的自由时,在这个时候,有真正商业头脑的人便能够思想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脚趾自由的时候,头脑才能够获得自由,只有在头脑自由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思想。这样,他在那种舒服的位置之中,可以追思昨天作事之成绩及错误,同时拣定今日工作之要点。他与其准时在上午九点钟或八点三刻到办公处,像奴隶管理人那样地监督他的下属人员,而“无事忙”起来,还不如胸有成竹地到上午十点钟才上办公处。
至于思想家、发明家和理想家,在床上静躺一点钟的效力尤其宏大。文人以这种姿势来想他的文章或小说的材料,比他一天到晚坐在书台边所得的更多。因为他在床上不受电话,善意的访客,和日常的琐事所打扰,可以由一片玻璃或一幅珠帘看见人生,现实的世界罩着一个诗的幻想的光轮,透露着一种魔术般的美。在床上,他所看见的不是人生的皮毛,人生变成一幅更现实的图画,像倪云林或米芾的伟大绘画一样。
无疑,这种幽默、调侃的叙说,道出了一种率真的性情,描绘出“自由”与“创意”的内在联系。所以,他强调指出:“身体上和精神上躺在床上的意义是什么呢?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休息、宁静和沉思的姿势。”自然,躺在床上不是要追求消极颓废式的人生,而是相反,追求的乃是一种优雅的人生形态,是审美与休闲的互动,即从审美的角度看休闲,休闲则是自在人生的愉悦和超然;从休闲的角度体验审美,是使休闲获得审美的感受,提升人生的境界,从而促进创意思维的萌发。
现代作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休闲、审美与创意思维活动存在内在的关联。又如,现代著名作家梁实秋的创作,也充分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他在1939年后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一类,曾风靡文坛的“闲适性”小品作品,从中就透露出一种博雅的人生情趣,一种盎然的创意思维。例如,《雅舍》一文虽写战乱时期,但他却是以自己在重庆的住所为题,写出极具新鲜创意的“雅趣”。这座住所虽简陋到“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透如滴漏”,他却久居生情,觉得自己的“雅舍”总是“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旁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虽为陋室,更何况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但外在环境的险恶,并不能阻止心灵的内在宁静,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并非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而是可以在“心”的闲适中,萌发出对险恶环境的诗意超越,萌发出更加无限的创意,使苦中的人生更加富有意味,并赋予无限的生命意义的强力支持。于是,我们在这种充满审美趣味的描述中,就自然而然地会从作者对“雅舍”的感触中,触发出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悟的联想,在培育知足常乐,洒脱豁达的性情中,萌发出对生命、对生活、对世界更加透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也使整个思维活动,特别是创意思维活动,在“物我两忘”的自由和超越中,得到更好的萌发与促进。
从休闲、审美和创意思维的关联上来看,创意思维并非只是突发奇想,即便是,它也是有着深厚的审美内涵和修养,并与休闲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审美休闲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深厚的审美功底,尤其是不与人的休闲活动紧密关联起来,所谓的创意思维往往是碎片化的,不连贯的,如同流星一闪而过,瞬间明亮,但过后则是消声无息,虎头蛇尾,不能展示创意思维内在的逻辑性,而想象力也必然受到相应的限制。从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正是因为他们有深厚的审美素养,有丰富的生活趣味,才会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表现出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的高度关切,对生命意义产生深刻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