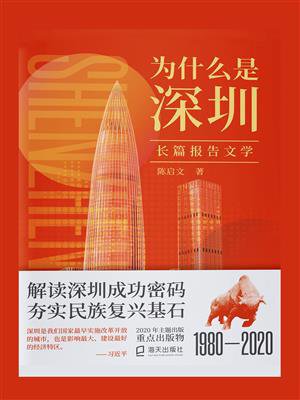历史的追问
我曾经离深圳很远,如今离深圳很近。我现在的邻居几乎都是深圳人,我也的确是深圳的邻居。最早听说深圳是1980年,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一个如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从遥远的中国南方海滨传到了内地,有个名叫深圳的小渔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许多人对深圳的名字还存在误读,将深圳读成“深川”。中国原本是一个充满了神话的国度,深圳也确实像一个神话,而神话往往会遮蔽历史真相。一直到今天,世人依然对深圳有一些误解,第一个就是对历史的误解。
深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难道真的是一个小渔村吗?
这是我对深圳的第一个追问。无论是追溯还是追问,一切都要从大海开始。
这是一片亘古以来就被大海拥抱的土地。这块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伶仃洋东侧的珠江入海口,拥有260余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和一个接一个的海湾:大亚湾、大鹏湾、深圳湾、前海湾、赤湾。那海岸线被风吹成一条条优美的曲线,随着潮汐起伏,活泛而灵动。然而,你绝对不能忽视这海岸线下的深邃和复杂。一些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开了那深埋在地底下的真相,当他们将考古铲深入到六七千年前的历史堆积层,发现这一带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便有人类活动的足迹。百越部族的一个分支—南越部族,他们是在这一带沿海沙丘谷地繁衍生息的海洋渔猎族群。早在夏商周时期,这些先民便面朝大海,凿木为舟,这一带的海湾便是他们奔波大海的港湾和可通舟楫的原始口岸。而大海,既是沧桑岁月的见证,也是这一方水土源远流长的归依。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转弯抹角,才能如同转世般,去接近那些已走出很远的先辈,去拜谒那一个个经世不灭的灵魂。这是走进深圳内心深处的一种方式。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岭南并入大秦帝国版图,原属百越的珠江三角洲被纳入南海郡管辖,郡治在今广州。汉武帝时在全国设置三十八处盐官,南头半岛便是其中之一,为番禺盐官治所,史称东官。三国东吴甘露元年(265年)又在东官设立司盐都尉,始建垒城,这便是深圳最早的城池。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将原南海郡东南部析出,置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县,而宝安的辖地包括今香港、深圳、东莞、番禺南部、中山、珠海、澳门等地区,以南头为郡城和县治。南头古城至今犹存,这是深圳的历史之根和文脉之源,就位于深圳市的南山区。当你沿着深圳市东西主干道深南大道一路向西,走到西头的最末端,就是深圳城市史的开端。若由此追溯,这一方水土的郡县史和城市史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年。
自宋朝以降,这座古城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盛产海盐、香料和珍珠。追寻那些在时空中穿过的身影,第一个不能遗忘的人物便是文天祥。这位南宋末年的右丞相兼枢密使,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南下的元军,最终兵败被俘,被押送到伶仃洋一带。他眼睁睁地看着南宋王朝的最后一场血战,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海战,一个王朝最终在大海里沉没。一位抗元将领无力实现对一个王朝最后的拯救,却在这里留下了最后的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今南头古城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建筑,便是当地人为纪念文天祥而建起的信国公文氏祠。正义堂中安放着文天祥的镀金塑像,从人体造型到衣褶线条都充满了纵放凌厉的动感,只有海风才有如此强劲的动力。文天祥的族人当年也追随他而来,如今文氏后裔在深圳宝安区的松岗、福田区的岗厦等地开枝散叶,“子孙繁衍,世泽流长”,这是历史为深圳注入的一股血脉。
当中国历史进入明代,这一带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多次伟大的远航,但他的壮行或远航就像一场辉煌的梦幻。当人类从陆地征战转向海洋争霸,从明朝到清朝都采取了壁垒森严的海禁。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今深圳境内同时设立了两座千户所城,一座是设于南头半岛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一座是设在大鹏半岛的大鹏守御千户所城,这两座海防要塞为“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进入十六世纪,粤海一带既有来自大西洋诸国的远征舰队,又有倭寇与海盗频频侵袭。葡萄牙原是一个扼地中海进出大西洋之要冲的西南欧小国,逐渐崛起为海上霸主,随后便开辟了东方航线,对东方诸国进行殖民掠夺。明正德六年(1511年)夏,葡萄牙武装商船驶入屯门澳,这一海湾三面环山,为天然避风港。当时,今深圳和香港皆属东莞辖地,史载“番夷佛郎机船队入寇,占据东莞县属屯门岛及海澳海道”。他们还在屯门岛上竖一石柱,刻上了葡萄牙王国的国徽,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广东按察使汪鋐进驻南头城,将葡萄牙武装商船赶出了屯门澳。据今世学者考证,此公不仅是中国抗击西方入侵者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武器的第一人。在击败葡萄牙入侵者后,他还对缴获的葡萄牙佛郎机炮进行研究和仿造,开“师夷之长技以驭夷狄”之先河。一个明朝的官员,既能用一只眼睛警惕地瞄准来自海上的侵略者,又能用另一只眼睛正视西方的先进科技。这正是中华民族必须具备的目光,而这样的目光最早出现在深圳海防前哨,又何尝不是深圳的历史眼光。
随着海上入侵者愈来愈多,为了加强海防,明万历元年(1573年)又从东莞县析出新安县,这一县名被寄予“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县域包括今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境。入清后,康熙年间又在新安县修筑了九龙寨、大屿山、南头寨、赤湾左右等六大炮台。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同时,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布防珠江口,对入侵的英军严阵以待。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期间,多次来新安县巡视海防要塞。而被称作鸦片战争揭幕之战的九龙海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深圳也因此被有些史学家称为鸦片战争的肇始地。
九龙海战的直接指挥者,为一位在深圳土生土长的水师参将赖恩爵,字简廷,为大鹏城客家人。深圳别称鹏城,就源自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大鹏所城,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据清代《新安县志》,其“内外砌以砖石,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周围三百二十五丈,高一丈八尺,面广六尺,址广一丈四尺,门楼四,敌楼如之,警铺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自建城以来,大鹏所城一直是伶仃洋东侧的重要海防堡垒之一。赖恩爵生于斯,长于斯,从小耳濡目染,深知海防之要害。而赖家乃是一个“三代五将”的武将世家,他少年随父从军,并未享受世袭恩荫,而是从普通士卒一步一步提升为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在九龙海战前夕,英军以坚船利炮频频挑衅广东水师,林则徐召众将商议应对之策。赖恩爵当时已四十四岁,老成持重,沉默低调,一开始没有主动请缨。众将领见英国舰船高大坚固,那枪炮又特别厉害,一个个望而生畏。赖恩爵这才打破沉默,沉着地表示愿意率师应敌,并向林则徐立下军令状。赖恩爵足智多谋,又善于选择战机。据说,除了水师船,他还下令征用一批渔船,在每船两旁排立稻草人进行伪装,并装上一口铁炮,配两个炮手,十个兵。就在他准备出战之际,九龙湾接连三天大雾,英军拿望远镜也看不清船上是军士还是稻草人。赖恩爵大呼一声:“天助我也!”随即率军出战,在大雾弥漫中把英军舰船包围起来,一声令下,百炮齐发,打得英军晕头转向。这一仗,击沉英舰一艘,击毙英军三十多人,连英军主帅道格拉斯的胳膊也被打断了。当时参与这场战事的英国军官亚当·艾姆斯里记述,中国水师船和岸上炮台的炮火都“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使英国官兵“人都瘫痪了”,“说不出话来”。最后,这名军官几近绝望地悲呼:“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
赖恩爵在家门口击败了英军,这也是他一生征战中的辉煌一页。他被道光皇帝赏戴花翎,封“呼尔察图巴图鲁”(巴图鲁有勇士之意),由参将擢升为副将。此后,赖恩爵又参加了中英穿鼻洋海战、官涌海战,屡立战功,被擢升为南澳镇总兵、广东水师军务提督。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虎门殉国后,赖恩爵继任广东水师提督,从一品。然而,由于大清帝国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已远远落后于英国,又加之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清廷临时换将,将一边抵抗侵略、一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力图“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革职查办,提前剥夺了他的指挥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惨败而告终。随着《南京条约》及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先后割让或租让给英国。国运衰落,天不假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赖恩爵在大鹏所城振威将军第病逝,年仅五十三岁。一位春秋鼎盛的将领,只因无力报国郁郁而终。在回光返照时,他将子孙叫到病榻前,这位抗英名将留下了“收回香港”的遗嘱。在他与世长辞近一百五十年后,香港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一百多位散居世界各国的赖氏后人,从未忘怀先辈的遗嘱,在香港回归之际纷纷回到大鹏所城,在道光皇帝钦赐的“振威将军第”横额上悬挂了一幅红色牌匾:还我祖愿!这其实也是深圳的百年祈愿啊。
从一座古城到另一座古城,从一条老街到另一条老街,感觉一直走不出一代代先行者的足迹。而“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孙中山就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0月6日,委派革命党人郑士良发动三洲田起义,在今深圳坪山区的马峦山腹地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这一年为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首义”。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庚子首义旧址—罗氏大屋。中山先生病逝后,当地民众为缅怀这位“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划时代伟人,将南头古城内的三条街命名为中山东街、中山西街和中山南街,又在古城外建起了中山公园。这也是深圳历史最悠久的公园,公园北边还保留着一段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南头城北城墙遗址,城墙高约两丈,城基宽约一丈,以红砂岩奠基和灰色巨石筑砌。这一段沿山形走势而筑砌的古城墙,那爬满苍苔的砖石以沉默的方式历数着兴亡与沧桑,在时空中延续着,一直延续着,而历史从未中断。在公园南门入口右侧,屹立着一座花岗岩石雕头像,这是由著名雕塑家钱绍武主持雕刻的、全国最大的孙中山石雕头像。在松柏掩映的雕像背面,镌刻着中山先生的手迹:“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大鹏所城所在的大鹏新区,也将其主干道命名为中山路。深圳人对一位先行者的敬仰,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更因中山先生首倡“敢为天下先”。老子《道德经》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中山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率先提出了“敢为天下先”的口号,穷其一生,身体力行,死而不已,还留下了“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而“敢为天下先”,正是深圳从先行者身上继承的人文精神。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冲破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一切力量。中山先生号日新,取自《大学》第三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不断革新和创新,才能遵循历史的大势,如大道之行。中山先生一直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致文化强、国家强、民族强。他尝为庚子首义处的一所学校题名为“强华学校”,以此激励当地学子为中华崛起、强大而读书。
如今,无论是始建于东晋的南头古城,还是明朝筑起的大鹏所城,均如大隐隐于市,以平实的姿态隐匿于如群峰崛起的楼群中。这古老的土地确实需要以一种雄健而强劲的方式崛起,也同样需要保持它的元气和底色,任你潮起潮落、众生喧哗,我自一派从容。这需要曾经沧海的历练,更需要一种海纳百川的涵养。透过这座古城,也让我见识了一个多元的老深圳,这里汇聚了广府建筑、潮汕建筑、客家围龙屋和中西合璧的骑楼。岭南文化原本就是在碰撞和交汇中产生的。第一次是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来自中原的华夏文化和岭南本土的百越文化在这片海湾发生了第一次碰撞和交融。随后中原王朝又因多次战乱而衣冠南渡,一批批中原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岭南,如今岭南人基本上是移民,岭南文化也基本上是移民文化。而岭南文化的另一个潮流就是海洋文化,那横亘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南岭阻隔了从岭南通往中原的路途,却挡不住奔向大海的珠江。在岭南文化的内核中依然保留有从百越时期流传下来的本土风度,那就是面朝大海、向海求生,也是岭南文化之元气。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国南方得风气之先,先后涌现出了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又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代表人物。在岭南人骨子里和文化里,逐渐形成了两种最突出的性格,一种如这古城青砖贯顶、石柱顶梁的岭南建筑一样—顶硬上;还有一种是他们在赶海时的一句口头禅—“我走先!”
从南头古城、大鹏所城走向历史上的深圳墟,感觉离大海越来越近。深圳之名,始见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史籍,那时的深圳还真是一个广府人和客家人聚居的小渔村,距南头古城约十公里。清康熙七年(1668年),在新安县边境修筑了深圳、盐田、大梅沙、小梅沙等二十一座墩台,为海防前哨,深圳从此便由一个小渔村逐渐形成了深圳墟。墟乃墟市,在今深圳的区域内当时共有三十六墟市,深圳墟为其中较大的一个。由此可见,深圳形成墟市的时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已历三百余年,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而随着香港岛、九龙、新界相继被割让或租让给英国,深圳河成为深港之间的分界线,内地与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都设在这里。若要追溯深圳的城市化或现代化之路,最直接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其毗邻香港的独特位置,一是得益于铁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广深铁路,原为广九铁路华段。这条铁路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动工施建,又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1911年全线贯通,一辆蒸汽火车从广州站出发,一路轰鸣着喘着粗气,浓烟滚滚地开往深圳。随后,广九铁路全线贯通,一趟趟列车往返于广州、深圳和香港九龙之间,而深圳则是广州和香港九龙之间的一个枢纽站。在火车的拉动下,深圳墟人口越聚越多,墟市渐渐变成了街道,街上挤满了琳琅满目的国货铺和洋货铺,俨然成了一个小香港。1953年,宝安县人民政府将县城从南头搬到了深圳镇,从此深圳镇便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历史的追溯,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诚实地正视历史。
如果你只看到了深圳崛起的一副面孔,就难以理解深圳为什么是深圳。
如果仅仅用四十年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待深圳,也同样难以理解深圳为什么是深圳。
对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必须放在一个辽阔而深远的背景下审视。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就有“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历史追溯,其核心和灵魂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浓缩。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每一个地方都有能追溯的悠久历史。深圳虽是经济特区,却也并非特例,它并非一座横空出世的城市,这古老的土地上也有自己深扎的根脉。只有深入它的根脉,才能看清在这一方水土更幽深的内部发生过什么。而一切历史的最终指向都是通往当下的道路。如此,你才能看清深圳走过来的路,从救亡图存之路到奋发图强之路,从近现代的历史变革之路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崛起之路。
历史其实一直在路上,只要你愿意回望,历史就在眼前。
若能正视历史,无论是从1979年3月深圳建市看,还是从1980年8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看;又无论是从如今的整个深圳范围看,还是从狭义的深圳看,深圳都绝不是一个小渔村了。诚然,那时候的深圳和全国的县城一样,很小,很狭隘,只有两条穿城而过的水泥路: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两公里。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广深铁路一直是单轨铁路,每日往返广深两地的旅客列车只有三对,日发送旅客仅一千多人次。那是典型的慢车,全程最快也得耗时两个多小时,最慢四五个小时。
站在1978年的时空中看深圳,那时候的深圳跟国内其他地区的县城差不多,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若同对岸的香港比,两地在一百多年的分治后已经拉开了千百倍的差距。这差距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当你站在这边灰暗的老街上眺望那边,香港那傲岸而炫耀的倒影几乎倾倒了整个南海。那倒影从对岸清晰地伸过来,连阳光照在玻璃上的光斑都历历可见。城市的差距还体现在那早已发黄又难以磨灭的历史数据上。1978年宝安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六千万元。深圳建市时,其生产总值还不到两个亿(1.96亿元),而香港当年的生产总值已超千亿(1117亿元人民币)。从面积上看,宝安县为香港的两倍,但其生产总值还不足香港同期的千分之二。
这就不能不让人下意识地追问,香港为什么是香港?深圳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河其实很小,并非难以逾越的天堑。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唱响了一首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条小河就是深圳河,而两岸最狭窄之处相隔只有三十多米。只要提到深圳河两岸的差距,谁都会提起深圳河畔的罗芳村。罗芳村早先叫罗方村,这原本是一个多以罗姓和方姓村民聚居的自然村落,两岸还有一座小桥相连。自从两岸以深圳河划界而治后,一个自然村就变成了两个世界。不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岸都未在边境线拉起铁丝网,小河流到哪里,哪里便是边界,河这边的村民还在对岸租地耕种,河这边的孩子还可以在河那边上学。后来,随着边境线管控越来越严,两岸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到1978年时,这边的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来块钱,而那边的村民人均年收入高达一万三千多港元,相差一百多倍,那时港币比人民币还值钱。如今罗芳村的很多老村民还记得当时一句话:“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这极为巨大的差距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也让老百姓用脚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河这边的村民纷纷逃向了河那边,一个罗芳村就跑掉了六七百人,在河那边又建起了一个罗芳村。河两岸的村民还约定日子,在河两岸见面,相互喊话,这也是当时的一大奇景—界河会。
逃港的又岂止是一个罗芳村。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既是逃港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也是世界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香港地区原本就与西方经济体系接轨,香港经济也进入腾飞时期。香港制造业以轻工业为主,工厂需要大量青壮年劳工,随着内地大量青壮年逃港,这些偷渡来的新移民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给香港经济腾飞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而港英当局针对内地去的偷渡客,曾从1962年开始采取“抵垒政策”,只要偷渡者抵达香港,一般就不会被遣返,还派送面包给偷渡客吃,并协助他们在粉岭、上水等车站登上开往九龙的火车。很多偷渡者就业后都领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人口在那三十年里增长了近十倍,由六十多万增加至近六百万,其中五分之四左右的人是从移民潮开始来港的内地居民,或这批移民在港出生的后代。而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大量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有的生产队在集体逃港前将七头耕牛杀了五头,导致无牛生产作业;有的民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而宝安又是当年的重灾区,至少有六七万人逃往香港。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我的邻居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香港老人,罗先生。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个香港人,我问他是哪儿来的,他笑着说,从深圳湾捞上来的。那次他带着两个亲老弟一起逃港。“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为了逃港,他们和珠三角的很多子弟一样,从小就苦练游泳。那时,沿深圳河早已拉起了带高压电的铁丝网,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很多人只能选择从海上偷渡。而这一带离香港最近的就是位于南头半岛东南端的蛇口,南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最近距离只有四公里。海边有大片茂密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而对于渺小的人类,哪怕四公里的海上距离也难以泅渡,一旦遭遇风浪就会迷失方向。谁往这海湾里一跳,就等于把自己的性命豁出去了。偷渡者有的以气垫作船、球拍为桨;有的抱着轮胎、空油桶或塑料泡沫之类的浮载物;还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只靠一条命。他们既要冒着被大海吞噬的危险,又要冒着被两岸边防军警抓捕的危险,一旦下水就只能拼命游向彼岸。罗先生刚开始还挺害怕,怕下海之后自己没有那么好的水性,不知能不能泅渡过去。这其实也是所有逃港者的心态。就在犹疑之际,有人突然看见红树林外边闪烁着边防巡逻队的手电光,那害怕和犹疑突然变成了豁出去的一跳,顷刻间一个个笼罩在夜幕下的阴影便扑通、扑通地跳进了大海里。谁都知道,等待他们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在泅渡中淹死,那不怪别的,只怪你命不好;一条活路,偷渡成功,那不就像从娘肚子里重新出生了一次吗?从此不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甚至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家里人知道了,马上就会烧香祭祖放鞭炮庆贺。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热烈庆祝。罗先生很幸运,他最终在沉浮挣扎中游到了彼岸。他的一个老弟还没来得及跳就被逮住了,还有一个很快就沉没在大海里了。一母生三子,三子不同命啊!说到这里,老人的眼里泪光闪烁,如回忆中的海水,幽深而冰凉。他充满忏悔地说,都是我,非要带着他偷渡,是我害死了他啊!
深圳,一座在大海的怀抱里孕育的城市,一个在大海的怀抱里诞生的经济特区,在分娩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撕裂和淌血的疼痛,而这如血流不止的逃港潮,其实也是其症状之一。深圳记者、作家陈秉安在其《大逃港》一书中,则把逃港潮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这一针直接扎准了穴位。
据广东省党史专家高宏研究,1977年11月,邓小平刚刚复出不久便南下广州,这也是他复出后首次外出视察。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广东情况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席卷深圳湾的逃港潮。邓小平默然地抽着烟,若有所思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还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完全有另一种思维。
邓小平在这次广东视察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他一再强调:“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邓小平在广东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正在一个伟人的大脑里酝酿,只有迅速、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多问题。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在这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力排重重阻力,启动了中国的一次伟大转型。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迈开了新时期的历史脚步,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两个词,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辩证地看,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词组:改革就是开放,寓改革于开放之中;开放就是改革,寓开放于改革之中。这两者之间连一个顿号也放不下。
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必须有关键人物来发挥关键作用。据《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记载,1978年春天,习仲勋肩负中央的重托,主政广东。在他抵粤赴任的当年7月,就深入逃港潮的旋涡中心宝安县调研。他从深圳湾一直走到了中英街。这条小街位于今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原名鹭鹚径(后更名鸬鹚径)。这一带曾是长脚鸬鹚栖息觅食的浅水湾,它们的长颈和长喙可以深入水底去捕食人们看不见的鱼虫,又以一种凌波微步的姿态款款而行,一旦有人走近,它们便振翅而起。这些大海的精灵,眼里从来没有人间的边界,那从天空飞过的翅膀投下的阴影,依然在贴着地面飞翔。一位迷惘的诗人曾经发问:“鹭鹚!鹭鹚!你自从哪儿飞来?你要向哪儿飞去?你在空中画了一个椭圆,突然飞下海里,你又飞向空中去……”
对于人类,这条长不足一里、宽不够七米的鸬鹚径,却如同两个世界之间的一条鸿沟。街心以界碑石为界,左手是深圳,右手是香港。小街的这边站着中方的边防战士,那边则站着英国大兵,他们近在咫尺,四目相对。尽管中方边防战士比对方要低半个头,但气势一点也不低于对方。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从来没有输在气势上,但在经济上却比那边差得太多。习仲勋站在中英街上,看到那边商铺林立,人流如潮,而这边却是冷落寂寥,四顾萧索,破败的老房子墙皮脱落,就像一块块刺眼的伤疤。
习仲勋透过一条小街,眼睁睁地看到了双方的差距,这让他心中非常难受也非常难堪,“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这个差距太大了啊!”时不我待,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习仲勋率先向中央请求:“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这正是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我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