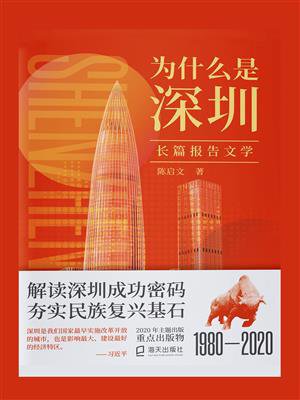世界是平的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先行者。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回归,一个特别行政区和一个经济特区的经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对进一步推进深港衔接、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加速推动深圳走向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2000年,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在南方首脑会议开幕式上指出,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反而造成南北差距加大,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数亿人口处于饥饿和贫病之中。这使全球化犹如一艘装载着不平等乘客的航船,很难安全到达彼岸。然而,全球化又是“一艘你不得不乘坐的船”,他呼吁发展中国家争取在这艘航船上占据应有的位置,以便使所有的乘客能够在团结、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安全到达彼岸。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下一直面临不公正的竞争,甚至受到排挤。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展示了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决心与开放的姿态。中国在1986年7月就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一直谈到关贸总协定走进历史。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国随即又由复关谈判转入入世谈判。历经十五年漫长而又艰辛曲折的谈判历程,中国终于在2001年11月10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有“经济联合国”之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入世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对一个国家全球化的程度,没有绝对标准,但有相对标准,主要以四大依据来衡量,即经济整合、人员往来、科技实力及国际政治参与。而在全球化视野内,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竞争力,又以产业结构、环境质量、公务员素质和机制、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评估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国人大多乐观以待甚至是翘首企盼,但也有人发出不可名状的惊呼:“狼来了!”那些早已洞见历史大势的专家,对中国入世的未来则充满信心,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强劲,中国的崛起将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催化剂之一。”
史蒂芬·罗奇的预言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一步一步经受考验。
中国入世后,由于深圳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先行先试的角色,国内外经济界几乎一致看好深圳,这个中国经济特区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受益者。深圳拥有众多的外向型产业和企业,在入世后的第一个红利就是其原材料进口成本会大大降低,而更重要的是将获得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迅猛发展,向深圳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特区如何继续“特”下去?深圳不是中国唯一的经济特区,随着更多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国家级新区加入开放的行列,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予深圳的那些特殊政策,已不再是深圳的特殊优势,更不是什么“特权”了。如果深圳一如既往地把发展思路局限于继续争取更多优惠或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那么在全球化的群雄逐鹿中就很有可能败下阵来,甚至有可能被抛弃。这让不少深圳人产生了焦虑情绪。2003年,互联网上贴出了一篇在国内外都引发了强烈反响的文章,它有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追问式的标题:“深圳,你被谁抛弃?”
此文堪称深圳的盛世危言,一篇网文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只因它触及了深圳的痛点,才让世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对于深圳来说,在中国入世后确实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世贸组织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的乘客能够在团结、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航行”,又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当世界变平时,最大的竞争是你与你的想象力之间的竞争—现在有太多教育、知识、联系和革新分配工具可用,内心全球化(没完没了地行走、交流、合作、体验)才能适应外部世界全球化的节奏感。”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深圳,还是深圳人,一方面要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跳出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和政策优势。深圳若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打造全面开放的新高地,就必须以先进城市为坐标,以世界前沿为参照,按国际规则“打篮球”,这样才能真正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世界是平的,你若想要登上“一艘你不得不乘坐的船”,先得把它变成一艘让“所有的乘客能够在团结、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航行”的船。而深圳最明显的城市分割就是“二线关”。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一条东西全长八十余公里的边防管理线把深圳“一分为二”,人为造成“一市两制”。关内和关外,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发展严重失衡。一座失衡的城市,势必形成心理上的落差,深圳人心目中,早已形成了关内是特区、关外是郊区的概念,有人说“关内是欧洲,关外是非洲”,还有人说“宁要关内一张床,不要关外一套房”。心理落差取决于现实的落差。在基础设施、市政配套、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关内关外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实力也悬殊,关外占全市面积的六分之五,每平方公里的产值仅仅相当于关内的五分之一。随着关内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越来越多,必然会给土地、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又必然会导致关内房价节节高升,让狭小的关内不堪重负。一个又一个必然,也让深圳必须向关外扩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必须消除一座城市内部的壁垒。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市民盼望已久的“特区外扩”终于成为现实。经中央批准,深圳将经济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一道在时空中延续了近三十年的“二线关”从此消失了,这为深圳能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填平了鸿沟,铺平了道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圳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并一步一步验证史蒂芬·罗奇对深圳充满了信心的预言。
这一次转型大致是在进入90年代后,尤其是香港回归和中国加入WTO后,深圳经济与世界经济基本接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转移,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深圳建立生产制造基地,这也促使深圳从“深圳加工”向“世界工厂”转型,使深圳成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主体部分,成长为信息化时代“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也成就了“深圳制造”。那些有着银灰色外壳的“世界工厂”成为深圳的标志,深圳也是“世界工厂”的代表,感觉浑身都充满了金属和电子元器件的味道。
这一阶段,一大批海内外的电子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在深圳和珠三角地区设厂,形成了以深圳为龙头的电子信息配套产业体系,而大批农民工也在流水线上历练成熟练的产业工人。无论是从中国制造看,还是从世界工厂看,深圳完善的制造体系和制造能力在国内几乎无可匹敌,放之于世界也名列前茅。如1988年在深圳投资建厂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就是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典型代表,拥有一百多万员工及全球顶尖客户群,在全球计算机和消费电子设备组装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一旦触及世界工厂,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提到一条路,那是我最不想走的一条道,却又是一条必经之路—广深高速。这条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于1997年7月1日开通运营,连接着广州、东莞、深圳三座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被誉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黄金走廊。据说,这是地球上最宽的高速公路,却也是世界上最拥挤的高速公路。一路走过来,沿途都是有着银灰色外壳的大型工厂,还有无数条道路连接着它,就像支流汇入主流。路上行驶的大都是巨大的货柜车,那些被挤在其间的小车,管你是奔驰还是宝马,一辆辆都在惊恐而又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密闭的货柜里装载最多的就是电子产品。这条路时不时就被堵住了,而全世界电子生产商最担心的就是这条路被堵,连老外都会操着生硬的中文惊呼:“广深高速堵车,世界电脑缺货!”
如今,深圳这条船上,已有全球八十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家企业于此落户,其中有近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设立总部或研发生产基地,如计算机产业的IBM、希捷、施乐,通信产业的飞利浦、北方电信、朗讯科技,新材料产业的杜邦等。国内许多企业也纷纷将研发生产基地搬到了深圳。还有很多跨国公司在深圳开设了“观察哨”,密切关注和追随“未来中国”发生的最新趋势。《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中山淳史到深圳实地探访后,发现深圳成为全球创业家的青睐之地,有赖于其全方位的开放以及惊人的效率。他发现深圳还存在一种叫“方案公司”的行业,对众多生产电子零部件和电路板的工厂了如指掌。只要创业者提出要求,他们就能快速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对接。即便创业者自身没有工厂或设计、研发部门,但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
从全球化的意义看,深圳是中国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城市,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如今已是中国内地市场机制最完善的城市。如今的深圳几乎容纳了整个世界,被誉为“小联合国”,蛇口被誉为“中国的夏威夷”,南头半岛被誉为“中国的曼哈顿”。这其实不是比喻,而是深圳对标国际的一种追求。深圳在对标世界,世界也在对接深圳。如美国《福布斯》杂志所说,从深圳的开放热潮中,你就知道旧金山湾区必须和深圳跨时空“联姻”,共建“加中湾”(Calichina),才能组合出世界最强的高新技术家庭。
若从深圳放眼中国,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电子、机电、家具、玩具、服装、食品……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识,但你却骄傲不起来。在深圳街头,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当夜幕上打出了沃尔玛的霓虹灯字幕,很多打工妹在下班后也来这里购物。这里的衣服和鞋子有的就是她们自己生产的,上面贴的却是世界名牌商标。放心,她们可以用自己的血汗作证,这里的每一件商品绝对没有冒牌,都是货真价实的名牌。在这个世界上,早已形成了一种通行的游戏规则,一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商标或品牌,一些人在流水线上制造衣服和鞋子。一双在流水线上经过上百道工序制造的耐克鞋,可以卖到三百美元,制造者可以拿到三十美元,而丰厚的利润属于商标或品牌持有方。这就是耐克,希腊胜利女神!但这些中国的打工妹还很少懂得它的英文原意,她们更懂得怎样拼命加班,拼命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在流水线上做一个月的耐克鞋,才能挣到买一双耐克鞋的工资,然后又到这里来买一双耐克鞋。
这也是一条生物链。不仅耐克,还有皮尔·卡丹、阿迪达斯、苹果、梦特娇、圣罗兰、香奈儿……美国的,法国的,世界的,中国已是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世界上最昂贵的产品。这个生物链的两端合作得最默契的还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人身上穿着中国人制造的衣服,中国人身上贴满了美国的品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自扮演的角色,就像命运的奇异安排。
在这强大无比的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背后,中国看似什么也不缺,但至少缺乏三样东西:一是具有原创性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二是对标全球的名牌商标,三是世界一流的经营理念。
对于中国,对于深圳,这些都形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倒逼机制。当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大海和世界,走在最前沿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占有先发优势,但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加速发展后,深圳经济特区若再按照原来的发展模式,那么土地、人口、环境、资源等要素均会难以为继。尤其是土地资源,深圳同其他城市相比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深圳经济特区(关内)只有三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和资源上已很难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即便拓展到整个深圳市,也只有约两千平方公里。若同国内一线城市相比,北京的面积相当于八个深圳市,上海的面积相当于三个深圳市,广州的面积超过了三个半深圳市。面对土地和资源这一难以拓展的大限,深圳人又一次做出明智的选择,如崛起的高楼一样向高端发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向自主创业和科技创新转型,由此迈进了位于价值链顶端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领域。
这是在深圳加工、世界工厂后的第三次转型,把深圳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推向了“高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