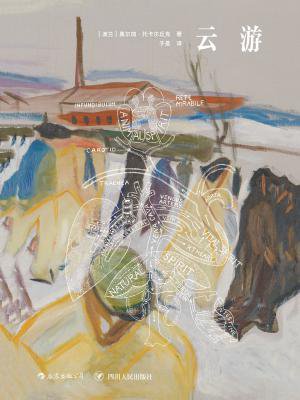库尼茨基:水(2)
“这个岛没那么大。”布兰科的妻子乔吉卡说着,往他杯子里添满浓烈的咖啡。
每个人都这样说,翻来覆去,有如念咒。库尼茨基明白他们的意思——本来他就不需要经人提醒才知道,这个岛小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岛上走丢。纵向总长不过十几公里,岛上只有维斯和柯米扎两个小镇。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被检查。无异于在抽屉里找东西。何况,岛民彼此知根知底,两个镇上的人都互相认识。而且,夜里也很暖和,藤上结满了成熟的葡萄,无花果也快熟透了。就算他们真的走丢了,也会安全无恙——既不会冻着,也不至于饿死,也几乎不可能被野兽吃掉。他们顶多就是在一片被阳光烤干的草地里睡一觉,在橄榄树下温暖地过一夜,背景中只有大海倦睡时的波涛声。不管他们在哪里,离主路最多三四公里。小石屋里有红酒桶,田间还立着压水机,有些棚子里还配备了给养,蜡烛。至于早餐,他们可以有葡萄汁,或是和水湾里的游客们一起吃顿正常的早餐。
他们下山回旅店时,有个警察已在门口等他们了。和之前的大个子不一样,这是一位更年轻的警官。看到他的那个瞬间,库尼茨基突然觉得有希望听到好消息了,然而,他只是问他要护照看。年轻的警官记下库尼茨基的个人信息,写得很仔细,一丝不苟,边写边告诉他,警方决定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内陆地区——从斯普利特开始,再到邻近的几个小岛。
“她有可能沿着海岸走到了渡轮口。”他是这样解释的。
“她身上没带钱。”库尼茨基用波兰语回道,再换成英语,“没钱。所有的东西,在这儿。”他把她的手袋拿给警官看,从包里掏出她的红色钱包,上面有白色珠串刺绣图案。他打开钱包,递给对方看。警官耸耸肩,用波兰文记下了他们的地址。
“孩子多大了?”
“三岁。”库尼茨基回答。
他们沿着蜿蜒道路下坡,回到了之前的地点,这天肯定会变得很热、很亮,一切都像在过度曝光的照片里。中午之前,照片上的所有物像就将在白色中一一消失。库尼茨基心想,考虑到这座岛几乎完全暴露在天光下,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高处,比方说,用直升机继续搜寻。他还想到了可以植入候鸟、鹳、鹤之类的动物体内的芯片,但没有足够多的芯片给人类用。为了自身安全着想,每个人都该植入那样的定位芯片,只要有人走失,你就可以在网上跟踪每个人的踪迹——道路,停车休息区。那该拯救多少条生命啊!他只需要对着电脑屏幕,盯着用不同颜色的线索标明的人、不间断的行踪、路标。圆形,椭圆形,迷宫。也许8字形会不完整,也许螺旋形会被突然中断。
他们带来了一条狗,黑色的牧羊犬;他们从后车座上拿起她的毛衣,给它闻。狗围着车闻了一圈,继而拔腿朝橄榄树林跑去。库尼茨基感受到那股冲劲儿:一切就要水落石出了,终于。他们跟着狗跑。狗停在一个地方了,他们肯定是在那儿小解的,但现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看上去,狗对自己的功劳挺满意的——可是,狗啊你得了吧!要找的不是这个!人呢?他们去哪儿了?狗不明白他们到底要自己做什么,只是很不情愿地再次闻闻走走,现在,它又返回到路边了,顺着路走,但不是葡萄园的方向。
所以,她沿着主路走下去了,库尼茨基心想。她准是搞糊涂了。她有可能走到前面去了,就在距此几百米的地方等他。她没听到他摁喇叭吗?然后呢?也许有人经过,让他们搭了段便车?既然他们至今仍未现身,那么,那个人把他们带去哪里了?那个人。一个失焦般面目模糊、宽肩膀的形象。脖子很粗。绑架犯。他会不会打晕了他们,再把他们塞到后备厢里去?他会不会带他们上了渡轮,到了内陆,现在已经在萨格勒布、慕尼黑或别的地方了?如果是,他的后备厢里有两个不省人事的人,他如何能过边境呢?
不过,现在狗跑进了空荡荡的山谷,斜穿过主路,下了满是石头、陡深的山口,贴着石壁径直往深谷里跑去。你可以看到,山谷下面还有一个疏于打理的小葡萄园,园子里有石头搭成的小屋,远远看去就像波浪铁皮屋顶的小报亭。一大垛干葡萄藤堆放在前门口,大概是用来生火的。狗在小屋旁边绕来绕去,不停地转圈,然后回到了门口。但门上有锁。他们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挂锁打开。门槛里面尽是被风卷入的碎木条。显而易见,谁都没办法进去。警官隔着污渍斑斑的玻璃窗往里看,接着动手砸起来,越砸越重,终于把那块玻璃砸下来了。大家都往里看,结果都被熏到了——饱含未发酵的葡萄汁和海水的气味从屋里一股脑儿地冲出来。
步话机刺啦刺啦地响起来,他们让狗喝了点水,接着,又把她的毛衣拿去让它闻。这一次,它围着小屋跑了三圈后,回到了主路,然后,迟疑了片刻,回头往石滩的方向走,只不过偶尔会在干草丛里走一段。从悬崖顶上可以俯瞰到大海。搜寻队的人凑在一起,向海而立。
狗闻不到气味了,便转过身来,趴在小路中间。
“To je zato jer je po noči padala kiša.”有人用克罗地亚语说了一句,库尼茨基只能套用波兰语的语法去推测,多少能明白,他们是在说昨晚下过了雨。
布兰科来了,带他去吃午餐,其实已经过了午餐时段。布兰科和库尼茨基下山去柯米扎的时候,警方依然留守山顶。他俩没怎么交谈,库尼茨基觉得,布兰科肯定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更何况要用外语说。这样也挺好,就让他沉默吧。他们在餐馆里点了煎鱼,餐馆搭在栈桥上,下面就是海水;那甚至都不算正牌餐馆,只是布兰科的朋友的地盘,这儿的每个人他都认识。他们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五官轮廓硬朗,很像饱经风雨的海狼部落人。布兰科给他倒了些葡萄酒,劝他喝光。他也把自己的酒喝光了。最后也不让他掏钱。
布兰科接了一通电话。“是警察,”他挂断后告诉他,“他们搞到了直升机,还有小飞机。”
他们制定了一套方案,决定乘布兰科的船沿着岛屿的海岸线走。库尼茨基给他在波兰的父母打了电话。他听到了父亲那熟悉的、沙哑的嗓音。他告诉他,他们还要待三天。他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一切都好,只是需要再待三天。接着,他打给工作单位,说他遇到一点小麻烦,能不能再请三天假。他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说是三天。
他在码头等布兰科。布兰科出现时,又穿着那件印有红色贝壳商标的T恤,但再仔细一瞧,库尼茨基发现不是那件,这件更新,更干净——他肯定有好几件同款T恤。他们停泊在码头上的许多小渔船里找到了他那条。写在一侧船身上的蓝色字母歪歪扭扭地标出船名:海神号。库尼茨基突然想起来,他们来这座岛时坐的渡轮叫作波塞冬号。很多东西——很多酒吧、商店、船只—都叫“波塞冬”。这两个名字就像过量的贝壳,全被大海吐出来了。你该如何向一位神明征求版权?库尼茨基很想知道答案。你们打算用什么支付版权费呢?
他们坐上了渔船,船很小,塞满了东西,其实就是加了船舱的摩托艇,船舱底板都是用木板拼铺的。布兰科在船上储备了很多水瓶,有的空,有的满。有些瓶子里装的是他自家葡萄园酿制的葡萄酒——白色的,品质好,很浓烈。这岛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家葡萄园和自酿葡萄酒。小船的马达也搁在船舱里,但现在,布兰科把它搬出来,装扣在船尾。试了三次,马达才发动起来。之后,他俩要说话就得大喊大叫了。马达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只过了一会儿,大脑就习惯了,如同在冬天,大脑会习惯性地相信,穿上厚衣服就能把身体和外部世界隔开。水湾和码头渐渐变小了,轰鸣声渐渐淹没了这片景致。库尼茨基远远瞥见了他们住的民宿房间,厨房窗台上的龙舌兰花犹如不顾一切向天空发射时被凝固的烟花,一次成功的喷射。
他看到一切都在缩小,渐成混沌一片:房舍化为不规则的深色轮廓,码头化为被无数细小的桅杆划过的白色斑点;小镇的上方山峰耸立,石壁光秃秃的,灰扑扑的,散布着斑斑点点的绿色葡萄园。天然景物不断增大,直到巨大无比。从岛上、从主路上看出去,这座岛似乎很小,但现在的它显现出了恢宏的魄力:坚固的岩石构成巨大的圆锥体,像一只从水中奋然挥冲而出的大拳头。
他们向左转后,海湾就在他们身后了,面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海,崎岖变幻的海岸线令人晕眩,看起来很危险。
拍打岩石的白色浪涛托带着小船,船的出现惊动了海鸟。他们再次发动马达后,海鸟惊慌地飞走了。喷气机留下一道笔直的白色痕迹,将天空分成两半。飞机是往南飞的。
船在往前开。布兰科点了两根烟,把一根递给库尼茨基。要抽烟也很难:海水从船身下翻溅上来,溅得到处都是小水花。
“看这海水啊,”布兰科大声说道,“一切都在水里游。”
他们接近一个有山洞的海湾时看到了直升机迎面飞来。布兰科站在小船中央,挥起手来。库尼茨基看着直升机,差点儿感到开心。这个岛不大,他这样想已不下一百次了;从那么高的地方俯瞰的话,什么都逃不出那么庞大的机械蜻蜓的视野,一切都会像你脸上的鼻子那样昭然若揭。
“我们去波塞冬吧。”他冲着布兰科大喊,但布兰科好像不为其所动。
“从这边没路过去。”他喊出了回答。
但船还是掉头了,放慢了速度。他们关了马达,驶进了石块间的小水湾。
岛的这一边也会被称作“波塞冬”吧,就和别的东西一样,库尼茨基心想。神在这里为自己建起了大教堂:中殿,壁龛,支柱,还有唱诗班。圣歌的形制是不可预料的,歌声有高有低,节奏未必很准。被海浪打湿的黑色火成岩闪着亮光,好像被涂覆了某种稀有的黑色金属。现在,天色已暗,构成这座教堂的一切元素都显得极其哀伤,令人悲痛——这是最典型的弃址:因为,从未有人在此祈祷。库尼茨基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正在目睹人类建造的所有教堂的原型,所有的旅游团去兰斯主教堂或沙特尔大教堂之前,都应该先被带到这里来。他想把这个新发现讲给布兰科听,但马达声太吵了,他们没法好好说话。他看到了另一条船,比小渔船大,船身上写着“斯普利特警察局”。这条船是沿着陡峭山壁下的海岸线开过来的。两条船汇合了,布兰科和警察谈了一会儿。没有找到他们,没有线索。至少,库尼茨基是这样推断的,因为船只的机械轰响完全掩盖了他们的言语声。他们肯定是靠对方的嘴唇动作、无奈的耸肩而领会对方在说什么的,轻微耸肩的样子和带肩章的白色警服并不很搭调。他们指示说,他们应该掉头回去,因为马上就要天黑了。库尼茨基只能听到一句话:“回去。”布兰科踩下了油门,小船发出了类似爆炸的巨响。水面绷紧了;细小的波浪像鸡皮疙瘩般延伸在前方的海面上。
这时候,向岛而行的感受和白天完全不同。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闪烁的灯光,在汇聚成形的浪头平息后再看到时,灯光就更鲜明可辨了。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中,光亮也越来越显著,各不相同,颗粒分明——抵达岸边的游船上的灯光和岛民家中的灯光是不一样的;广告牌和店面的灯光和晃动的车灯是迥然不同的。那是被驯服的平凡世界,给人安全感的景象。
终于,布兰科关掉了马达,小船静静地以侧面靠近海岸,没有任何预警的,船底就擦到了石头——船已靠上了镇上的小沙滩,就在他们的民宿边上,离码头还有很长一段路。现在,库尼茨基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泊在这里了。就在沙滩坡道边,停着一辆警车,还有两个穿白色衬衣的男人显然是在等他们。
“他们有事跟你说。”布兰科说着,开始拴船。库尼茨基浑身的气力仿佛违背了他的意愿——他害怕自己可能会听到那种消息。诸如,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他就怕这个。走向他们的时候,他的膝盖发软。
不过,感谢上帝,那只是一次常规调查。不,没有任何新线索。但事发已久,现在,事态变得严重了。他们带他下山,沿着和上次同样的——也是唯一的——主路开到了维斯镇上的警察局。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但他们显然很熟悉山路,连弯道处都不减速。他们很快地驶过了他失去他们的地方。
这次,在警察局里等他的人又多了一个。是个翻译,也是警官,高高的帅小伙,会讲波兰语,但——也不必遮遮掩掩——讲得磕磕巴巴的,尽管如此,警方还是特意把他从斯普利特召来了。他们问了些惯常的问题,好像有点不太自然,他渐渐明白了:现在的他已是嫌疑犯了。
他们再送他上山,回民宿。他下了车,做出走进去的样子。但他只是在假装进门。他在黑漆漆的小过道里等到他们的车开走,直到完全听不见汽车引擎声了,他才走出来,回到街面上。他朝灯光最密集的方向走,走向码头边的大道,所有咖啡馆和餐馆都在那儿。但现在太晚了,虽然是周五,那儿也没有太多人了;大概已经半夜一两点了。他环顾四周,想在寥寥几桌客人里找到布兰科,但没看到他,没看到那件贝壳T恤。客人里面有意大利人,那一大家子快要吃完晚餐了,他还看到两个老人,他们一边用吸管喝着什么饮料,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那家吵吵闹闹的意大利人。还有两个秀发如云的女人,很亲密地挨着,肩头抵着肩头,沉浸在她们的交谈中。还有一对儿都是本地人,两个渔夫。没有人在乎他,多么如释重负啊。他顺着一片阴影的边缘走着,刚好在水岸边,他闻得到鱼味,感受得到海上吹来的咸咸的、暖暖的轻风。他有点想转身,往上,沿着某条后巷,走去布兰科家,但他不能放任自己那么做——他们肯定已经睡了。于是,他在栈台边的一张小桌边坐下。侍应生没有来招呼他。
他望着走向邻桌的那几个男人。他们搬来了一把椅子——因为总共有五个人——全都坐下了。甚至没等侍应生过来,还没点任何酒水,他们就已经构成了一种不谋而合的紧密关系,彼此之间仿佛有一条隐形的、默契的纽带。
这几人岁数不等,有两人留着大胡子,但所有的不同之处都很快消隐在他们不约而同构建的小圈子里。他们在交谈,但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好像在排演一首合唱曲,每个人都要唱,现在都要试试音,开开嗓。小圈子里注满了他们的笑声——笑话是绝对应景的,甚而是需要的,哪怕是老掉牙的笑话。一阵低沉的笑声令空气颤动,占领了整个小圈子,也镇住了邻桌游客——那两个中年女人突然被吓到似的,安静下来。笑声引来了很多人好奇的注视。
他们是在为亮相做准备呢。侍应生的出现俨如拉开了序幕。这个托着一盘饮料的侍应生只是个孩子,却在不经意间担任了他们的司仪,宣布歌舞剧正式开场。他们一看到他就立刻活跃起来;有人举起了手——这儿——示意他该把东西放在哪里。一时间安静下来,玻璃杯被举起来了,杯沿凑上了唇边。他们中有些人—尤其是没耐心的那几个—无法抵抗闭起眼睛的冲动,恰如在教堂里,当神甫将圣餐庄严地放在伸出的舌头上时那样。世界随时都可以天翻地覆—地板在我们脚底下,天花板在头顶上,这些不过是陈规罢了,身体不再只属于身体本身,而是从属于生物链的一部分、生活圈的一个分区。现在,玻璃杯移动到了唇边,酒水倾空的瞬间其实是看不清的,就像用镜头对准瞬间发生的重力所引发的急速发射。从现在开始,他们就将紧握不放了—杯不离手。围着小桌团坐的人们开始展现彼此的牵连,揭示各自分属的小圈子,好像把各自头顶的光点连成乐谱,先连成小一点的圈,再是大一点的。光环会重叠,有如唱出新的和弦。到最后,他们的手也会举起来,先试探自己在空中的力量,用手势辅助他们的言词,继而滑向同伴的臂膀,在后背、肩头拍一拍,鼓励彼此。这些,其实都是爱的手势。这种动用手掌与后背、亲如兄弟的招呼方式并不带侵扰性,更像是一种舞蹈。
库尼茨基很羡慕地在一旁看。他很想走出阴影,加入他们。他从来不曾体验如此的亲密。他更熟悉北方,北方的男性社交比较含蓄腼腆。而在南方,葡萄园和阳光令人更快速地敞开身心,更容易变得没羞没臊,在这儿,这种舞蹈是相当真切的。仅仅过了一小时,就有人率先推开座位,抓住了座椅的扶手。
夜里的微风像只温暖的小爪子,轻轻拍打库尼茨基的后背,好像在推搡他朝那张桌子走,在催促他:“去吧,快跟上去。”他真的很想跟上去,不管他们要去哪儿。他希望他们能够带他一起走。
沿着没有亮灯的那半边路,他走回了自己的民宿,很小心地始终没有越过阴影和灯光的交界线。走进闷热、狭窄的楼梯井前,他深吸了几口气,呆呆地站立片刻。然后,他走上楼梯,在黑暗中摸索着每一级台阶,然后,连衣服都没脱就立刻倒在了床上,人趴着,双臂伸在两侧,好像有人从后面开枪击倒了他,好像他花了一点时间思考,终于接受了那颗子弹,便死去了。
几小时后他起来了——也就两三个小时,因为天还黑着——稀里糊涂地又下楼去,上了车。解除遥控防盗系统时,警报声轻响了几下,车灯也善解人意地闪了闪,好像在说,它孤单很久了。库尼茨基从后备厢里把他们的行李一股脑儿地都拎出来。他把行李箱搬上楼,甩在厨房和卧室的地板上。两只行李箱和一堆包袋、包裹、篮筐,包括一篮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还有装在塑料袋里的一双蛙鞋、几只潜水面镜、一把遮阳伞、几条沙滩毯,一箱他们买的本岛葡萄酒,一瓶他们非常喜欢的本岛红辣椒酱,还有几罐橄榄油。他把所有灯都打开,然后,坐到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之中。然后,他拿来她的手袋,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摊在厨台上。他坐在桌边,呆呆地看着那堆令人悲戚的小玩意儿,好像置身于一场复杂的挑木棍游戏,现在轮到他走——在不触碰别的东西的前提下,取出某一根小木棍。迟疑片刻后,他拿起了一支口红,拔下盖子。深红色,几乎是全新的。她不常用到这支口红。他闻了闻。很香,但很难形容究竟是什么香味。他的胆子大起来,把每一样小东西都拿起来,摆放到一边。她的护照很旧了,封面是蓝色的——照片上的她比现在年轻多了,留着蓬松的长发,还有刘海。最后一页上,她的手写签名已经模糊了—他们在过边境时常为此耽搁。用橡皮带捆住黑色的小笔记本。他松开橡皮带,翻看起来—笔记,手绘的夹克衫,一组数字,波兰尼卡某家法式小餐馆的店卡,后面记了一串电话号码,一缕头发,深色的头发,确切地说也不算一缕,也就十几根。他把笔记本放到一边。接着,他更仔细地检查剩下的东西。化妆包是用异域风情的印度织物做的,里面放了一支深绿色的眼线笔,粉盒里的粉都快用完了,防水绿色眼影膏,塑料削笔刀,唇彩,眉钳,一条磨旧、发黑的小链子。他还发现了一张特罗吉尔博物馆的门票,反面写了个外语单词;他把这张小纸片举到眼前,好不容易才辨认出来,那个词是:καιρóç,他觉得应该是K-A-I-RO-S,但也不能确定,他想不出那是什么意思。手袋底部尽是细沙。
然后是她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他查看了她最近的通话记录——他自己的号码最先跳出来,出现的次数也最多,但还有两三个人是他不认得的。收信箱里只有一条短信——是他发的,那天,他们在特罗吉尔走散了。“我在大广场的喷泉边等你。”她的寄信箱是空的。他返回到主菜单后,特定模式的屏幕光亮了一会儿,继而熄灭了。
有一盒开封的卫生棉。一支铅笔,两支原子笔:一支是黄色笔杆的比克原子笔,另一支笔身上印有“美居酒店”的商标。零钱:也有波兰的,也有欧元的硬币。她的钱包里有克罗地亚的纸币——不太多——还有十张波兰的兹罗提。她的Visa信用卡。一本橘色小便签,边缘已经发黑了。一枚古色古香的铜币,表面似有裂纹。两颗可比可咖啡糖。一只数码相机,带着黑色机套。一枚小夹子。一枚白色的回形针。一张金色的口香糖包装纸。面包屑。沙子。
他把这些东西井井有条、间距相等地摊放在黑色哑漆台面上。然后走到水槽边,喝了点水。再走回厨台边,点了一根烟。然后,他开始用她的数码相机拍照,每一样东西单独拍一张。他拍得很慢,近乎肃穆,尽可能放大,让影像撑满取景框,并使用闪光灯。唯一的遗憾是,他没办法用相机给相机本身拍一张照。毕竟,它也是物证。拍完这些后,他转战到走廊,包袋和行李箱都在那儿杵着,他也一一拍了照。但还没完,他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搬出来,开始拍每一样单品: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子,每一瓶药妆,每一本书。孩子的玩具。他甚至把塑料袋里的脏衣服也都倒了出来,把那堆不成形的东西拍在一张照片里。
他刚好看到一小瓶拉基亚水果酒,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把酒一饮而尽,接着给空瓶子拍了一张照。
他开车去维斯时,天光已亮。他吃了她原本为旅途准备、现在都干掉了的三明治:黄油经不住高温,融化后浸入了面包,留下一层晶晶亮的油光,奶酪现在都硬透了,变得半透明,像塑料片一样。驶离柯米扎的时候,他吃掉了两块,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开得很慢,很小心,留意路的两边,留意经过的每一样物事,牢记着他的血液里还留有酒精。但他觉得很踏实,感觉自己像机器那样可堪信任,像引擎那样强劲有力。他没有回头看,虽然他知道身后的大海正在涨潮,一米一米地上涨。空气是那么纯净,要是站在岛屿的最高处,你说不定能遥望到意大利。但此刻的他把车停在了湾口,环顾四周,看到了每一张废纸,每一样垃圾。他还带着布兰科的望远镜——他就是用这个检视了山坡。他看到了焦土色的护根覆土下、被晒枯的干草下尖耸的石头,看到了永生不灭的黑莓树丛用长长的枝条紧紧攀附在岩石上,被日光晒成了深黑色。野生橄榄树树干扭曲,已被采光了果实;废弃的葡萄园前还有一排矮小的石墙。
过了一小时左右,他直奔维斯而去,慢慢开,像警察巡逻那样。他驶过了他们去买过杂货的小超市——买的大多是葡萄酒——接着就到镇上了。
渡轮已停靠在码头。这船很大,像一栋大楼,一个漂浮的街区。波塞冬。船舱的大门洞开,一排小汽车和一群没睡醒的乘客排好了队,马上就要登船了。库尼茨基站在扶栏后面,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买票的人。有些是背包客,其中有个裹着鲜艳头巾的漂亮姑娘;他看着她,仅仅因为他无法移开视线。站在她身边的是个高个子青年,有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英俊面容。还有带着孩子的妇人,也许是本岛居民,没带任何行李;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提着手提箱。还有一对儿——她依偎在他的胸口,闭着眼睛,似乎还不想立刻结束一夜好眠,哪怕已被打断了。还有好几辆车——有一辆德国车牌的小汽车塞得满满当当的,还有两辆是意大利牌照的。还有去进货的本岛小货车,它们会带回来面包、蔬菜和邮件。小岛肯定就是这样维持日常生活的。库尼茨基很谨慎地往车里瞧。
队伍开始挪动了,渡轮把所有人和车都吞进肚了,没有一个人反抗,就像一群牛。又来了一群骑摩托车的法国人,一共五人,他们是最后一拨上船的,但也以同等的顺从消失在波塞冬洞开的大嘴里。
库尼茨基一直等到舱门发出机械的呻吟,完全闭拢。卖船票的人砰一声拉下窗板,走到外面来抽烟。两个男人一起目睹了渡轮骤然启动,渐渐离岸。
他说他在找一个女人和孩子,还把她的护照放到他眼皮底下。
售票员眯着眼睛,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他用克罗地亚语说了什么,无外乎是:“警察已经来问过她的事了。这儿没人见过她。”他吸了一口烟,又说道:“这个岛不大,我们要记住。”
他突然像老朋友一样,拍了拍库尼茨基的肩膀。
“喝咖啡吗?”他朝港口边刚刚开张的小咖啡馆点点头。
咖啡,当然要喝。为什么不呢?
库尼茨基坐在小桌边,没过多久,售票员就拿着一杯双份浓缩咖啡过来了。他们在沉默中喝咖啡。
“别担心,”售票员开口了,“在这里,不会找不到人的。”他又说了什么,摊开双手,十指张开,手心里的掌纹很深,这时候,库尼茨基正慢慢地在心里把克罗地亚语翻译成波兰语:“我们就像肿胀的手指头,很扎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售票员给库尼茨基拿来一块炸饼、几片生菜。他就这样走了,留下库尼茨基一个人坐在没喝完的咖啡前。他刚走,库尼茨基就感到短促的呜咽从内里袭来;那就像一块面包,被他硬是吞了下去。没什么味道。
肿胀的手指头,这个印象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谁会觉得我们扎眼呢?会是谁,一直注视着他们,在汪洋中的岛屿上,循着平铺在港口间的错综小路,注视着往来不息的本地人和游客们、快要融化在高温中的千百人中的一对夫妇?卫星图像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据说,你可以在卫星拍摄的照片上看清楚火柴盒上的小字。可能吗?如果是真的,那你从那么高的地方肯定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谢顶了。不停转的卫星、移动的小眼睛已填满了这无垠的冰凉天际。
他穿过教堂边的小墓园,走回停车的地方。所有墓碑都面朝大海,像是在古罗马的圆形剧场里,以便让死者们细细观瞻以缓慢的节奏日夜反复的海港景致。也许,白色的渡轮会让他们欢呼起来,甚或把它当作引领灵魂升天的大天使。
库尼茨基注意到,有几个名字反复出现。这儿的岛民肯定和岛上的野猫一样,不喜欢与外人交往,仅在几户人家间跑来跑去,几乎不会离开那个小圈子。他只停了一次——因为他看到一块小墓碑上只有两行字:
ZORKA 9 II 21——17 II 54
SREČAN 29 I 54——17 VII 5
看上去像密码,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下意识地根据字母顺序算了算日期。母亲和儿子。岁月定论的悲剧,分两段写完。死亡的接力。
这里已是城市的尽头。他累了,暑气飙升到峰值,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他攀过小岛的中心点、回到车里的这一路上,眼看着犀利的太阳把这座岛转化为地球上最不友善的地方。高温就像定时炸弹般滴答作响。
在警察局里,他们给他喝啤酒,好像警官们很想把自己的无助掩藏在白色的酒沫下面。“没有人见过他们。”一个魁梧的男人说着,很客气地把电风扇转到库尼茨基的方向。
“我们现在怎么办?”库尼茨基站在门口问道。
“你应该好好休息。”警官回答。
但库尼茨基没有走,只是待在警局里,偷偷听他们讲电话,听警方的步话机刺啦刺啦地响,那么多隐秘的信息啊,最后,布兰科来了,要带他去吃午餐。他俩几乎没怎么交谈。后来,他要求他把自己送回民宿。他很虚弱,和衣躺倒在床。他闻得到自己的汗味,令人厌恶的恐惧的味道。
他穿着衣服平躺着,躺在从她的手袋里倒出来的东西之中。他用专注的眼神去检视它们:犹如星群,有各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指向,不同的形状。那很可能是一种预兆。那是一封给他的信,信的内容涉及他的妻儿,但归根结底也是关于他的。他认不出那种字迹,认不出这些符号——这封信并不出自人类之手,这一点,他倒是可以确认。这些东西和他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他正在凝视它们——这件事很重要:他可以用双眼去看,并且看得到—恰恰是这一点最为神秘:他的存在即为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