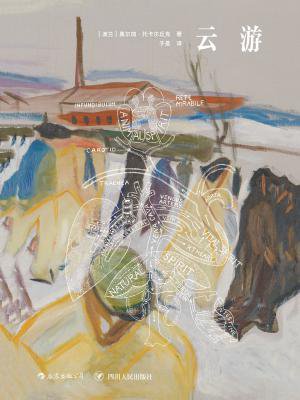处处,无处
不管为了什么或用什么方法远行,只要我踏上旅途,我就从雷达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从何处出发?前往何处?难道不可以在两点之中吗?我不就像你向东飞行后白白丢掉的一天,或是西飞后多出来的那一晚?我是否符合广受赞誉的量子物理学理论——一颗粒子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或许还符合另一条尚未被验证、甚至未经思考的法则——你无法重复存在于同一个地方?
我认为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找不到人,已然消失。他们突然出现在到达航站楼里,在海关官员在他们的护照上敲下入港章,或是在哪个酒店里拿到彬彬有礼的前台服务员递给他们的房间钥匙时突然存在于世。那时候,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自身的动荡,他们的存在其实依赖于地点、钟表显示的时间,依赖于语言、城市及其氛围。可迁徙、流动性、虚幻性——正是因有这些素质,我们才变得文明。野蛮人不旅行。野蛮人只是去目的地,或是去围捕猎物。
把自己保温杯里的香草茶分给我喝的女人也赞同这个观点,当时我们都在火车站等待机场大巴;她的两只手上都有散沫花染剂做的复杂图案,随着时间推移,图案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我们上了机场大巴后,她讲述了她的时间理论。她说,定居者和农夫更喜欢时间循环的概念所带来的愉悦,在循环的时间里,每一样物件、每一个事件都将必然回归起点,重新蜷缩成胚胎状,重复成熟到死亡的过程。但是,游牧民和商人在启程出发时,必须为自己想出不一样的时间概念:更能适应其旅行需要的一种时间。那是一种线性的时间,可以将进展量化,测量出距离目标或终点还有多远,用形象的百分比增加来表现,因而更实用。每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重复任何一个瞬间。基于这种理念,冒险、活到尽兴、把握每一天这些概念就都行得通了。然而,从骨子里说,这种观念的变革也是很苦涩的:随着时间流逝,一切不可逆转,损失和哀痛就成了日常事件。所以,你永远听不到那些人说出“徒劳”或“空洞”这样的词语。
“徒劳无功,账户空空。”那女人大笑起来,用一只染过图案的手捂住脑袋。她说,在那种被延展的线性时间里,只有一种幸存的方法,那就是保持距离,不要一步到位,那有点像先接近、再后退的组合舞步:一步向前,一步向后,一步向左,一步向右——简单好记。世界越大,你就能舞动得更远,跨越七大洋、两种语言、一整套信仰。
但我对时间有一套不同的看法。每个旅行者的时间都是相当宽泛、许多时间的整合体。可以是岛屿时间,但整片混沌汪洋中的群岛是无序排列的;也可以是火车站的时钟显示的时间,但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还有常用时间、平均时间,也就是没有人会当真的二十四小时太阳时间均分法。小时,消失在高空飞行的飞机里;黎明,被迫快进,因为下午和夜晚都快追到它的脚后跟了。你只是蜻蜓点水,掠过时间繁忙的大城市,你只盼望能彻底投入城市高空的夜晚,或大草原上的慵懒时光——从高处俯瞰下去,草原上渺无人迹。
我还认为,世界是可以内嵌的,嵌入脑沟,嵌入松果体——这个地球,可以只是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异物。事实上,你咳几下就能把它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