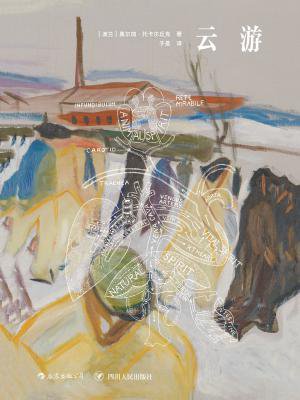你头脑里的世界
此生第一次远行,我就穿过了田野,步行。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不见了,也就是说,我走出了相当长的距离。我走过了整座公园,甚至往下沿着土路,穿进玉米地,走过被水沟分成了几个大方块、长满樱草花的湿漉漉的草甸,最终走到了河边。当然,在那个山谷里,那条河可谓是无所不在,流经各处的田野,还让地表植物下的泥土吸饱了河水。
爬到河堤上后,我能看到一条波动不止的丝带,一条总往视野外绵延的路,从这个世界里延伸出去。如果你运气好,还能瞥见一条船,或是往这个方向,或是往那个方向,行驶在河中的某条平底大船,不被两岸注意,不被树木注意,不被站在河堤上的人注意,也许是靠不住的地标,所以不值得去注意,只有一个观众觉察到,那些船自身的移动优雅至极。我梦想着长大后能在那样的大船上工作——或是索性变成一条那样的船,那就更妙了。
只是奥德河而已,不算大河,但我那时也很小。它在河流的等级里自有一席之地,后来我在地图上查找过——级别不高,但存在,好歹算得上亚马逊女王皇宫里的子爵夫人吧。但它对我来说已经够宏伟了,看起来庞然无际,随心所欲地流淌,不受任何阻挡,很容易泛滥成洪,完全无法预料。
偶尔会有些障碍物聚积在沿岸水底,形成小漩涡。但河水涌流,朝着北方一往无前,只在乎远在天边、遥不可见的目标。你不能一直盯着那河水看,因为河水会牵着你的目光一路奔向地平线,会害你失去平衡感。
当然,河对我毫不在意,只在乎它自己,河水涌动不息,令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长大后才知道这句话。
每一年,河水都要为承载那些沉重的船只索取高昂的代价——因为,每一年都有人溺死在这条河里,或是某个在炎炎夏日里下河戏水的孩子,或是某个在桥上发酒疯的醉汉,哪怕桥边有栏杆,醉汉还是会翻落到河里。为了搜寻溺水者,总会搞出一番大阵仗,邻近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结果。他们会请来潜水员和军用小船。我们偷听大人们的议论,从而得知那些被找到的尸体无不肿胀、惨白——河水把他们的生命荡涤得一干二净,把他们的脸孔冲刷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他们的亲眷们在辨认尸体时都会觉得很艰难。
站在岸边、凝视河流的我明白了一件事:流动的物事总是比静止的好,哪怕,流动会带动出各式各样的风险;相比于恒久不变,改变总是更高尚的;静止的物事必将衰变、腐败、化为灰烬,而流动的物事却可以延续到永远。从那时开始,那条河就像一根针,插入了我之前安稳的生活环境:公园里的景致,种着可怜巴巴的几排蔬菜的暖房,我们玩跳房子的水泥板铺就的人行道。这根针穿刺到底,标出了垂直发展的第三维度;被如此穿透后,我的童年世界就像一只漏气的橡胶玩具,在嘶嘶声中,气都漏光了。
我的父母不能算是安居型的那种人。他们不停地搬,一次又一次,最后总算在一所乡村小学附近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那地方离任何一条正儿八经的大路、任何一个火车站都很远。之后,旅行就仅仅意味着在犁沟里行走,翻过没有耕地的天然山脊去附近的小镇,买点东西,在当地办事处交几份文件。市政厅大广场的理发师总在店里,总系着那条围裙,无论怎么洗、怎么漂白都没用,因为客人用的染发剂留下污迹,看起来就像中国书法的一笔一画。我妈妈会去染发,我爸爸就在新新咖啡店里等她,坐在户外的那一两张小桌子边。他会看看当地的报纸,最有意思的通常是有警事报道的版面,讲的无外乎是谁家地窖里的腌黄瓜和果酱罐被偷了。
然后,假日到来,带来怯生生的游客,他们的斯柯达小车里都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早春,雪刚停,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做准备,在夜里提前计划,哪怕大地还没恢复生机;你必须等到能犁地、锄地的时候才能再次播种,从播种的那一刻起,地里的事就将占据他们所有的时间,从清晨到傍晚。
他们那代人喜欢用房车,把整个儿家当拖在身后。一只煤气炉,可折叠的小桌椅。一条塑料绳和一些木衣夹,可以在停车后晾洗干净的衣服。防水桌布。一套野餐用品:彩色塑料碟,厨具,盐罐,胡椒罐,玻璃杯。
沿途有个跳蚤市场是我父母特别喜欢光顾的(因为他们对教堂里、纪念碑前留影这种事并不感兴趣),我爸爸在那儿买过一只军用水壶——黄铜做的,壶身里有个容器,装满水后,可以整个儿吊在火上烧。虽然营地里有电,他却总用那只冒着热气、喷溅水沫的铜壶烧热水。他会跪坐在滚烫的水壶前,非常自豪地用咕噜咕噜滚烫的开水冲我们的茶包——像个地道的游牧民。
到了营地,他们就能与很多同道中人为伴了,他们会在指定区域停车安顿好,和左邻右舍热络交谈,周围尽是吊在帐篷吊绳上的袜子。通常,他们决定行程前都会参考那些煞费苦心罗列了所有观光景点的旅行书。清晨,去海里或湖里游个泳;下午,游览城里的历史景区;以晚餐告终,主菜通常是从玻璃罐里倒出来的:菜炖牛肉,浸在番茄酱里的肉丸子。你只需要再煮个意面或米饭就好了。开销总要一省再省,波兰兹罗提是一种疲软的币种——不太值钱。一路都要找到能用电的地方,然后百般不情愿地拔营离开,其实,这样的旅行都逃不出家的轨道,都逃不出同一种形而上的归家引力。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旅行者;他们离开是为了返回。等他们返回到原点就会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圆满了某种职责。他们回到家,把堆积在五斗柜上的信件和账单收拾好。好好地洗刷一通。到处展示照片,把朋友们烦得要死,忍不住直打哈欠。这张是我们在卡尔卡松。这张是我老婆站在雅典卫城前面。
然后,他们会安安稳稳地过上一年,每天清晨都回到前一晚留下的日常生活中,自家公寓的气息渗进他们的衣物,他们的双脚在同一块地毯上不知疲倦地磨出一条路径。
那种生活不适合我。在一处逗留时,不知不觉就开始扎根——不管是何种基因造成了这一点,我显然没有遗传到。我试过,很多次,但我的根总是很浅;最轻微的一阵小风都能把我连根吹跑。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根发芽,天生不具备那种植物般的能力。我无法从大地中汲取营养,我是安泰俄斯
 的对立面。我从移动中——从颤动起步的公车、轰隆作响的飞机、滚滚向前的火车和渡轮中——获取能量。
的对立面。我从移动中——从颤动起步的公车、轰隆作响的飞机、滚滚向前的火车和渡轮中——获取能量。
我有一副很实用的体格。小个子,很结实。我的胃小巧紧致,需求不多。我的肺和肩都很强壮。我不吃任何处方药——连避孕药都不吃——也不戴眼镜。我用剪刀自己剪头发,每三个月剪一次,几乎不用化妆品。我的牙齿很健康,也许有点不整齐,但颗颗完好无损,只有一颗牙是补过的,我相信填充物仍在左下方的犬齿里。我的肝功能指标在正常范围内。胰腺指标也正常。左右两边的肾都形状完美。我的腹主动脉也很正常。我的膀胱运作正常。血红蛋白指数12.7。白血球指数4.5。血细胞比容41.6。血小板228。胆固醇204。肌酸酐1.0。胆红素4.2。别的指标也都正常。我的IQ——如果你看重这类指标的话——是121;算是过得去吧。我的空间感特别发达,远远超出正常水准,但左右脑侧化却很明显。个性不够稳定,或者说,不太可靠。年龄随你说。性别符合常规。我总买平装本的书,以便不带懊悔地搁在月台上,留给找到它们的人去看。我不收藏任何东西。
我完成了学业,但从未真正掌握任何一门专业,对此,我是有点遗憾的;我的曾祖父是个织布匠人,把羊毛布料铺在山坡上,在日光直晒下漂白晾干。我可能也会擅长编织经线和纬线,但世上没有“便携式织布机”这种东西。织布是定居的部族人所擅长的技艺。我会在旅行途中织毛衣。可悲的是,最近,有些航空公司不再允许你在飞机上使用织毛衣针或钩针了。正如我所说,我从没学过哪种特定的行当,父母也曾苦口婆心地说过我,但事实上,我一直可以靠打不同的短工维持开销,云游四方。
我父母终于厌倦了干旱和霜冻,结束了二十年的旅行实验,回到城市生活之后,健康的食物在冬天的地窖里积攒起来了,从他们养的羊身上剪下的羊毛一点一点地填满了被子和枕头敞开的大嘴,他们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出发了:第一程旅行。
不管到了哪儿,我都会打零工。我曾在大都市郊区的跨国企业的车间里组装高级游艇的天线。那个工厂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拿黑钱的,从没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们每周五拿工资,谁要是不想干了,下周一就不来上班。那儿有高中毕业生,想在申请大学前歇一阵子。也有在半途的移民,坚信在西方的某个地方有个田园诗般公正、美好、国富民强的家园,在那里,人们必将情同手足。还有从原本的家园中出逃的难民——从他们的妻子、丈夫、父母身边逃出来的;还有在爱情中得不到幸福的人,困惑的人,忧郁的人,那些一直很冷漠的人。还有逃避法律的人,因为他们还不清债。流浪的人,漂泊的人。下一次发病时必会被送进医院的疯狂的人,然后,依据各种莫测高深的法规被遣送回国——从医院直接被送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地方。
只有一个印度人一直在那儿干活,工作了许多年,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他的待遇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他没有保险,也没有带薪假期。他干活时沉默不语,很有耐心,镇定自如。他从不迟到。他从不需要请假。我曾试图说服一些人建立工会——那是团结工会
 盛行的年代——哪怕只是为了他,但他不想要。不过,他被我投入的热情打动了,要和我分享他每天带来的午餐:辣咖喱。我已经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盛行的年代——哪怕只是为了他,但他不想要。不过,他被我投入的热情打动了,要和我分享他每天带来的午餐:辣咖喱。我已经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当过女招待、高档酒店里的服务员、保姆。我卖过书。卖过票。还在一家小剧院的戏装保管间里干过一整季,那个漫长的冬季里,我一直躲在后台,置身于厚重的戏服、绸缎披肩和假发中间。只要我做足了功课,也会当当老师,或是康复顾问,或是在图书馆里工作——尤其是最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攒够了钱,就会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