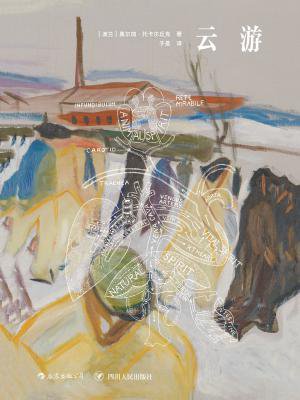珍奇柜
我历来都不算艺术博物馆的头号粉丝,但如果把博物馆换成珍奇柜——柜里的收藏品尽是些罕见、独特、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我就乐此不疲了。那些东西存在于意识的阴影中,一旦你要真切地看一眼时,它们就会飞出视野。是的,我绝对有这种倒霉的症候群。我不会被摆放在正中央的正经藏品所吸引,反倒会走向靠近医院的地方,去看那些常被挪到地下室的展品,因为人们认定它们配不上有价值的展厅,因为它们暗示了最初的收藏者的趣味很可疑。有两条尾巴的火蜥蜴,脸朝上,被收纳在一只椭圆形的长罐子里,等待着它的审判日——因为世上的所有标本最终都将得以复活。一只海豚的肾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一只异常的绵羊头骨,有两对眼窝、两双耳朵、两张嘴,俨如代表双重性的古老神像。一个被串珠和标签包起来的人类胎儿,标签上用拉丁文小心翼翼地写着“埃塞俄庇斯人,五个月大的胎儿”。经年累月的收藏,自然界里的异类,双头的,无头的,未出世的,全都懒洋洋地浮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再比如说:至今仍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博物馆里展出的“连体双胞胎”有一个头、两个身体,其病理形态表现出不容置疑的1=2,足以让人去质疑逻辑的基础。还要提一下始终在变化的食物标本:1848年的几只苹果,浸泡在酒精中,每一只都奇形怪状。显然有人认定,自然界中的畸形异类是不朽的:只有与众不同,才能存活下来。
就是这类东西让我奔波于旅途,缓慢但真切,沿着造物的差错和谬误。
我习惯了在火车上、旅店里、候机厅里写作。在飞机的折叠餐桌上。我在午餐时做笔记,在桌面下偷偷地写,或是在洗手间里。我在博物馆的楼梯井里写,在咖啡馆写,在暂停在高速公路路肩的车里写。我在碎纸片上、笔记本里、明信片上、自己的另一只手心里、餐巾纸上、书页的边缘写下只字片语。通常,写下的都是短句,小图案,但有时也会抄下报纸上的某些句子。有时,会有一个形象突显而出,宛如从庸众中切割出来的浮雕,我就会偏离原有的行程,追随片刻,启动它的故事。这是个好办法;我很擅长这样做。这些年来,时间已成我的盟友,如同它对每一个女人所做的那样——我已变成透明的隐身人。现在,我可以像幽灵一样移动,看到别人身后的东西,听到他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头枕背包睡去,或在睡梦中自言自语,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他们只是动动嘴唇,唇形意味着词语,而我很快就能代替他们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