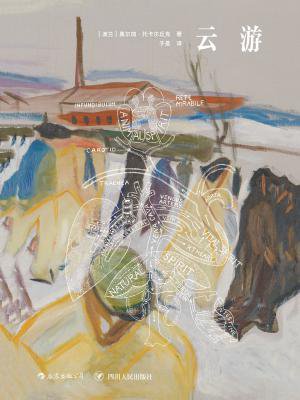看见即知晓
我的每一次朝圣之旅都会走向另一些朝圣者。这一次,朝圣者本身已被解体,仅存碎片。
比方说,有一堆藏品都是骨头——但都是有问题的骨头:弯曲的脊骨,有波纹的肋骨,必定是从畸形的身体里取出的,处理过了,干燥过了,甚至涂过清漆了。每一块骨头都有一块小号码牌,本来,观看者可以根据数字,在某本索引目录中找到相应的疾病描述,但目录本身已不复存在。毕竟,和骨头相比,纸张能有多耐久呢?他们真该把注释直接写在脊骨上。
你还能看到一根大腿骨,某些好奇心很强的人把这根骨头纵向切开,以便窥探里面的奥秘。想必那些人看过后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用麻绳把那两半骨头捆合起来,把整根骨头塞回到展示柜里了,他们的心思早就窜到别的东西上去了。
这个展示柜里收纳的几十个人彼此没有亲缘关系,在地理和年代上也相差很多——现在却聚在如此美丽的歇息处,宽敞,干燥,灯光通明,在一座博物馆里被宣判永存于世。他们肯定很羡慕那些永远困在大地下、与泥土缠斗不休的骨头吧。但他们之中难道没有人——也许是天主教徒的骨头—会担忧吗:到了审判日,他们怎么才能被找到呢?他们的骨头被分散到了不同地方,到时候,又如何能够重构那些犯下罪过,也有过善举的躯体呢?
各种头骨,涵盖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生长结构形态,带着弹孔的,或是别的武器留下的孔洞,或是萎缩的。手骨,被关节炎折磨变形。一条手臂骨,在多处骨折后,随其自然地愈合,想必经历了令人恐慌的长期疼痛。
太短的长骨,太长的短骨,骨结核,覆盖骨头表面的病变迹象会让你觉得:这骨头已被树皮甲虫啃过了。可怜的人类头骨,在维多利亚式展示柜的背灯照耀下,用咧嘴大笑的方式展露所有的牙齿。比方说,这一位,前额正中央有一个大洞,但牙齿却很完美。谁知道那个洞是不是致命伤呢?不一定。以前有个铁路工程师,脑部被一根铁棍直通而过,但他带着那样的伤口又活了很多年;不用说,这对神经心理学家来说是非常好用的现成案例,因为它向所有人宣告了一点:从根本上说,我们是靠大脑生存的。他没有死,但他整个人都变了。据说,他变成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人。既然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的大脑,那就让我们直接朝左转,进入陈列大脑的展厅吧。都在这儿呢!存放在溶液中的奶油色海葵状大脑,有的大,有的小,有的非常聪明,有的从一数到二都做不到。
再往下走就是胎儿专区,迷你版的小人儿。这儿有玩偶般的、最小的标本——每一样东西都很小,所以整个人能装进一只小玻璃罐。有些最年幼的小人儿就像小鱼、小青蛙,确切说是胚胎,吊在一根马毛上,漂浮在一大瓶福尔马林溶液里,一眼望去,你甚至都看不到它们。稍大一点的胎儿已展现出妙不可言的人类躯体的外表。尚未成人的小碎粒,半原始的幼仔,他们的生命从未冲破潜在的可能性,从未跨越那种魔法的边界线。他们拥有了恰好的形态,但灵魂从未入驻其中——灵魂是否现身,恐怕终究和形态的大小有关。在他们的身体里,物质开始运作,顽固地嗜睡,为生存做好准备,积攒生物组织,让各个器官运转,让各个系统贯通;眼部的功能正在启动,肺部已准备就绪,当然,应对光线和空气还需要别的系统。
下一排展柜里也摆放着人体器官,但已是发育成熟的,在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欣然接受了自己该有的、完备的尺寸。完备?它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能长到多大、长到何时就停止呢?有些真的不知道:这儿有一条肠子,长啊长啊,以至于我们的教授们很难找到能装下它们的标本瓶。更难想象的是:它们怎么能装进这个男人的肚子?他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被标在了肠子的标签上。
心脏。最后一步,揭示有关心脏的所有秘密——这种块状组织有拳头大小,不够匀称,脏脏的淡褐色。请注意,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颜色:发灰的褐色,很丑。我们不会想把这种颜色用在自家墙壁上或汽车里。那是内部的颜色,黑暗的颜色,光线到不了的地方的颜色,物质都掩匿在潮湿的内部,躲开了旁人的凝视,这样的内部色彩没必要自我炫耀。唯一可堪浮夸的就只有血液了:血是一种警告,用红色拉响警报——身体的外表已出现缺口,整合的皮肤已被划破。实际上,我们在身体内部是看不到颜色的。当心脏把血液压进血管时,血看起来就像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