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讲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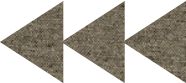
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罗兰、卡莱尔对我的不良影响,是因为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的自觉,一个太高的调门。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他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在中国,不稀奇。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都美极,美得无懈可击。这本应是文学的菜单,结果菜单比菜好吃。
福克纳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道德在土中,滋养花果——艺术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什么道德?现代文学,我以为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评断。
批评是很广义的名词。讲文学史,当然是文学批评。就文学本题讲,所谓文学批评,是指散文。历史学家,善批评者,作品收入散文。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大名鼎鼎。十九世纪后半的大批评家。我读罗曼·罗兰和爱默生时,起劲地读过一阵卡莱尔。我告别罗兰时,也告别卡莱尔。读书如交友。读万卷书,朋友总有千把个,但刎颈之交,不过十来人。卡莱尔不算。
父为石匠。农家子弟。求学于爱丁堡大学。当时学而优则教(士),他不想去当教士,最终决定坚持信仰,靠讲课、写作维持生活。长寿,身体却坏,一辈子胃病。
1825年出《席勒传》( 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 )。1826年结婚,此后撰稿为生,所作大多为德国文学论文。1837年,出版重头书《法国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 )。1841年,将多次讲演成集《英雄和英雄崇拜》(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他的名字与此著作联在一起。后又出版另一代表性著作《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
怎样评价卡莱尔?
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长得雄伟,爱默生推崇备至,敬爱他。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
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
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罗兰、卡莱尔对我的不良影响(不是他们不良,是于我不良),是因为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的自觉,一个太高的调门。
人要从凡人做起,也要学会做观众。
罗兰一上来就起点太高,结果并不长进。他在师范大学时写信给托尔斯泰,是这点水准,到老得诺贝尔奖,还是这点水准。傅雷也相似,上来就给罗曼·罗兰写信,从法国留学回来,到红卫兵冲击,还在那些观点。
起点高,而不退到观众席,老在台上演戏,那糟糕极了。后来罗兰访苏,简直失态。
他是讲文以载道的。
卡莱尔在文学上比罗兰好,辞藻丰富,句法奇拔。他认为无情与冷漠是世上的大罪。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
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
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
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
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卡莱尔痛恨快速发展的商业工业社会。眼光远。他反对物质主义。
我与他不同的是,他演讲,讲正经话,我只能讲俏皮话,笑话,骂人,写散文诗——骨子里,倒是英雄崇拜。
我反对民主?这话要有一个前提的。要这样讲下来,把民主和英雄主义对比下来,才可以讲讲。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他说的。说得好!
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受的苦没有白受。
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生于伦敦,苏格兰人,父为酒商。童年少年很快乐。1839年在牛津大学以诗得奖,四年后发表《近代画家》( Modern Painters ),1849年发表《建筑的七盏灯》(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1853年发表《威尼斯之石》( The Stones of Venice ),均属艺术论文集。
他谈艺术,谈谈就谈到当时的社会道德,这是他关心的东西。他在伦敦大学讲艺术,都宣传社会道德、人生等等,也是文以载道派。他的目的,想创造纯洁、快乐的理想国。
“美学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说。
这种类型的文人,中国历代有的是,认为诗赋小道,安邦定国才是大丈夫所为。我的看法,你要做政治家、教育家,你就去做,别做艺术家。拿破仑指挥军队,贝多芬指挥乐队——这很好嘛。要拿破仑去指挥乐队,贝多芬去指挥军队?
罗斯金人是好的,心是热的,这是我的评论。他的观点今已无人感兴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现在还常常提到他。诗人,以批评家传世。他的可贵,是对产业革命以后的庸俗物质主义,大肆攻击。我们目前所处的平民文化、商品极权,是他预见的社会。他是有远见的。
罗斯金、卡莱尔,都可为了道德,艺术要靠边。阿诺德不这样。他从不标举什么具体的道德方向,他知道艺术的道德是在底层。
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
道德在土中,滋养花果——艺术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
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什么道德。
现代文学,我以为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评断。
他的行文,流利庄重,不明说,多做暗示。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批评。我有一句不愿发表的话:
艺术家是分散的基督。
如果面对阿诺德,我就说给他听。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他是个老侠客,样子潇洒,文章漂亮。唯美主义的旗手,是佩特。唯美主义的健将,都是他的学生,王尔德也在他旗下。
唯美主义起于英国,到法国后,法国人却很自尊,不提佩特,其实法国那群精致玲珑的文人诗人,都受过佩特理论的影响。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莱里、纪德,都从唯美开始,又能快步超越唯美主义,潇洒极了。
佩特文体美丽。在西方,这种美丽的论文体是自佩特首创的。在中国,不稀奇。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都美极,美得无懈可击。这本应是文学的菜单,结果菜单比菜好吃。
他的《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 )和《希腊研究》( Greek Studies ),都写得好极。他是文学上的雅痞。《想象的肖像》( Imaginary Portrait )是他写的美好而不可及的传奇。另有《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 Marius the Epicurean )。
此公不能等闲视之。
英国历史著作,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写过《英国史》(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和《弥尔顿论》( Essay on Milton )。
据说此二书受到现代人的重视,远超过卡莱尔等人。他的文章无一页沉闷。他表白的是多数人的见解,可是别人表白不清楚,在他却是轻轻易易,通而不俗,文笔愉快。实际上,这种才能,正适合写历史。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这个人文章要看。很好很好。达尔文的继承人、发扬者。他是生物学家,杂文、论文、讲演,文学价值都很高,看似轻松,毫不在意,而又雄辩,旁征博引。我很喜欢他的文笔,完全是文学家在那儿谈科学。请各位留意,碰到赫胥黎的作品,别忘了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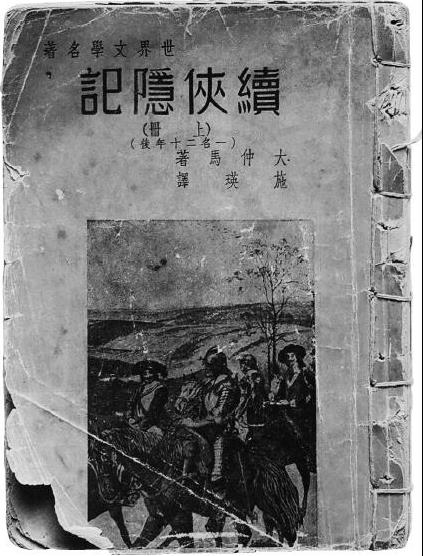
“这是文学上的水、空气,一定要有的。”民国版大仲马小说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