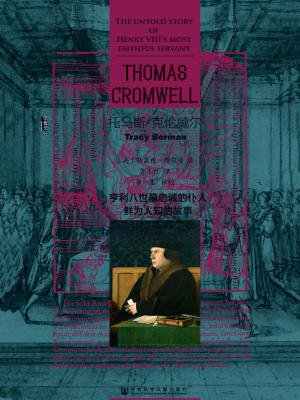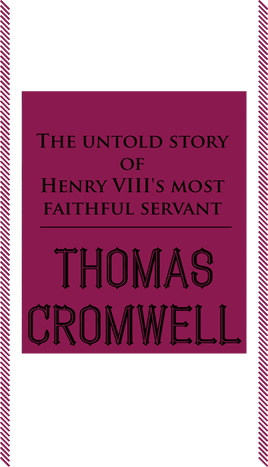
第一章
“一位伟大的旅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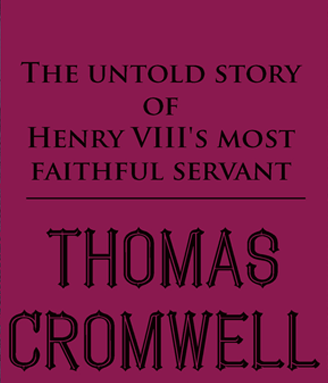
这位后来成为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的出身是如此卑微,以致没有人能够确定他出生的时间或地点。在对16世纪殉道者的记述中,约翰·福克斯把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血统和出身都很卑微的男人” [1] 。他的出生年份最有可能是1485年,这一点如果属实,倒也恰如其分,因为都铎家族正是在这一年掌权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在博斯沃思战场上战胜理查三世(Richard Ⅲ)之日素来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场胜利结束了玫瑰战争,即金雀花王朝两个敌对王室分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使英格兰分裂超过30年之久的战争。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威尔士人、这位王位继承权存疑的兰开斯特派会建立一个统治英格兰并影响欧洲政治、宗教和社会超过一个世纪的王朝。
虽然值得注意,但是1485年8月在遥远的莱斯特郡领地一个新的王朝的开端在生活在帕特尼的人看来一定非常遥远,那里正是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家人居住、谋生的地方。克伦威尔如果不是在这个位于伦敦以西的小村庄,就是在温布尔顿附近出生的。约翰·福克斯记载克伦威尔出生于“帕特尼或者其周边一个身份低微的、名不见经传的家庭”。 [2] 传说克伦威尔的出生地位于帕特尼荒野(Putney Heath)边缘的帕特尼山上,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强盗聚集地。 [3]
克伦威尔家族的祖籍并非位于伦敦西南,而是诺丁汉郡的诺威尔。当时克伦威尔家族既有财富又有地位,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克伦威尔的祖父)大名鼎鼎且备受尊重。1461年,他与族人以及姐夫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起迁至温布尔顿,在那里,坎特伯雷大主教租给他一个漂洗作坊和一栋房舍。
 他的长子约翰搬到兰贝斯成了一个富裕的酿酒商,后来成为大主教的厨师。
[4]
而他的次子沃尔特留在温布尔顿,或许做了他姑父的学徒,因为他将史密斯的姓放进了自己的名字里。
他的长子约翰搬到兰贝斯成了一个富裕的酿酒商,后来成为大主教的厨师。
[4]
而他的次子沃尔特留在温布尔顿,或许做了他姑父的学徒,因为他将史密斯的姓放进了自己的名字里。
沃尔特·克伦威尔(Walter Cromwell)和其妻子凯瑟琳·梅弗莱尔(Katherine Meverell)唯一的儿子便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有记载显示他是三个孩子中最为年幼的。托马斯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孩子,因为他比姐姐们小了许多。在唯一一份提及他母亲的记载中,托马斯不是很确定地说母亲生下他时是52岁。 [5] 同时代的文字记载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凯瑟琳的唯一信息是她是来自德比郡威克斯沃斯的尼古拉斯·格洛索普(Nicholas Glossop)的阿姨,她在1474年左右出嫁时住在帕特尼一位名叫约翰·韦尔贝克(John Welbeck)的律师家里。尼古拉斯比他的表弟大30多岁,这更加证实了托马斯是凯瑟琳所有孩子当中最年幼的。
沃尔特·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从事多个不同但据推测有互补关系的职业,比如铁匠、酿酒商、漂洗工(布料加工工人)。根据当时的资料,沃尔特曾在博斯沃思战役中作为亨利·都铎军队的一名蹄铁匠参军。以他的出身几乎不可能参与最激烈的战斗,但有意思的是他选择了,或者说被选去为进攻一方的都铎军而不是为占优势的国王理查三世军效力。从沃尔特儿子的职业发展来看,推测克伦威尔家族在踏上英格兰土地之后便开始为都铎家族效力是非常合理的。
克伦威尔家族在帕特尼经营一个漂洗作坊长达50年。沃尔特还拥有一间名为“锚”的旅店、一座啤酒厂和两威尔格(60英亩)土地。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密封敕令中,沃尔特被记为一位“啤酒酿造商”。 [6] 作为一位当地商人,他的成功受到认可,经常被叫去做陪审员,1495年被任命为帕特尼的治安官。他很快获得了新的土地,截至1500年,他拥有八威尔格土地(土地面积大到需要两头公牛耕种)。克伦威尔家族宅邸和酿酒厂位于一条名副其实的酿酒巷(Brewhouse Lane)的两端。这条酿酒巷至今仍然连接着帕特尼桥路和泰晤士河。河边是在泰晤士河作业的渔船的停靠码头,这里也是从伦敦返回西萨里以及其他郡城镇与乡村的行人们的驻足地。如果是在现代的帕特尼,河边的一栋房舍售价不菲,但是这个区域在16世纪并没有那么宜居。酿酒巷的另一端紧邻渔场,所以克伦威尔家族的宅邸应该经常受渔场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困扰。
关于宅邸的样子并无文字记载,但是考虑到沃尔特在当地社区的地位以及各种商业所得,他的宅邸应该比帕特尼其他大多数居民的更舒适一些。当时大多数房舍是由木料、枝条和粗灰泥而不是砖块建成的。木质框架表层通常会涂有黑色的沥青以防止腐烂,框架之间是刷白的墙壁。因为房屋主要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易燃,假使沃尔特·克伦威尔的铁匠铺紧邻宅邸的话,他们家的宅邸着火的风险会比其他大多数宅邸更高。普通的房舍通常只有一间房屋,作为厨房、盥洗室、卧室和起居室使用。稍微大一点的房舍,比如克伦威尔家族可能拥有的房舍,也许会有一到两处隔墙来隔开这些功能空间,同时像大多数房舍一样,配有一个室外的厕所。在都铎时期,壁炉及烟囱在较为富裕的家庭得到了广泛普及,取代了常见于中世纪和当时较为贫穷的居民房屋中央的开放式火炉。即使如此,这两种房舍一般阴冷、透风,很多居民冬天会把牲畜牵入室内帮助取暖。诸如长椅、木凳、桌子、木箱之类的家具稀少而简陋。人们在用稻草填充的、满是各种寄生虫的床垫上睡觉。地毯是富裕人家才有的奢侈品,普通人家会在屋内地面撒上灯芯草、芦苇和好闻的草药。这些草药用来遮盖各种难闻的气味,其中有用动物肥脂制成的脂蜡或者灯芯草蜡的气味,也有不常盥洗的居民身上的味道。
安德烈亚斯·弗朗西斯库斯(Andreas Franciscius),一位意大利的旅行者,于1497年11月描述了托马斯·克伦威尔青少年时期所熟悉的伦敦。“它的位置如此舒适宜人,很难找到比伦敦更便利、更有魅力的地方,”他写道,“它屹立于英格兰岛最大的河流——泰晤士河的岸边,而泰晤士河将伦敦一分为二。”弗朗西斯库斯估计当时的伦敦城区方圆不超过3英里,但是他补充道:“伦敦城的郊区是如此广阔,它们极大地增加了伦敦的地域。”他继续描述了伦敦一些较著名的地标:
伦敦筑有雄伟的城墙,其中尤以伦敦城北部最近重修的部分最为美观。矗立在其中的是位于泰晤士河岸边防卫森严的城堡——伦敦塔,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偶尔会在那里居住。还有其他一些宏伟的建筑,尤其是一座横跨在泰晤士河上的大桥,它外观宏伟、交通便捷,由很多大理石桥拱构成,桥上有很多石砌的商店和住宅,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教堂。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好、更壮观的大桥。
因为没有现代防洪屏障的阻碍,所以每天涨潮时场面壮观:“伦敦城离大海60英里,尽管如此,满潮时涌入泰晤士河的海水仍如此汹涌,不仅令河流停滞,还推动河水逆流而上,构成一幅宏伟的图景。”
弗朗西斯库斯继而描述了“很多从事各种机械工艺的工匠作坊”,这些工匠包括像克伦威尔的父亲那样的铁匠。甚至伦敦的食物都得到了这位旅行者的赞许。
他们喜爱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肉类和其他食物,他们烹饪的食物极其丰盛,无与伦比。他们经常甚至过度宴饮,尤其钟爱小天鹅、兔子、鹿和海鸟。他们经常食用羊肉和牛肉,据说这里的羊肉和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主要得益于他们优良的牧草。他们拥有各种各样、数量众多的鱼类,还有海上运来的大量牡蛎。虽不能说每个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喝我之前提到过的“麦芽酒”,并且有各式各样的酿造方式。因为英格兰岛上没有葡萄生长,所以葡萄酒非常昂贵。 [7]
然而,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合弗朗西斯库斯的心意。
所有街道铺设得如此简陋,稍有一点儿水就会变得泥泞,因为大量运水的牛群经过,加上英格兰岛本身降雨丰沛,所以街道经常泥泞不堪。大量气味难闻的淤泥随之形成,这些淤泥总要很长时间,实际上需要将近一年才会消失。因此,居民为了清理这些淤泥和靴子上的污垢,常常在各个房屋的地板上放置新鲜的灯芯草,每逢进入房屋的时候都会在灯芯草上清理自己的鞋子。
同样,他为伦敦人“火爆的脾气和刻薄的性情”而震惊,他也很厌恶伦敦人对自己孩子的轻视和疏于照料。
沃尔特·克伦威尔看似属于这一类型,尤其是在他跟儿子托马斯的关系上。不过他至少为女儿们都找到了不错的夫家,虽然他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出于对女儿们幸福的考量。长女凯瑟琳嫁给了一位胸怀壮志的威尔士律师摩根·威廉斯(Morgan Williams),他的家族由格拉摩根郡迁至帕特尼。摩根的哥哥是内兰德领主约翰·斯凯尔斯(John Scales)的管家,是帕特尼一位有名望的人。凯瑟琳的妹妹伊丽莎白嫁给了一位牧羊的农场主威廉·韦利费德(William Wellyfed),后来他跟着岳父一起做生意。
尽管沃尔特其人在当地社区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经常卷入法律纠纷。1475~1501年,他因“违反麦芽酒法定标准”被庄园法庭处罚6便士不下48次,这意味着他一直在用水勾兑自售的麦芽酒。
 15世纪以来,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日益常见,促使酿酒者行会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条例,确保所有“从事酿酒工艺者”生产“优质的麦芽酒,使酒的浓度和纯度与麦芽酒的价格相称”。此外,行会还任命了正式的品酒师对该城的酿酒商进行随机抽查。所以沃尔特的这种牟利方式很快被发现了。
[8]
他的妻子可能协助他经营酿酒生意:酿酒是为数不多的鼓励妇人们参与的行业之一。诗人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创作了一个脾气暴躁的酿酒作坊女主人的讽刺形象,她醉酒的滑稽姿态给这类从事酿酒业的女性带来了(往往不是她们应得的)不好的名声。虽然当时有像沃尔特和他的妻子这样的本地酿酒商,但英格兰真正的优质酿酒中心仍然是修道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出身酿酒作坊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手策划了修道院的衰败,进而给整个国家的酿酒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15世纪以来,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日益常见,促使酿酒者行会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条例,确保所有“从事酿酒工艺者”生产“优质的麦芽酒,使酒的浓度和纯度与麦芽酒的价格相称”。此外,行会还任命了正式的品酒师对该城的酿酒商进行随机抽查。所以沃尔特的这种牟利方式很快被发现了。
[8]
他的妻子可能协助他经营酿酒生意:酿酒是为数不多的鼓励妇人们参与的行业之一。诗人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创作了一个脾气暴躁的酿酒作坊女主人的讽刺形象,她醉酒的滑稽姿态给这类从事酿酒业的女性带来了(往往不是她们应得的)不好的名声。虽然当时有像沃尔特和他的妻子这样的本地酿酒商,但英格兰真正的优质酿酒中心仍然是修道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出身酿酒作坊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手策划了修道院的衰败,进而给整个国家的酿酒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沃尔特·克伦威尔的违法活动并不止酿酒一项,他还时常因为放纵牛群在公共土地上任意吃草而被申饬。他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发生在1477年,他因“抽取”了一名叫作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chell)的男子的“血液”而被判犯有人身侵犯罪,并被处以罚金20便士。沃尔特和他的父亲约翰同样也因为过度放牧给帕特尼的公共土地“增加负担”、过度采割荆豆和荆棘而经常被起诉至当地法院。 [9] 1514年,因为在当地社区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用欺骗手段”修改与租赁期相关的文件之后,沃尔特最终被逐出承租的庄园。 [10] 他所有的土地都被没收,并且之后的文字记载中再未提及他,这说明在这之后不久他可能就去世了。
很多年后,沃尔特的儿子托马斯在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中暗示他继承了父亲身上一些不好的品质。他向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吐露“他年轻时是多么无法无天”。 [11] 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也曾说“克伦威尔年轻时行为不端,在一次入狱服刑后被迫离开英格兰”。 [12] 虽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但在当时一个父亲是可以避开合法程序把自己的儿子送入监狱的。
虽然没有其他关于托马斯童年和教育经历的记载,但是考虑到沃尔特在社区的地位以及他的多项收入来源,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为儿子的教育做了一些投资。但是根据1715年出版的关于克伦威尔生平的记载,“这位伟大男人的父亲从事的工作如此卑贱,没有能力为儿子的教育投入许多”。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的编年史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
 也曾暗示克伦威尔是自学成才,他写到克伦威尔的“满腹学识,是通过勤恳、刻苦的努力积累而得”。当时,孩子们在7岁到9岁之间离开家乡去“其他人家辛苦劳作”是常见的现象。这些学徒期通常持续7年或者9年,“在此期间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虽然并没有关于克伦威尔当学徒工的记载,但是霍林斯赫德写到“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13]
也曾暗示克伦威尔是自学成才,他写到克伦威尔的“满腹学识,是通过勤恳、刻苦的努力积累而得”。当时,孩子们在7岁到9岁之间离开家乡去“其他人家辛苦劳作”是常见的现象。这些学徒期通常持续7年或者9年,“在此期间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虽然并没有关于克伦威尔当学徒工的记载,但是霍林斯赫德写到“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13]
有文件记载暗示了克伦威尔家的这两个男人之间关系紧张。如果说托马斯跟他的父亲很像,那么显然这并没有帮助他赢得父亲的喜爱,或许正是他跟父亲之间的一次争吵促使他决定于1503年前后离开帕特尼。与克伦威尔同时代的意大利小说家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称克伦威尔逃离了父亲。 [14] 约翰·福克斯则描绘了一个美好得多的图景,称“在其成长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和成熟,他脑海里冒出了要去游历他国、一览外面的世界并增加阅历的想法”。 [15]
仅仅逃离家还不够,托马斯干脆离开了英格兰。在那个人们鲜少冒险迈出本乡边界、视那些由别郡来的人为“外地人”的时代,离开家乡是一个极为大胆且冒险的事情,对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来说尤为如此。于1602年出版的关于托马斯生平的一部剧作中,已经梦想着赚取财富的年轻的克伦威尔这样告诉父亲:“有一天我会视金钱为粪土……为什么要任由我的出身阻挠我向上的心志呢?”
 年轻人梦想的图景是引人神往的。克伦威尔在离开伦敦之前很有可能已经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伦敦到处都是从国外来的商人,正如弗朗西斯库斯所描绘的那样:
年轻人梦想的图景是引人神往的。克伦威尔在离开伦敦之前很有可能已经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伦敦到处都是从国外来的商人,正如弗朗西斯库斯所描绘的那样:
来自世界各地的,不仅有威尼斯的,还有佛罗伦萨的、卢卡的以及很多来自热那亚、比萨,来自西班牙、德国、莱茵河畔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带着极大的热情来这里进行贸易。但是英格兰岛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羊毛以及毛织物,还有白铅,因为相比其他国家,英格兰更加盛产这些商品。通过大海和泰晤士河,各种各样的商品可以运到伦敦来,也可以由伦敦运往其他地方。 [16]
克伦威尔或许通过他父亲的生意跟这些商人中的一位有了联系。
至于他是如何攒够船费的尚且不清楚:虽然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偷渡者的假想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同样有可能找到了一份船上的工作。一艘大的轮船,比如亨利八世命途多舛的旗舰“玛丽·罗斯”(Mary Rose)号,船上人员最多能有400人,其中包括仆人、厨师、事务长以及医生,还有船员和军官。克伦威尔可能找到了一个稍微低级的工作。正如福克斯后来所说:“没有什么是他靠着智慧和勤勉不能达成的。” [17]
克伦威尔首先去了尼德兰,然后从尼德兰旅至法国。史料鲜少记载他具体是在哪里生活,以及他是如何赚取足够的钱财生存下来的。直到1503年秋末,他作为法国军队的一分子、远征意大利的时候才第一次有了关于他的记载。他的参军时限至今尚未可知,但后来他能够展示出对于法国军事体系超乎寻常的详细了解,说明他在随军远征意大利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据他后来的对头——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所说,克伦威尔当时是一名普通士兵
 。虽然苏格兰士兵经常会为法国征战,但是这一时期这样做的英格兰士兵极为少见。克伦威尔或许是从14世纪在意大利征战获得财富的英格兰雇佣兵那里受到了启发。但如果他以为为法国征战是一条通往财富和荣誉的路,那么他就要失望了。
。虽然苏格兰士兵经常会为法国征战,但是这一时期这样做的英格兰士兵极为少见。克伦威尔或许是从14世纪在意大利征战获得财富的英格兰雇佣兵那里受到了启发。但如果他以为为法国征战是一条通往财富和荣誉的路,那么他就要失望了。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意大利城邦就成为法国和西班牙激烈的权力之争的焦点。而最近的一轮战事则发端于四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称对米兰和那不勒斯公国拥有所有权。在此之前,法国和西班牙军队联手占领了那不勒斯,但是他们在占领区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争端,继而引发了战争。1503年4月,西班牙在切里尼奥拉大败法国,然而法国军队并没有灰心丧气,于11月中旬在那不勒斯以北约60千米处的加里利亚诺河口聚集。西班牙数次试图渡河,终于在12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成功偷袭法军。法国军队驻扎在泥泞而不健康的环境中,因疾病而衰弱,不敌西班牙步兵中的长矛兵、剑士和火绳枪手,尽管大名鼎鼎的法国骑士“好骑士”巴亚尔(Bayard)在加里利亚诺桥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法国还是被逼退至加埃塔并宣布投降。
这场战败以及战败前法国军队连续数周的糟糕境遇或许让克伦威尔决定尽早放弃军旅生涯。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军队,不过他决定留在意大利而不是以战败者的姿态返回英格兰。他生活在意大利历史上文化最兴盛的时期,这对他的性格、信仰和兴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拉斐尔(Raphael)、贝利尼(Bellini)、提香(Titian)正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创制杰作,博吉亚家族(Borgias)主宰着教宗国的政治与宗教生活,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则开始在佛罗伦萨政府施加影响。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意大利保留了它的独特气质,相比道德,彼时的意大利社会更注重美学。其夺目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与社会环境和民族脾性引发的普遍的暴力与流血事件呈鲜明对比。白天文化和政治精英进出的精美广场,到了夜晚就变成斗殴、持械伤人和凶杀事件的案发地。对年轻的克伦威尔来说,这是一个残暴又具有启蒙性质的训练场。
再次出现关于克伦威尔的书面记载是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艺复兴是受古典时代影响的一次文化、思想的大爆炸,它变革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和宗教。文艺复兴的影响如此之大,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连接中世纪和近代世界的桥梁。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在艺术中探寻现实主义与人类情感。有着令人惊异的精密细节的作品取代了中世纪高度程式化的绘画和雕塑,并赋予题材以生命力。
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够成为意大利所有文艺复兴城市中最有生机活力的一个,并且拥有乔托(Giotto)、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波提切利(Botticelli)等诸位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强大的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有了精美的绘画、壁画、雕塑和建筑的装饰,佛罗伦萨成为无与伦比的美都,闻名全世界。克伦威尔到达佛罗伦萨的具体日期不详,但应该早于1504年6月,因为这时他已经进入强有势的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家弗朗切斯科·弗雷斯科巴尔迪的府邸。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自12世纪以来就是有名的金融家,在佛罗伦萨公共事务中声名日盛的同时,他们也在英格兰建立了收益颇丰的商业往来。到了13世纪末,他们成为王室银行家,赞助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和二世的战争。弗朗切斯科是“一个非常忠诚、正直的商人”,“非常富裕”并在整个欧洲市场“拥有很大的生意”。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伦敦,不过克伦威尔是在他返回佛罗伦萨的一次旅途中与他相遇的。当时的小说家班戴洛描述了这位商人是如何遇见在街上乞求施舍的克伦威尔(“一个可怜的年轻人”)的。当弗朗切斯科停下来跟他说话的时候,克伦威尔乞求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他。弗雷斯科巴尔迪见他虽然“衣衫褴褛”但“举止中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就产生了怜悯之情。当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来自他熟悉并且热爱的英格兰时,就询问了年轻人的姓氏。“我叫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如是回答,“是一个布料加工工人的儿子。” [18] 克伦威尔接着给他讲了自己是如何从加里利亚诺战役中死里逃生的,无需多言,这位富商显然已被说服:他带克伦威尔回到自己的府邸,为他提供衣食和居所。
虽然未经验证,但这种说法是可靠的。班戴洛的小说基于真实事件,克伦威尔后来的生平也证实了他拥有善于赢得精英群体好感的杰出能力。私下里熟识克伦威尔的夏普伊和雷金纳德·波尔的记述也佐证了这一点。唯一不一致的地方是班戴洛笔下的克伦威尔称他的父亲是一个剪切工(一个剪羊毛的人)而不是一个铁匠,也没有提及他父亲的其他职业。这一出入或许是因为克伦威尔的母亲在沃尔特死后改嫁了一个剪羊毛的工人。 [19]
克伦威尔显然没有辜负弗雷斯科巴尔迪对他的信任,他忠诚且有力地服侍着他的主人。班戴洛将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斗志非常昂扬、机智、果断的年轻人,他非常清楚如何迎合他人的想法,当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他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好地掩饰自己的情感。” [20]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磨砺而成的这些性格特点在他回到英格兰之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在服侍弗雷斯科巴尔迪的过程中,他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见识。那个时期佛罗伦萨还是一个共和国,政客、外交家、人文主义学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共和政府的积极分子。或许可以推测克伦威尔了解,甚至可能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方法论,但是几乎可以断定的是两人并不相识:克伦威尔当时是共和国极为卑微的一个居民,不可能跟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有交集。
弗雷斯科巴尔迪以“好客”和“生活奢华”闻名,所以克伦威尔在他的府邸生活得很舒适。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后来因好客而出名的克伦威尔。作为佛罗伦萨名门望族中最富有、最显赫的一员,弗朗切斯科雇用了最好的厨师、乐师和表演者来宴请、招待他的宾客。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利润最丰厚的生意之一是酿制托斯卡纳红酒,自14世纪早期开始他们便精于酿制此酒,后来还进贡给英格兰宫廷供亨利八世本人享用。弗雷斯科巴尔迪酷爱艺术,他与大名鼎鼎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有一个互惠的约定,凭此约定拿红酒来换画作。因此克伦威尔曾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最好的作品之间,难怪在那之后他会如此热爱艺术。
弗雷斯科巴尔迪在意大利各地为生意奔走的时候会带上他的这位英格兰侍从,直到最后把克伦威尔留给了一位威尼斯商人。没有迹象表明克伦威尔对此有异议,因为弗雷斯科巴尔迪给了他丰厚的饯别礼物——16个金杜卡特和1匹壮马。枢机主教波尔证实后来克伦威尔被一位他熟识的威尼斯贸易商雇为会计。 [21]
此后克伦威尔的行踪无法确定,他很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离开了意大利,在欧洲其他地方游历了一段时间。可以确定的是他作为布料商人在尼德兰(Netherlands)待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威尼斯和安特卫普贸易联系密切,这可能促使他多次游历。对这位未来的英格兰政客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之都就是最好的训练场。安特卫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化都市,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所有贸易国家的商人。英格兰的毛织品和布匹有半数经由这座城市出口。克伦威尔亲身经历了商人冒险家公司——一家由英格兰主要海外商人组成的公司——尝试将这些出口原材料制成成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经济努力。过了一段时间,克伦威尔开始为安特卫普英国会馆(The English House)的商人效力,随后他自己成为一名独立的贸易商人。
许多年之后,一位名叫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yot)的商人回忆说,“自1512年在米德尔堡的辛松市场我就感受到了克伦威尔的热情和真诚”。 [22] 米德尔堡是位于尼德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是中世纪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商业往来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从英格兰贸易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来看,克伦威尔完全有可能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他在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商业家族之一的府邸的工作经历也增加了他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克伦威尔可能也获得了一些法律上的经验。虽然从未受过训练,但是他肯定有从事法律这一行业的天赋,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因在法律事务方面的知识和本领而出名。
克伦威尔大概在1512年夏末或秋初返回了英格兰。两年之间,年近30的他就已经在伦敦商界和法律界站稳了脚跟。从亨利八世官方文件的一次偶然提及可以看到,克伦威尔在回到英国之后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其律师生涯。克伦威尔的签名出现在一份1512年11月前后的文件中,文件内容涉及白金汉郡大小金布尔庄园及地产产权。 [23] 在他整个律师生涯中,克伦威尔专攻产权转让。早年间,他的很多客户都来自其生意上的人脉。
但是克伦威尔四处游历的日子并未结束。1514年,他再次来到尼德兰,在一些主要的贸易中心(特别是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开始自己做起了生意。在积累生意经验的同时,他也建立了一个将在未来对他大有助益的交际圈。在此处,他也对欧洲经济和政治事务形成了极好的基本认知。他学会了几种语言,可以熟练使用法语和意大利语,通晓西班牙语,可能也会德语。对意大利的钟爱伴随了他一生,他收到的很多国外信件都是用意大利语写就的。吝于夸奖的圣罗马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后来也坦言:“克伦威尔英语口才极好,除此之外他的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说得相当好。” [24] 克伦威尔也熟谙古典文学,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后者是非常难得的成就。后来成为克伦威尔死敌的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也坦言克伦威尔经常对他“直言不讳,不管跟我讨论什么他都非常自信,无论是希腊语、拉丁语还是其他,他知晓的都跟我一样多。” [25]
虽然关于克伦威尔这一时期的生活,当时的文献能够提供的只有零零散散的细节,但从中可以看出在1514年克伦威尔还返回了意大利。根据位于罗马的英格兰救济院——至圣三一和圣托马斯救济院(the Most Holy Trinity and St Thomas)的记载,克伦威尔1514年6月曾在那里居住。至圣三一和圣托马斯救济院建于1362年,旨在照管“来自英格兰的贫穷的、体弱多病的、需要关爱的不幸旅人”,克伦威尔旅居于此的时候,该救济院已经成为罗马接待英格兰来客的主要中心。它每年接待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不过克伦威尔旅居于此更有可能是由于生意需要而非精神需求。根据梵蒂冈城档案馆的文件,克伦威尔这时是枢机主教雷金纳德·班布里奇(Reginald Bainbridge)的代理人,在由教廷建立的最高宗教事务裁判所处理英格兰教会事宜。
1514年夏,克伦威尔回到英格兰。一份日期为8月26日的文件上的签名被认为是他的。文件与约克大主教有关,文卷编辑者描述文件的背书部分写有“一些线条,明显是刻意的字迹练习”。 [26] 这(虽未经考证)提供了一个青年克伦威尔的迷人形象,他为了让自己的字迹看起来优美、老练而不断练习。如果这真的是他的字迹,那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谜题。这位刚刚回国的冒险者在本国鲜为人知,他是如何介入英格兰最重要的一位神职人员的事务的呢?这说明克伦威尔的社交网比当时资料所披露的要大。
无疑,在欧洲大陆的几年,克伦威尔由一个未受良好教育、早熟并混迹街头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人脉广且成功的商人。后来克伦威尔称自己是“世间伟大的旅行者”也不无道理。 [27] 他的天资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正如福克斯所说:“他的记忆力超群,无论学什么都可以记住,这也是他最为出众的能力。” [28] 同样,霍林斯赫德在描述他时也说“有如此超群的记忆力,有如此胆量和韧性,可以利用手中的笔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在人们看来他经验丰富,不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 [29] 他有随军服役并参加作战的经历,又在几个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工作过,在文艺复兴期间亲眼见证了文化和思想的异常繁荣,并且吸收了当时开始在北欧扎根的一些激进的宗教思想。他的人生历练可谓卓越。
克伦威尔在意大利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这段经历培育了他对艺术、文学、音乐和精美器物的终生热爱。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非常有感染力。很多年后,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枢机主教沃尔西的随身教士,曾写信给他:“很久之前你就答应借我彼特拉克的《凯旋》(‘Triumphs of Petrarch’),希望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意大利人,我恳请您让奥古斯丁先生的侍从给我送来,如果您有意大利语的《廷臣论》(
Cortigiano
)就更好了。”
[30]
意大利作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一直被认为是对克伦威尔有特别影响的人。克伦威尔可能获得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君主论》的早期手稿。这本最终于1532年出版的著作使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与无情、不择手段的治国之道画上了等号。

作为一个伦敦人,克伦威尔对一切意大利事物的热爱是极为不寻常的。安德烈亚斯·弗朗西斯库斯在游历这个都城时震惊地发现它的居民“不仅看不上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带着难以抑制的憎恶咒骂他们”。 [31] 这一时期另一位意大利旅行者也证实了这一点:“英格兰人大爱自己以及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眼里只有英格兰和英格兰人;每当看到一个英俊的外国人,他们会说‘他长得像英格兰人’……他们对外国人有很强烈的反感,幻想他们一旦踏足自己的岛屿,就必然是为了将其据为己有、夺取英格兰人的物资。” [32] 克伦威尔要心胸宽广得多,游历让他比大多数同胞更加文雅、好奇和开明。他是一个真正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克伦威尔在国外的这几年经历与在帕特尼他父亲的啤酒作坊做学徒的时日堪称天壤之别,他拥有只有少数统治者和极少数大臣花费一生才能掌握的关于地理、人文和时政的见识,因此没有常见于其英格兰同胞身上的成见和偏见。他的游历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他学会了质疑一切、颠覆传统并且行事求新。他的经历教会他不要急于相信(如果还有信任可言的话),但是同时他也真正关心他人,他的平易近人在同侪当中罕有其匹。他从默默无闻到站在辉煌事业的顶点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优点。正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后来所评述的:“虽然卑贱的出身和生活的匮乏是他养成能够立身于世的优点的较大障碍……但是凭着异常卓越的才智和勤劳刻苦的心性……他逐渐培养了如此充分、熟练的权衡重要事务的理解能力和本领,以至于旁人认为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任何一个职务,他都能胜任。”霍林斯赫德确信克伦威尔的旅行对他后来的事业十分有益,因为他从中观察到了“本国以及其他各个国家和政府的运作原理”。 [33]
1514年回到英格兰后不久,克伦威尔娶了伊丽莎白·威廉斯(Elizabeth Williams),伊丽莎白的旧姓是威基斯(née Wykys)。他能够寻得如此佳偶显示出他所取得的成就。伊丽莎白是王室护卫托马斯·威廉斯(Thomas Williams)的遗孀。她的父亲亨利·威基斯(Henry Wykys)跟克伦威尔的继父从事同一行业,都是帕特尼的羊毛商人,有可能正是这两人安排了这门婚事——或者至少介绍他们相识。亨利·威基斯曾是亨利七世的引见官,这给托马斯提供了一个薄弱但有价值的宫廷关系。他的岳父也帮助他在英格兰的布料生意中立足。有记录显示伊丽莎白是一位坐拥财富与地产的女性,这可能是克伦威尔娶她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在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克伦威尔个人的财富快速增长,其速度远比他仅靠自己所能达到的要快得多。
如此博学且也在岳父家里做羊毛和布料生意的克伦威尔同样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商业代理人的地位,这是一个没有明确业务范畴界定的角色,明显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训练,但可能涉及包括借贷在内的多种业务。这个角色同样也让他进入了英格兰的法律界。他充分利用这次转行的机会,努力以律师为自己的主业。鉴于在此之前他的经验都来自跟英格兰有不同法律系统的其他国家,他能如此之快地在法律事业上获得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克伦威尔的知识不是在大学里学来的,而是从伦敦现有的已出版的法律书籍或者同时代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人那里学得的。加上在欧洲的人脉和训练,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开始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
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生育了至少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安妮(Anne)和格雷丝(Grace),还有一个儿子叫格雷戈里(Gregory)。
 他们的出生日期没有记载,不过正如大多数历史中常见的,跟儿子年龄相关的证据比关于女儿的要多。通常认为格雷戈里大约在1520年出生。
[34]
同时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了安妮,这或许说明她是两个女儿当中年长的那个。
他们的出生日期没有记载,不过正如大多数历史中常见的,跟儿子年龄相关的证据比关于女儿的要多。通常认为格雷戈里大约在1520年出生。
[34]
同时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了安妮,这或许说明她是两个女儿当中年长的那个。
他们一家生活在位于伦敦城东部的芬丘奇(Fenchurch),可能租住在圣加百利一个小的教区教堂附近。这一区域经常有许多商人光顾——附近有布料工人、锡匠、五金商——所以克伦威尔很容易接触到很多生意客户。
尽管他很快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但是克伦威尔很快又踏上了旅程。1517年他收到一位来自林肯郡波士顿的熟人——市政官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请求帮助的来信。这两个人可能是在生意往来中认识的,当时波士顿是汉萨同盟的一个城市。汉萨同盟是一个主导北欧贸易的强大的商人联合体。罗宾逊的同乡杰弗里·钱伯斯(Geoffrey Chambers)正要代表波士顿圣博托尔夫教堂(今天当地人热切地称之为“波士顿之桩”)圣母公会去一趟罗马,目的是获得教宗的准许以出售赎罪券。这是该镇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所以该镇官员迫切需要确保其能够继续。罗宾逊问克伦威尔是否可以陪同钱伯斯前往。虽然克伦威尔“对宗教事务缺乏兴趣与良好的判断力”,因而无法直接出面说服教宗,但他游历甚广,精通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事务,这一点相比之下更为罗宾逊所看重。
[35]
克伦威尔或许急于冒险,便欣然同意。他跟钱伯斯在安特卫普见面,一起前往罗马。
 他们的出行显然很气派,因为整个旅程花费竟高达1200英镑——比今天的45万英镑还要多。
他们的出行显然很气派,因为整个旅程花费竟高达1200英镑——比今天的45万英镑还要多。
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于1517年到访极盛时期的梵蒂冈城。米开朗琪罗已经于5年前完成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这一杰作对西方艺术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另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于1508年开始装饰教宗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的居所。教宗宫殿四个接客室装饰有大量的系列壁画,这些壁画是如此精美,以至于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Leo Ⅹ)在1513年成为教宗之后留用拉斐尔和他的团队继续完成壁画创作。当克伦威尔和罗宾逊抵达罗马的时候,这项工作应该仍在进行中,但是他们在拜访利奥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了一些已经完成的壁画。
克伦威尔做了一个可以绕开通常漫长乏味的等待、获得教宗接见的计划。当他们到达罗马的时候,他发现教宗即将开始狩猎之旅,所以他暗自等待教宗回来并通过一场英格兰“三人联唱”的表演给教宗以惊喜。克伦威尔知道教宗喜爱“新的、流行的、不常见的小食和精致的菜品”,于是他给教宗准备了一些精选的英式甜点和果酱,并称“在英格兰这些通常是只供国王和王子食用的”。 [36] 教宗被他打动,立刻批准了公会所有的请求。1518年2月24日签署的一份教宗训谕给波士顿公会颁发了许可,允许其继续出售利润颇丰的赎罪券。虽然这一事件的细节是在事情发生大约50年后由约翰·福克斯提供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克伦威尔为获得这一许可做了努力并且完全获得了成功。这是他第一次显示出在与社会上最显贵的人交往时的技巧和胆识。他的经历给了他与其卑贱出身不符的自信,但是他一定还有一种天生的傲慢——甚至是狂妄——能够劝服有权力的人听从他的要求。
这一事件或许还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在证明教宗是多么容易被人哄骗并因此答应他人诉求之后,克伦威尔可能对教宗权威和宗教社团产生了一种轻蔑,这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发展成强烈的敌意。正如编年史家霍尔(Hall) [37] 那句有名的评述所说的那样,他后来对“一些高级教职人员的自命不凡”怀有强烈的憎恶。此外,福克斯说克伦威尔曾在漫长的返程途中默记、研读伊拉斯谟(Erasmus)刚出版的拉丁译本的《新约圣经》以排解旅途的乏味。显然,从那时候开始,克伦威尔对《圣经》的理解就出奇地好,这种理解持续了一生。对《新约》教义的深刻认识或许也为克伦威尔后来的福音主义信仰埋下了种子。鉴于这一信念诞生在去罗马天主教中心寻求获批出售赎罪券——一种改革派基督徒尤为反对的活动中,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
但在当时,当克伦威尔和钱伯斯乘胜而归,返回英格兰的时候,这一在罗马诉求获批的事迹极大地增添了他的资历。福克斯将克伦威尔描述为“在向各地发行并推动波士顿赎罪券的事业上……一个伟大的行动者”。 [38] 他决定宣传自己的成功以让他的声誉达到能够有效影响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的地步。如果教宗可以任他如此巧妙地摆布,那么英格兰的国王或许也可以。
[1]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5.
[2]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3] 1618年对温布尔顿庄园的一项调查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它描述在那个地方的“一座古老的房舍叫史密斯的商店,位于从里士满到旺兹沃思的大路西侧”。Walford,E.,‘Putney’, Old and New London ,Vol.6(1878),pp.489-503.
[4] 这是帝国大使夏普伊所说的。目前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的,因为同时代的其他资料中没有提及此事。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5]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68. 他在争论时就亨利的“大事”以及阿拉贡的凯瑟琳是否还能生下一个儿子进行发言。
[6] Calendar of the Close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Henry Ⅶ ,p.18.
[7]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p.188-190.
[8] Hornsey,I., 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 (Cambridge, c .2003),pp.321-322.
[9]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4.
[10]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2-4.
[11]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13] Anon., Life of Thomas Lord Cromwell ,p.3;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 pp.190,196;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14] Payne,J.(ed. and trans.), 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 ,Vol.Ⅳ(London,1890),p.107.
[15]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23.
[16]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89.
[17]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23.
[18] Payne,J.(ed. and trans.), 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 ,Vol.Ⅳ(London,1890),pp.106-107.
[19] Foxe, Actes and Monuments ,Book II,pp.419-434. This is repeated in 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20] Payne,J.(ed. and trans.), 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 ,Vol.Ⅳ(London,1890),p.107.
[21]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18-19.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218;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11. 辛松市场是尼德兰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2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Part i,no.1473.
[2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25] Muller,J.A.(ed.), 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 (Cambridge,1933),p.399.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no.3195.
[27]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03.
[28]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23.
[29] 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346.
[31]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90.
[32]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96.
[33] 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34] 此前一直认为格雷戈里于1528年进入了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这是不准确的。这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格雷戈里可能早在1514年就已出生。事实上,格雷戈里于1528年被安排了一位来自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他本人并没有去那里。Pratt,J.(ed.), 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8 vols.(London,1877),Vol.V,p.73.
[35] Pratt,J.(ed.), 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8 vols.(London,1877),Vol.V,pp.363-365.
[36] Pratt,J.(ed.), 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8 vols.(London,1877),Vol.V,p.364.
[37] Hall,E., 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p.838-839.
[38] Pratt,J.(ed.), 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8 vols.(London,1877),Vol.V,p.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