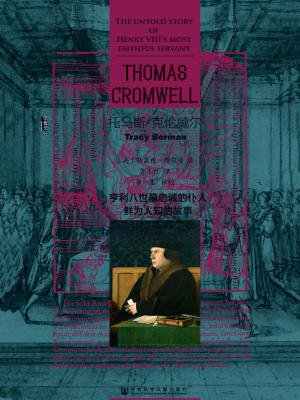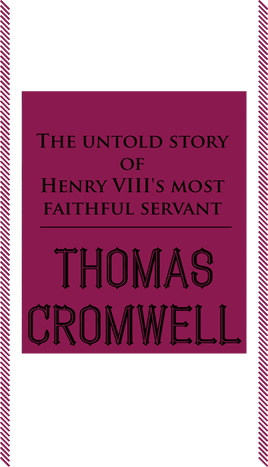
第二章
枢机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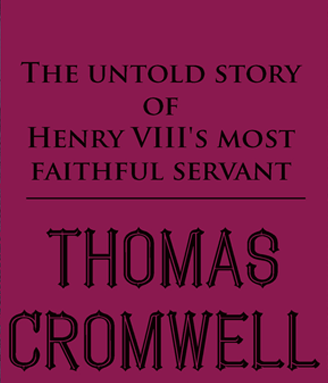
克伦威尔1517年到访罗马是他最后一次有文字记录的国外旅行。在那之后,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在英格兰的事业上。根据当时的一份资料,他在这一时期对自己家族关系的利用并不亚于对商业人脉的利用。沃尔特·克伦威尔兄弟的儿子,亦即托马斯的堂兄罗伯特当时已经成为巴特西教区牧师,直属于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托马斯·沃尔西是约克大主教、英格兰大法官,也是亨利八世最亲近的顾问。
沃尔西是一位旅店老板的儿子,跟克伦威尔出身相仿。他比克伦威尔年长约15岁,大约在 1470年或1471年出生于伊普斯威奇。不久之后,他的父亲成了一个屠夫,正是这个屠夫的身份让年轻的沃尔西在随后的几年受尽嘲讽。不管他在宫廷里如何高升,他的贵族对头总会嘲笑他是“屠夫的儿子”。
虽然出身卑微,但沃尔西还是受到了极好的教育,这或许得益于他富有的叔叔的资助。沃尔西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15岁的时候就从牛津大学毕业,获得了“小学士”的绰号。他继续自己的学业,在莫德林学院攻读神学,对于一个在政治领域有野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不过对沃尔西来说,宗教和政治一直都是相互交错的——无论是在他内心里还是在他的事业中。他的首次重大突破是在1507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王室御用牧师。他很快利用自己的职位,与宫廷中“他认为是枢密院最得意的和最受国王重用的” [1] 人结为同盟。不久,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经验。
沃尔西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博学的人。他完全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宗教范围内,听任亨利八世的差遣、从事各种外交活动。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吹嘘说他仅用三天半就完成了对身在佛兰德斯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的访问,惊艳了国王。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改革家,将沃尔西描述为“一个有欲望、有勇气、身强体壮的人”,沃尔西处理繁重工作的能力让人震惊。 [2] 在亨利八世1509年继位之后,沃尔西平步青云。
“未来,整个世界都会讨论他”,亨利17岁继位的时候,威尼斯大使曾以其非凡的眼力如此预言。每个人对这位热情洋溢、魅力非凡、睿智英俊的新王——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君主赞不绝口。“如果你们见到也会抑制不住流下喜悦的泪水,这里所有人都为能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王而欣喜,他们满心祈愿他的安好”,廷臣蒙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兴致勃勃地说。“天地为之欢喜……贪婪被驱逐,强夺被制止,慷慨的手大方地施舍财富。吾王渴求的不是黄金、宝石和贵重的金属,而是美德、荣耀和不朽。” [3]
新王的体格也在宫廷里鹤立鸡群。身高6英尺2英寸的亨利仪表堂堂,(直至晚年)身材矫健。他擅长运动,乐于在竞技场上展示他的技能。他继承了外祖父爱德华四世的英俊相貌,被称为“历史上最英俊的君王”“肤色白皙的美男子”。一位威尼斯外交使者1515年到访英格兰宫廷,写了一篇汇报,对新王赞不绝口,称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统治者,比常人要高,小腿矫健,肤色白皙透亮,赤褐色的头发梳成法式,又短又直,圆圆的脸如此美好,若生为女子,一定是一位美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也同样赞美“在1000个贵族同僚中,国王是最高大的,他的力量与他高大的体格相称。他的眼神饱含热情,脸庞俊秀,双颊如两朵玫瑰一样红润”。 [4]
亨利的性情同样具有魅力。他继承了母族——约克家族的魅力和感召力,在几乎各个方面都跟他阴沉、心胸狭窄的父亲截然相反。亨利八世平易近人、聪慧机智、理想主义并且极其慷慨,伊拉斯谟称他是“最有心的男人”。托马斯·莫尔也认同:“国王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他的特别青睐。”威尼斯的大使认为他“谨慎、明智、没有任何恶习”。 [5] 这并非完全属实。虽然可以说亨利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但是总体上他的性情也有较为黑暗的一面。他容易激动、任性放纵且自负虚荣,那令人恐惧、难以捉摸的脾气会吓得廷臣四下逃散。他同样也很冲动,常常随自己喜好突然提升或者贬黜侍者。虽然尚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亨利已经染上了常见于他晚年的那多疑、无情、残忍的性情,但是他的随从们在侍奉他时仍不得不为他转瞬即逝的青睐提心吊胆。
另一个对亨利的统治有很大影响的缺点是他对运动的过度热爱。他酷爱狩猎,经常整天骑马外出,黎明之前出发,夜深了才返回。这爱好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国王青春活力渐失,不得不参加一些略不耗精力的消遣。就在1526年,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淡漠地评述道:“因为整个夏天国王闲暇时都在狩猎……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 [6] 即使是在亨利无意狩猎或者(这更有可能)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通常也只是在上午听弥撒的时候以及晚上晚宴过后关注一下正事。他对冗长的汇报和陈述没有耐心,自己也曾经承认书写“对我而言有些乏味、痛苦”。 [7] 要不是有人数可观的书记员、侍从和顾问大臣负责将王室政策、财政、行政的细枝末节付诸实施,政府事务早已停滞。
亨利天生寻欢作乐的性格给老道的廷臣以机会,这一机会很快便被沃尔西迅速抓住。据说在察觉年轻的国王更热衷于悠闲消遣而不是国家事务之后,他向“安逸的国王”保证“只要有他在枢密院,国王无需利用享乐时间来处理枢密院里的事务”。 [8] 他有策略地发挥国王的作用,在最有利的时候让国王参与进来,正如17世纪教会历史学家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记述的:“沃尔西虽然知道如何让国王纵情享乐,有时也会提示他出面理政。” [9] 这位枢机主教证明自己非常擅长应对各项国家事务。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说:“傲慢且有野心的沃尔西……声称自己能够处理几乎所有公务。”结果,他获得了国王越来越多的信任,并且掌握了超乎寻常的自主权。“事态之严重以至于此,”一位震惊的同时代人评述道,“枢机主教处理所有政事,国王对此毫不过问。” [10]
然而,沃尔西受宠并不只靠他减轻国事重担的能力。极为精明、有识人之能的沃尔西很快感知到亨利需要他身边的人对他绝对忠心和忠诚。他同样也知道他的权力之路取决于如何让自己尽可能对君主有用。据卡文迪什所说,“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满足国王的心意,他知道这是让自己升至高位的一条非常虚荣且正确的道路”。沃尔西因此“得到国王特殊的恩典和宠信,每日在宫廷陪侍在国王左右”。最终,“国王对他心生喜爱,尤其认为他是所有廷臣中最忠诚、最甘心乐意的,且他不论如何只推进国王的意旨和意愿。国王因此把他当作一个合用的工具,用来实现他的筹谋,满足他的娱乐,并且让他更接近自己,给他如此高的尊崇,以至于他受的尊荣和宠信使得其他所有廷臣都失去了原有的宠信。”虽然威廉·廷代尔不是沃尔西的崇拜者,但他也承认沃尔西“顺从且有用,并且在所有消遣和娱乐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11]
沃尔西在如何赢得国王宠信的这门学问上可谓大师,而克伦威尔也将作为他的门徒从中受益匪浅。一系列关键的教会任命成为沃尔西自身迅速得权的标志,其顶点是他1514年8月成为约克大主教。一年后,他被封为枢机主教,甚至有流言称他有成为教宗的野心。时人很快就认识到宫廷真正的权力之源在哪里。伊拉斯谟也在亨利的宫廷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形容沃尔西“事实上”的统治“更胜于国王本人”。威尼斯大使朱斯蒂尼亚尼(Giustiniani)称沃尔西是“尊敬的枢机主教,这个国家所有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并且是一个“就权威而言堪与国王相比”的男人。亨利八世本人的举动也加深了这一印象。1515年他授意教宗利奥十世“重视沃尔西的话,一如这些话是从国王本人口中说出的”。 [12] 至此,沃尔西作为亨利宫廷首席大臣的地位完全确立。
沃尔西的晋升如此迅速,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的府邸众人没能跟上节奏,因此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值得信任的仆人。当时并不缺少有野心且愿意接受聘用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有了多达400个仆人。同时,他开启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宏大的建筑计划,仅有国王的宫殿可与之匹敌。他最豪华的府邸是汉普顿宫,这座杰出的建筑里置满了珍贵的艺术作品。也难怪嫉妒他的廷臣开始议论说沃尔西的奢华使国王黯然失色。“他几乎在同一时间担任如此多的公职,并变得如此高傲,以至于他开始自视与国王并驾齐驱”,一位怀有敌意的时人如此说。
很快他开始使用金色的座椅和金色的软垫,铺金色的桌布,他徒步出行的时候把他的帽子——枢机主教品级的象征——给仆人拿着走在前面,并且像举神像一样高高举起,在举行礼拜的时候,他把帽子放在国王小礼拜堂的祭坛之上。沃尔西因其傲慢和野心招致了来自全国的憎恶,因为他对贵族和普通大众的不友善,他们对他的虚荣产生极大的反感。他确实为每个人所憎恶,因为他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担任英格兰几乎所有的公职。
伊拉斯谟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所有人都畏惧但几乎没有人爱戴”他。 [13]
截至当时,没有人限制沃尔西的权力,1515年年末亨利任命这位枢机主教为大法官,证实了他对后者的钟爱。这一任命惹怒了沃尔西的同僚,他们憎恨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这位“屠夫的儿子”手里。1516年5月,托马斯·阿伦(Thomas Alen)向他的侍主什鲁斯伯里伯爵汇报宫廷里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14] 这位新任大法官几乎没有做什么去迎合他的同僚。沃尔西不咨询共事的大臣,只征求国王的准许。他的策略是“在他进一步确定或者决定最应该满足谁的意愿或者听从谁的意见之前,先让国王知晓所有(本该由大臣经手的)事情,以最大限度地赢得国王的欢心”。 [15] 虽然他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策略的危害也将暴露出来。
对克伦威尔开始服侍沃尔西的时间的判定多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一些历史学家推断最早是1514年,而另一些推断最晚是1525年。不过,历史学界一致认为两人是在1516年结识的。
 罗伯特·克伦威尔有可能帮助了他的堂弟成为大主教约克坊——沃尔西在伦敦的宏伟官邸的管家。但直到克伦威尔1518年从罗马返回英格兰后,他才作为枢机主教的门徒崭露头角。1519年他成为沃尔西个人理事会的一员——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从那时起,他开始穿黑色和褐色的天鹅绒制服,表明他是服侍枢机主教的数百人之一。
罗伯特·克伦威尔有可能帮助了他的堂弟成为大主教约克坊——沃尔西在伦敦的宏伟官邸的管家。但直到克伦威尔1518年从罗马返回英格兰后,他才作为枢机主教的门徒崭露头角。1519年他成为沃尔西个人理事会的一员——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从那时起,他开始穿黑色和褐色的天鹅绒制服,表明他是服侍枢机主教的数百人之一。
据尤斯塔斯·夏普伊所言,沃尔西很快就注意到了克伦威尔的潜力。“约克枢机主教看到了克伦威尔的警觉和勤勉,以及他在不论正邪的诸般事务上的能力和机敏,便把他招至麾下,主要派他负责拆除五六座修道院。” [16] 这一说法的前一部分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在后一部分,夏普伊将不同的事件混在了一起:克伦威尔确实帮沃尔西解散了一些宗教设施,但这是在他已经服侍沃尔西多年以后。夏普伊暗指这是克伦威尔的第一个任务,其实只是一个将注意力吸引到他眼中的克伦威尔最大的罪过上的手段。约翰·福克斯更为积极地描述了克伦威尔早期对沃尔西的服侍:“他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主教府中,他在那里确实担任过几份职务,并在这些职务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忠诚,很快他看起来比枢机主教更适合服侍国王。” [17]
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什么克伦威尔和沃尔西如此迅速地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他们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二人都出身卑微,都利用他们与生俱来的机智、悟性、精明和勤奋成就了自己,并如风暴一般征服了世界。当然,他们结识的时候,沃尔西已经比克伦威尔高出了好几节。但是后来者看到了他的机会:如果他自己能成为国王首席大臣的左右手,那未来更大的提升也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同时,克伦威尔发展迅速的法律事业也让他离宫廷的社交圈更近一步。他开始在几个重要的法律诉讼中代理客户,其中最早的案件之一就是坎特伯雷特权法院1520年10月向罗马教宗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复件送到沃尔西那里,其中附有“其他信息详见托马斯·克伦威尔信件”的字样,在信件中克伦威尔总结了案件的关键点并就如何最好地处理提出了建议。 [18] 显然克伦威尔表现得很好,第二年他受命为曾在第三代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Edward Stafford)手下任监督员的查尔斯·尼维特(Charles Knyvett)担任代理律师。尼维特在1521年5月17日公爵被处死前不久辞职并对公爵做出了不利指证。他就因辞职而失去的几份职位提出赔偿诉求,同时要求免除价值3100英镑(比现在的110万英镑还多)的债款,这是他被迫代替主人承担的。
为一个已被判刑的叛国者的侍从申诉赔偿是一个冒险的工作,大多数律师都会拒绝。但是克伦威尔知道这个案件能让他接触到宫廷社会的最高层人士,所以他欣然受理了这个案件。他一丝不苟地替他的客户准备并修改了多份诉状,一些送到了国王那里,一些送到了枢机主教沃尔西那里。虽然克伦威尔没能为尼维特打赢官司,但是他实现了为自己在宫廷里立名的目的。
现存文献中没有关于克伦威尔何时获得了国王接见的记载,但是1515年第一次到访宫廷的威尼斯使臣描述了接见的可能场景:
有人引我们进入宫殿,各个房间里都挂有极为精美的壁毯,护卫根据等级从上至下依次穿着金、银和丝绸,其中包括300个身着银色胸甲、手持长矛的戟兵;我对上帝发誓,他们每一个都像巨人那么高大,所以排列起来很是壮观。我们终于到了国王那里,他坐在一个金线织成并在佛罗伦萨加工刺绣的华盖下,这个华盖是我见过的最昂贵的东西:他斜靠在镀金的宝座上,宝座上有一个大的金线锦缎制成的软垫,上面放着那把金色的国剑。
亨利衣着白色和深红色的缎子制成的华丽衣衫,脖子上戴一个“金色的项圈,项圈上镶有一枚圆形钻石,跟我见过的最大的胡桃一样大小,还有一颗极为炫目的、特别大的珍珠吊在下面……他的手指上戴满了镶有宝石的戒指”。国王的右边有“8个贵族,衣着与他相仿”,并且“还有6个手持权杖的男人,以及10个传令官,他们身着金色织物制成的短袖制服,衣服上饰有英格兰纹章。此外还有一群贵族,他们都身着金色织物和丝绸”。 [19] 即使对一名经验丰富的使臣来说,那一定也是令人敬畏的场景。虽然因为经常游历,克伦威尔对宏伟的宫廷并不陌生,但是在第一次被召见的时候,他一定也会对此感到印象深刻——或许,尽管他天生不羁,也会有一点惶恐。据小说家班戴洛说,克伦威尔立刻就给国王留下了好印象:“他(沃尔西)会时常让克伦威尔跟国王汇报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位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要讨好国王,国王开始对他面露慈色,认为他是一个适合处理任何极其重要事务的人。” [20]
在尼维特案之后,克伦威尔的律师事业继续发展。毫无疑问这得益于沃尔西的影响,克伦威尔任务使他与宫廷的接触越来越多。1522年年初,他代理了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诉讼当事人,案件由星室法庭的理事会听审。而在该案件之外,其他正式法庭文件中也有多处提到了他的名字,表明他作为一名本领和能力相当大的律师的名气正在迅速扩大。他的其他委托还包括代理理查德·乔费尔(Richard Chawfer)起诉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和蒙乔伊勋爵(后者蒙国王喜爱),案件由伦敦主教听审。在1522年8月15日写给克伦威尔的信件中,乔费尔写到主教指示双方指任“一个中立且对这种庭审有了解的人”,还写道:“我选了您,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会在城里,这样我可以进一步知会您详情。” [21] 从他这个时候的通信来看,克伦威尔也没有忽视他的羊毛和布料生意。 [22] 他的英格兰客户包括金匠、杂货商、裁缝、布商、鱼贩和市议员,还有从巴黎、诺曼底到奥格斯堡和佛罗伦萨的国外人脉。到1522年年中,克伦威尔认识沃尔西已有约6年了,他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势令他有资格在德意志的汉萨同盟授予的委托书中被称为“先生”。
大约这个时候克伦威尔雇了一个学徒,一个精明的、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名叫拉尔夫·萨德勒(Ralph Sadler)。萨德勒在1521年就已经服侍克伦威尔了,当时他十三四岁,但有可能自1514年开始就被收养在克伦威尔的宅邸。可能是他的父亲——第二代多塞特侯爵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管家亨利·萨德勒(Henry Sadler)——把他带到了克伦威尔的面前。克伦威尔曾在1522年充任多塞特的律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因为格雷家跟国王关系密切),不过显然当时他已经认识亨利·萨德勒了。他很快注意到拉尔夫的潜力,并保证这个男孩受到极好的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以及法律培训。拉尔夫很快证明自己堪当大任,而且克伦威尔开始让他承担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责任。他大约19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主人的秘书,这让他在法律、管理、财务尤其是政治等各个方面接受了基础训练。克伦威尔给了拉尔夫如此大的信任,后者开始负责撰写克伦威尔的大量信件。他因此直接接触国家事务,并且几乎可以像他的主人一样精准地理解国家事务的细微差别。这是一个信任度极高的职位,萨德勒证明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不久之后,人们都知道他跟克伦威尔关系密切,开始请他帮忙。
萨德勒诚心诚意、忠心辅佐克伦威尔,不仅能够跟得上后者的节奏,甚至有着与克伦威尔相当的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干劲。他习惯以小时而不是以天为单位给自己的信件标注时间,由此可以很好地看到他繁重的工作日程,他经常凌晨4点就起床,很少在午夜之前休息。由此可以推断他的主人也是这样。克伦威尔有一次发牢骚说他一直“忙于其他的事务……几乎没有时间进食”。 [23]
1523年克伦威尔在上流社会的快速爬升迎来了一个高点,他第一次进入下议院。
 那时,议会已经由一个国王召集显贵的臣民以传达自己意愿的集会演变成一个可以制定法律、批准征税,甚至偶尔反对王室意志的活跃机构。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成员为根据君主敕命出席的本国贵族,而下议院成员则是通过地方选举获得席位的人。
那时,议会已经由一个国王召集显贵的臣民以传达自己意愿的集会演变成一个可以制定法律、批准征税,甚至偶尔反对王室意志的活跃机构。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成员为根据君主敕命出席的本国贵族,而下议院成员则是通过地方选举获得席位的人。
议会总体上是一个临时的机构。虽然会不定期举行集会,但每次集会之间间隔很长,都铎时期它的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在亨利七世24年的统治中,他召集了7次议会,总共只持续了25周。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在位37年间,召集了9次议会,总共持续了183周。自1529年以后,议会大多数都集中在克伦威尔手握大权的时期。议会成为克伦威尔施展他和王权影响力的重要舞台,让他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雄辩家和律师的优势。
1523年议会——自1515年12月之后第一次集会——之所以被召集起来,是为了给沃尔西激进的对外政策筹措资金。得益于克伦威尔的一个勤勉的书记员,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演讲的文字记录,由此可以难得地一窥亨利统治之下的议会辩论的喧闹实况。显然没有因议会首秀而感到紧张的克伦威尔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他利用那让他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出类拔萃的雄辩能力,冒险质疑国王长期以来意欲宣示自己对法国的古老的所有权。考虑到亨利是如此喜爱扮演伟大的勇士之王这一角色,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这同样也公然违背了他的新侍主的策略。但是,正如克伦威尔辩论的那样,英格兰没有能力负担与法国开战带来的巨额花费。他的长篇演讲巧妙地糅合了恭敬与理性。意识到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新来者,他的意见可能会被有权势的同僚忽视,他表示:“我认为我是所有人中最不配在诸位睿智、高贵的大人面前以任何方式发表自己看法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每当我思量的时候都会因敬畏而战栗的事情上。”他同样假装顺从这些“远比我有智慧、学识和经验”的人。
克伦威尔随后提出的论据源自他自身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经历,因为他有能力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给出最新的评估。这给那危险的怀旧观点泼了冷水,这个观点经常以伟大的克雷西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为参考。克伦威尔在结论中建议国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英格兰北部边境构成威胁的苏格兰上。总之,在失去理智妄想获得广阔的海外领土之前,国王应该先整顿好家门内的事。结束的时候,跟演讲开始时一样,他本着谦逊的姿态说:“因此我表达了我纯粹、单纯的想法。”然而,这个演讲真正的妙处在于克伦威尔自始至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国王坚定又强烈的忠诚。他宣称正是他对国王安危的强烈担忧促使他反对沃尔西的计划。这纯粹是权术,克伦威尔知道他在议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详尽地记录下来并呈给国王。因此他重视并充分利用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奉承他的君主并给他留下印象。 [24]
这次出色的演讲是克伦威尔谨慎的外交手段的早期迹象,这种谨慎也是克伦威尔日后对外政策的基础。我们虽然可以轻易将他对与法国开战的厌恶归咎于年轻时在法国的经历,但其实克伦威尔是一个精明、有洞察力且非常务实的人。虽然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有着强烈的忠诚,但是他从不允许个人偏见主导他的事务决断。此外,他会适时地、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不是与法国的联盟。
至于克伦威尔公开表达对与法国开战的异议是否背叛了他的新主人,这一点则颇值得玩味。沃尔西偏向好战的外交政策,因此可能会因为他的门徒如此有说服力地驳斥这一政策而愤愤不平。不过,也有人暗示,克伦威尔如此行事是受向来诡计多端的枢机主教的指示,是为他改变政策奠定基础的方式。但是,不管沃尔西怎样相信克伦威尔的能力,他不大可能会冒险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新人。况且,克伦威尔演讲的语气透露出他是真的试图制止这个他(凭经验)认为十分错误的政策。
虽然克伦威尔的辩论很有说服力,但是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议会拖了整整17周,几乎相当于平均周期的两倍。议会结束后不久,克伦威尔对他的朋友约翰·克雷克(John Creke)抱怨:
包括我在内的议员们都坚持了长达17周之久的议会,在议会上我们谈论了战争、和平、冲突、怨恨、富足、匮乏、贫穷、真实、虚假、正义、平等、欺骗、压迫、慷慨、敏锐度、力量、节制、叛国、谋杀、重罪、调节,有争论,有辩论,也有窃窃私语,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在我们的王国建立并维系一个英联邦。然而结果我们做了前辈们惯常做的,我们可能也会习惯这样做,讨论最终又回到了起点。 [25]
这是克伦威尔现存最早的信件。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因与这群威严的男人争吵而害怕,反而已经开始嘲弄议会的不足。这种天生的不羁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他的这一特点帮他结交朋友,但同样也为他树敌。
克伦威尔迅速理解了议会的运作方式,这反映出他头脑敏捷、适于从政。沃尔西曾经告诉他:“你有很好的理解力。” [26] 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克伦威尔是一个聪慧的男人,非常熟悉政府事务,且足够理智,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评判。” [27]
克伦威尔给克雷克的信同样也说明了他出色的交友能力。这不是一个通常会与诡计多端的律师联系在一起的特质,但是这方面的证据令人信服。约翰·克雷克非常忠于自己的朋友克伦威尔,他广泛游历欧洲大陆,并告知克伦威尔发生在大陆上的各种事件。就在前一年的7月,他向克伦威尔寄了一封真情洋溢的信。“我对你的爱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样热烈。我的心,像以前怀念别人一样,怀念你和沃达尔先生的陪伴……我的一生从未在如此短暂的相识中对别人产生如此真诚的情谊,这种情谊如火一样日益炽烈。上帝知道分开的时候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每每记起我们在你的花园里漫步,我就会不顾一切地陷入沉思。我想写更多,但是我的心不允许。”克雷克就此结束了他的信:“但凭尊夫人差遣。” [28]
就克伦威尔自身来说,他是一个秉笔直书的通信者,完全没有一个知晓大量机密信息的人应该有的矜持。他答应克雷克,在后者还居住在毕尔巴鄂的时候,他会告诉后者国内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据说消息可以更新生命的活力”。不过,他的确采取防范措施在一些回件中使用了加密的标记。“据我所知,你所有的朋友都很健康,尤其是你担心的那些人: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想用寓言来表述最好,因为我有所怀疑。” [29]
克伦威尔和克雷克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沃达尔先生”应该是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或者是乌维达尔(Uvedale)],是一名隶属于掌印司(the Signet Office)和国库的办事员。他比克伦威尔年长三岁,也像克伦威尔一样在政府开拓了一份事业,他很快引起了枢机主教沃尔西的注意。这三个人之间有一段融洽的友情,在一封信中克伦威尔告诉克雷克“伍德尔是一个没有妻子的人,我把他引荐给你”。 [30]
克伦威尔和克雷克另一个共同的朋友是斯蒂芬·沃恩(Stephen Vanghan),一位英格兰商人兼御用外交官。他经常造访尼德兰,应该是在尼德兰的时候跟克伦威尔结识的。沃恩出生在商人世家,他自己也延续了这个传统,成为商人冒险家公司活跃的一员。他是一个跟克伦威尔一样勤勉的人,他的生意让他不断地往返于低地国家的各个市场之间。“我从来没有休息,”他曾经对一位通信者抱怨,“我一会儿在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一会在布鲁日,一会儿在根特,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这样经历了异常的麻烦我才能满足我服务的所有人……尽可能地取悦他们。”
 克伦威尔应该是肯定且尊重沃恩对自己事业的投入的。这种投入得到了回报,因为沃恩在商业圈的地位迅速攀升。不管有多少其他的需求,沃恩总是优先处理来自他的英格兰朋友的需要。“我会尽快答复你的指示,”他曾经向克伦威尔保证,“虽然作为一个为多个对象效力的人,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31]
克伦威尔应该是肯定且尊重沃恩对自己事业的投入的。这种投入得到了回报,因为沃恩在商业圈的地位迅速攀升。不管有多少其他的需求,沃恩总是优先处理来自他的英格兰朋友的需要。“我会尽快答复你的指示,”他曾经向克伦威尔保证,“虽然作为一个为多个对象效力的人,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31]
他们的通信表明沃恩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克伦威尔,因为他的大多数书信结尾都是问克伦威尔的母亲安好。 [32] 克伦威尔毫无保留地信任沃恩,两人很快建立了亲密、长久且互相扶持的友谊。1524年3月克伦威尔指任沃恩为自己在尼德兰的代理人。他是克伦威尔不断扩大的海外交际圈、代理人圈和朋友圈的第一人,这些人为克伦威尔提供宝贵的国内外时事信息。沃恩以及克伦威尔圈子里的其他人在事实上充当了他的个人间谍,让他及时了解关于经济、政治事件的传闻和情报。克伦威尔不得不为这项服务花费大量金钱,一如沃恩在一封信中坦言:“要知道这里的隐秘之事,一个人必须知道可以从哪些人那里了解这些事——这代价很高,是我力不能及的。” [33] 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回报,1526年克伦威尔帮助沃恩在沃尔西那里谋得一个职位,为沃尔西在牛津的学院“记录证据”。 [34]
不过,他们的交往延伸到商业事务以外。沃恩受益于他的老主顾的殷勤好客,以及克伦威尔为他介绍的广泛人脉。克伦威尔视他为一个忠实的朋友,还把一名年轻的爱仆托马斯·埃弗里(Thomas Avery)托付给沃恩培养。在1529年埃弗里离开克伦威尔家去往尼德兰前不久,克伦威尔为这个年轻人准备了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慷慨馈赠。他要求沃恩确保埃弗里“得到适合他年龄的知识教育和培养”。他的朋友是一个理想的监护人,并且经常汇报这个男孩的成长状况。 [35]
沃恩和克伦威尔一样热爱学习。沃恩可能受教于伦敦有名的圣保罗学院。沃恩知道他朋友的文学兴趣,会竭尽全力帮他找到在英格兰没有的书籍。这些书包括《纽伦堡编年史》( Nuremberg Chronicle ),这是1493年首次出版的图解世界史。沃恩知道他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到这本书的最新版,因为克伦威尔还提出给他寄些钱以加快寄书的速度。伤心的沃恩于1530年6月写信给克伦威尔说:“我打心底跟你说实话,如果你想要我的外衣,你可以连同我的斗篷一起拿走,我不缺为我朋友做事的钱,所有朋友中我最尊崇的是你,我更不缺少为你做事的钱。” [36] 沃恩还给克伦威尔寄了一个地球仪并向他保证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物件”。 [37]
这位商人乐此不疲地关心他朋友的安危。1528年3月,在回伦敦的一次旅程中,他有些惊恐地写信给克伦威尔,告知在他家附近发生的一起暴力抢劫事件:
上周四,下午6点到7点之间,五个窃贼敲响了罗德雷戈(Roderego)的门。他是住在紧靠着你门口的金匠旁边的西班牙人。他问门外是谁,窃贼回答说:“宫廷派来的,要找罗德雷戈问话。”门打开之后,三个男人冲进来,看到上面提到的罗德雷戈坐在火炉旁,与他为伴的是一位在温莎女士隔壁居住的可怜妇人。另外两个人等着,看着门,掐住妇人的脖子不让她大叫。然后他们拿走了罗德雷戈的钱包,并刺中他的腹部,将他杀害。
虽然窃贼很快被逮捕,但沃恩还是未雨绸缪,为克伦威尔的大门了订了一条结实的门链,这样“陌生人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38] 克伦威尔对沃恩也同样关切,后者曾经感谢他“亲切而慈爱的言语”。 [39]
克伦威尔的其他朋友来自各个地方。一些来自他或他妻子伊丽莎白的家庭,还有一些是来自他不断加入的更有文化的圈子。他在意大利期间培养的对艺术和人文的热爱让他结识了亨利时代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包括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爵士(Thomas Wyatt),他后来因与安妮·博林的交往而臭名昭著。据说他是“忠于”克伦威尔的。 [40] 当时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律师爱德华·霍尔也成为克伦威尔的好友。虽然他们可能在法律圈结识,但是克伦威尔也热爱历史,并收集了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包括古代编年史和宪章的抄本。伦敦主教爱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被福克斯称为“罗马(即教宗)教令最忠实的拥护者和保护者”——也会放下他对克伦威尔改革主义信念的不齿,一有机会就突然到访翻阅他家中卷帙浩繁的藏书。 [41] 著名的宫廷画家汉斯·荷尔拜因也成为克伦威尔的熟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后者的赞助,这位艺术家才能得到如此好的名声。
克伦威尔到访意大利的时候正值人文主义盛行之际,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恢复古典知识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学习和翻译原著——这一原则在克伦威尔稍后生涯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场运动的首要推动者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他的作品得益于1517年印刷机的出现而得到广泛传播。结果,这些作品迅速传到英格兰,被亨利八世宫廷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接受。一个尤为活跃的支持者是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他跟克伦威尔的友谊开始于1519年前后。埃利奥特曾在巡回法庭在西部巡回的时候作为书记员为他的父亲服务,所以他跟克伦威尔有相同的法律和知识兴趣。这两人可能是在沃尔西注意到埃利奥特并任命他为枢密院书记员的时候结识的。虽然他和克伦威尔的宗教信仰不同,在未来几年会有数次冲突,但是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克伦威尔去世。
克伦威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安东尼奥·邦维西(Antonio Bonvisi),一位生活在伦敦的成功的热那亚商人。他是为政府服务的银行业者,为在欧洲的外交使节们递送钱和信件。得益于他的人脉,他消息极为灵通,往往在国外事件的消息还没到达宫廷的时候就已经知情。因此,他对克伦威尔十分有用,但他们的友谊远不止是商业联系。邦维西亲近有学识的人,特别是那些——像克伦威尔一样——到过他的祖国意大利的人。克伦威尔能说意大利语这一点肯定也促进了他们的友谊。两人住得非常近,都在今天伦敦金融城的中心地带。
有趣的是,邦维西与那位后来会成为克伦威尔死敌之一的托马斯·莫尔也过从甚密。传奇的圣人莫尔给欧洲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带来了创作颂词和赞美诗的灵感。他是一个“有着非凡美德和纯净无瑕的良心的人,正如伊拉斯谟所说,比最白的白雪还纯净、洁白;作为一个英格兰人,他有天使般的智慧。伊拉斯谟说,从前及今后再无人能像他一样”。 [42] 莫尔比克伦威尔年长7岁,他接受法学训练,年仅18岁的时候就被林肯律师学院录取。跟克伦威尔一样,他也因机智、令人愉悦的谈吐和出色的学识而出名。他也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因此,他与当时欧洲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联系,包括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以及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1516年莫尔出版的《乌托邦》( Utopia )——一本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小册子——轰动一时,并多次再版。这部作品讽刺欧洲社会目光短浅地追求物质,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的虔诚和博爱。这样做表现了莫尔本人强烈的虔诚之心,这让他远离财富的诱惑。虽然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但是他不在乎美食,喜欢水胜过酒,也不关心衣着。这让他与宫廷的大多数人不同,不过,他跟克伦威尔一样精通法律事务,加上他的魅力人格,确保了他会快速成名。
莫尔约于1515年开始为王室服务,他大概是沃尔西的一个门徒,并在三年后成为枢密院的一员。但他一直对廷臣生涯缺乏兴致。他的女婿,也是他最早的传记作者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说他“有令人愉快的性情”,并且说“国王和王后对他很满意,在枢密院晚餐结束、他们用餐的时候,为了开心,经常找他来一起娱乐”。亨利非常喜欢莫尔的陪伴,以至于“他整月不能离开宫廷回家一次去陪伴妻子和孩子们(而他渴望与家人在一起),也不能连续两天不出现在宫廷里”。罗珀称他的岳父憎恨这种“对他自由的禁锢”,在国王身边也日益忧郁,结果——这无疑也是他的初衷——他不再那么频繁地被国王召见。 [43]
克伦威尔服侍沃尔西,这意味着他跟莫尔几乎肯定有过交集。考虑到他们在个人兴趣和职业生涯上都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他们彼此间有可能十分熟悉。但是他们之间有着明显且危险的不同:莫尔极度自律、虔诚;克伦威尔则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莫尔不太在意个人财富和权力;而克伦威尔渴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权力。难怪人们习惯上会视他们为对立面:圣人莫尔和恶人克伦威尔。
约翰·福克斯对他俩以及斯蒂芬·加德纳进行了有趣的比较,说他们三个“从年少时就在一起成长(在沃尔西的府邸)”,年龄也大致相当:
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很大差别,虽然他们的性情和学业大不相同。尽管这三个男人有相似的学识和悟性,在本国的名望地位也大体相当,并且莫尔和温彻斯特
 可能更加博学,但这个人(克伦威尔)的天资更为聪慧、判断更敏捷,其口才也与前两者相当。而据推测,这个人也更能机警应变,还有一种英雄式的抑或王公式的气度,仿佛专为伟大且重要的事业而生。
[44]
可能更加博学,但这个人(克伦威尔)的天资更为聪慧、判断更敏捷,其口才也与前两者相当。而据推测,这个人也更能机警应变,还有一种英雄式的抑或王公式的气度,仿佛专为伟大且重要的事业而生。
[44]
撇开福克斯对克伦威尔惯常的奉承不说,他指出莫尔和加德纳的“学识”得益于全面的教育,而克伦威尔则靠自学并且在天资上可能更胜他日后的这两位对手一筹,这一点还是合乎情理的。
邦维西不是莫尔和克伦威尔之间唯一的共同朋友。克伦威尔也和莫尔的连襟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成了亲密的伙伴,后者是一位出庭律师、议会议员、印刷商以及作者。他们有很多共同爱好,偶尔会在一起打保龄球并相谈甚欢。拉斯泰尔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这一事实后来预示着麻烦,但克伦威尔能够和一些在教义和政治问题上与他立场相反的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这一点也是他思想开放的一个证明。
克伦威尔社会地位的急速攀升促使他寻找新的居所。1522年9月之后不久,他和家人就从紧挨着伦敦塔的芬丘奇街搬到了宽街(Broad Street)上的奥斯丁会。虽然他们的新房子离曾经居住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却显示了他们地位的显著提升。奥斯丁会是一片隶属于奥古斯丁修道会(Augustinian Friary)的大型宗教设施,可追溯到13世纪60年代,坐落在伦敦城内,占地约5.5英亩,离现在的英格兰银行不远。建立这一设施的奥古斯丁修道会隐士在英格兰以奥古斯丁托钵修会之名为人所知,后者通常被略称为奥斯丁会。在1598年出版的对伦敦的调查中,古文物研究者约翰·斯托(John Stow)描绘了这座宏伟的教堂:“紧接着是奥古斯丁修道会教堂和教堂墓地:经由南门走进西门厅,可以看到一座很大的教堂,教堂顶上有一个最精致的塔状尖顶,纤细、高耸而笔直,我从没有见过类似的建筑。” [45] 他继续列举了几个葬在教堂墓地的名人,包括理查二世的兄长,还有几个在伦敦塔和塔山被斩首的叛国者,其中包括在1521年被斩首的白金汉公爵。
伦敦的修道院经常把辖区内的土地租给世俗租户并由此大赚一笔,奥斯丁会也不例外。奥斯丁会在辖区的西侧建了一些公寓,同时也在辖区外紧挨思罗格莫顿街(Throgmorton Street)的地方有一些房产。克伦威尔家位于宽街上的新居所就靠近这里,与奥斯丁会教堂墓地的西侧相接。他们的邻里都很好,因为修会其他房产的租户都是一些杰出的人,其中还有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他未付租金就离开了。他们北面隔壁的邻居是约翰·卡瓦尔坎蒂(John Cavalcanti),一个富有的意大利商人。虽然这充分反映了克伦威尔的新地位,但是考虑到他后来成了修会最大的敌人,他选择在奥斯丁会的地界上居住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

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第一座房子(比例尺1∶400)
根据当时的记载,克伦威尔的房子实际上是一座三层的房舍,有三面、至少14个房间,还有一座花园。不过尚不清楚他和家人是什么时候搬到那里的,但这一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522年。那年12月,克伦威尔参加了一场宽街选区的会议,此时他显然已是该区的一个住户。
 1523年年底,他当选宽街选区法庭的某一高级职位,有可能是负责为市议员编写本选区年度报告的书记员,那时他肯定就已经住在那里了。这是克伦威尔地位迅速攀升的另一个体现,因为在晋升到高级职位之前,他必须在选区几个级别略低的位置上任职。
1523年年底,他当选宽街选区法庭的某一高级职位,有可能是负责为市议员编写本选区年度报告的书记员,那时他肯定就已经住在那里了。这是克伦威尔地位迅速攀升的另一个体现,因为在晋升到高级职位之前,他必须在选区几个级别略低的位置上任职。
有资料提供了其他几个关于克伦威尔这一时期家庭生活的线索。他的妻子伊丽莎白1525年肯定生活在奥斯丁会。她的母亲默西·普赖尔(Mercy Pryor)及其第二任丈夫不久之后也过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都十分优渥,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舒服的、布置精美的房间,有资料显示默西生活在这里直至去世。1532年当克伦威尔的一个熟人汇报说她身体康健的时候,她肯定还住在那里。 [46] 克伦威尔后来给他的岳母留下慷慨的遗赠,说明他相当尊重她。
依靠仅有的关于伊丽莎白在奥斯丁会生活的零碎证据,可以知道她既承担了家庭事务又支持了丈夫的事业。1525年11月29日克伦威尔从肯特寄信给她,他在那里处理解散贝汉姆修道院(Bayham Monastery)一事。他给她送了一头在附近打猎时猎杀的母鹿。他的附信非常简短潦草。“伊丽莎白,愿你一切安好。我让这个信使给你送了一头肥美的母鹿,请你把其中一半送给我的老师史密斯,剩下的你留着享用。”信的其余部分包括其他数件需要他的妻子处理的差事:“还有,如果理查德·斯威夫特(Richard Swift)正在家中拜访,或者碰巧不久后即将到访,我希望他迅速来贝汉姆或者汤布里奇找我。请你把在那些聚会中得到的信息都通过这个信使发给我。”然后,他又想起来什么,写道:“还有,请在信里写下自从我离开你之后有哪些来找我商谈的人拜访了你。”他落款:“你的丈夫托马斯·克伦威尔。”即便这封信缺少情感,但至少证明克伦威尔信任伊丽莎白,让她在他不在的时候代表他,并向他汇报家里的人员往来。与信件内容相比,克伦威尔对妻子的称呼流露出更多的爱意。他在信封上题写道:“致我挚爱的妻子伊丽莎白·克伦威尔,请送至伦敦奥斯丁会。” [47]
伊丽莎白显然从她丈夫不断上升的地位中受益,因为她从迫切想讨他欢心的人那里收到了很多礼物。其中一位是威廉·巴雷斯(William Bareth),1525年11月,他“为了讨一夸脱酒喝”给克伦威尔夫人送了六只鸻。 [48] 不过几乎没有关于她和她的三个孩子在奥斯丁会的日常生活的其他记载。安妮、格雷丝、格雷戈里幼年时期大概生活在家里,当时通常由妻子负责这一阶段孩子们的教育。在很多富裕的家庭里,男孩子7岁的时候会被指派一个家庭教师。格雷戈里是克伦威尔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所以他的父亲很可能非常热衷于为他的教育投入资源。除了学习拉丁语、希腊语、算术、古典文学和宗教典籍之外,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培训以为未来的事业做准备。有史料证据显示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同样从事法律和贸易行业,接管自己一手创立的盈利颇丰的生意。
格雷戈里有一段时间可能受教于约翰·帕尔格雷夫(John Palgrave,或称帕尔斯格雷夫),后者曾为国王的女儿玛丽担任家庭教师。1525年帕尔格雷夫被指派在布赖德韦尔宫辅导国王的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Henry Fitzroy),布赖德韦尔宫离克伦威尔在城里的家很近,所以格雷戈里可能在那里跟菲茨罗伊一起学习。帕尔格雷夫制订的学习计划颇具野心。受当时一些最伟大的学者的影响,包括托马斯·莫尔、托马斯·埃利奥特、斯蒂芬·加德纳,他的学习计划包括语言、古典文学、法律和音乐。但是他跟沃尔西交恶,次年被辞任。
相比之下,女儿们幼儿时期的教育是母亲们的责任,只有最有权或者开明的家庭才会为她们花钱请一个家庭教师。女孩们常常生活在家里直到成人,她们的学习通常仅限于缝纫、刺绣、跳舞、音乐和骑马。培养的主要目标是把她们变成敬虔的、有道德的年轻女性,擅长家庭管理和社交。鉴于她们的追求被限制在婚姻上,一个女孩在这些“身为人妻的”技艺上受到的教育越好,她的父亲为她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可能性越大。16世纪后期,加尔文教牧师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说:“女人最完美的品德就是服侍、顺从男人。”他声称女性“软弱、不堪一击、焦躁、不可信且愚蠢……经验证明她们善变无常且残酷,缺乏协商态度和组织精神”。 [49] 为了增长学识而学习是不被鼓励的:一个女人能从智力激发中得到什么乐趣呢?亨廷顿伯爵夫人凯瑟琳·波尔(Katherine Pole)认为她的四个女儿离开她的照料时“尽管没有过多的学识,但是识字”。在男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然且令人满意的状态。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女人被比作一个拿着剑的疯子:她会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中。
这个一般惯例也有例外。托马斯·莫尔爵士让她的所有女儿接受了跟男人同等的教育。他在音乐和文学上指导妻子,使她在原来接受的家庭教育上有所提升。亨利八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后来成为一个天资聪慧且早熟的学者,她在8岁时就已经在学习几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与之相反的则是亨利的两任妻子简·西摩尔和凯瑟琳·霍华德,她们几乎不识字。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生意人,克伦威尔肯定计划给女儿们安排好的婚姻,因此会确保她们掌握当时社会通行的为妻之道。但是很难想象他没有让她们分享他那普世开明且富有修养的背景所带来的好处。克伦威尔后来的生涯显示他热衷于男孩们和女孩们的宗教教育。此外,克伦威尔在1529年起草的遗嘱中特意提到了安妮和格雷丝的教育,留下了11英镑的遗赠用于两个女儿直到长大成人之前的“道德教育和培养”, [50] 这表明他重视女儿们的教育超过当时常见的程度。克伦威尔成长在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家庭,跟父亲相处得并不好。有证据显示他在后来的生涯中对女性抱有积极的看法。一些他最常往来的通信对象都是女性。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为那些向他寻求帮助的妻子、寡妇和女儿们在诉讼中取得进展。 [5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克伦威尔是如何利用他服侍沃尔西之余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的。他在家用餐的时候通常是跟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家人总是在一起用餐。一天只有两顿主餐:午餐通常是11点进行,而晚餐通常是在晚上5点到6点之间。宴会通常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用餐时间(和菜单)也会大大增加。克伦威尔家有能力提供以都铎时期的标准来看可谓丰盛的饮食,有分量可观的烤肉、炖肉、家禽、鱼、面包、麦芽酒和葡萄酒。他们在水果和蔬菜的食用方面较为克制,1500年的一本居家手册告诫读者“要注意绿色植物和生的水果,因为它们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人们认为水果会加重瘟疫,所以在异常致命的瘟疫爆发时会禁止售卖水果。 [52]
在大多数普通家庭,食物是用木质餐具盛放的。最大的“盘子”是一个薄的正方形木板,中间有一个大的凹陷用来盛肉和肉汁。克伦威尔家的一份清单表明他的餐具在16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财富的增长换成了锡铅合金制的,可能他是想仿效他的侍主所举办的盛大晚宴。乔治·卡文迪什描述了沃尔西家庭及其宴客用餐时盛食物的精致餐具:在一个大的碗橱里摆放着“6层架子高的、满满的金制餐具,非常奢华,都是最新的样式,在最下面一层架子上的餐具全部由黄金装饰、加工尤为精巧细致”。 [53]
克伦威尔在欣赏艺术、文学和音乐之余也热衷园艺,或许还在他新近加入的宫廷社交圈的影响下培养了对驯鹰捕猎的热爱。他是一个好客、慷慨的主人。1529年夏普伊大使在英格兰任职之后在克伦威尔的住宅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他描述克伦威尔“好客,在财产上慷慨大方,言谈彬彬有礼,家庭出色、房舍华丽”。有一次,他回忆克伦威尔对他的接待“跟往常一样,极为和善”,还有一次他说克伦威尔“按照他一如既往值得称道的习惯,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 [54] 尽管是对手,但夏普伊也承认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言谈彬彬有礼的、举止慷慨大方的人”。沃尔西的一个仆人托马斯·阿尔瓦尔德(Thomas Alvard)也认同夏普伊的体会。他对克伦威尔极尽赞美之词:“您的持家待客之道让我看到,除了国王以外,没有一个英格兰人能像您一样接纳并款待国内外的来宾。” [55]
一份1527年6月奥斯丁会的清单提供了一条关于克伦威尔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引人遐想的线索。 [56] 这份极为详细全面的“克伦威尔大人家中物品”清单包括从家具、室内陈设、衣物和珠宝到碗橱中木板和桌上锡铅合金制的盘子数量。清单上甚至描述了摆放在其中一个卧室里的“老旧安乐椅”。整个清单就是对克伦威尔良好品味的证明。
显然在那个时候克伦威尔家的生活相当舒适。奥斯丁会的房子有三翼,主要的房间在前翼,俯瞰教堂墓地,大厅和走廊与位于后面的勤务侧翼连接,显然这个住宅不仅可供居住,还可以用来宴请宾客。勤务侧翼有厨房、酒储藏室、食物储藏室和柴棚。个人起居室在第一层,卧室(总共有8个)在第二层,仆人的房间在顶层。另外还有一处配备齐全的地下室。
克化威尔家的每个房间都按照最新流行品味和风格进行装修。位于一层的起居室尤其宏伟,铺有地毯并且配有长桌和屏风,也是克伦威尔的客人到访时要展示的地方。大厅经由“大门”亦即气派的门廊进入,是克伦威尔招待密友或者重要来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奢华的陈设才显出最炫目的效果。即使最显贵的大使都会对房屋主人坐的那把“镀金的大椅子”——他个人宅邸的宝座印象深刻。这里还有三把稍小一些的“女人专用”的镀金椅子、十二个镀金凳子和脚蹬、一张镀金桌子、一个橱柜和一面镜子。地板上铺着精美的地毯,房间各处放有绣着兰开斯特红玫瑰的软垫。克伦威尔对他的另一位侍主的忠诚可以从“画布中镀金的枢机主教大人的纹章”中看出来。他同样还展示了他的第一个贵族客户多塞特侯爵的纹章。此外,皇帝查理五世的一幅画像则是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大胆收藏,毕竟英格兰国王的外交政策经常在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和支持法国的立场之间变幻不定。但是克伦威尔显然觉得可以在自己家中表达自己的个人偏好——虽然它算不上一个私密的宅邸。有记录表明他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曾多次在这里主持枢密院会议。
大厅和起居室都装饰有一系列宗教图画,包括罗马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 Romana)的画像。根据传说,贞洁的卢克雷蒂娅是贪恋性爱的塔尔奎尼王子(Prince Tarquin)追求的目标,后者的暴行导致了罗马君主制的终结。尽管这个故事在这份清单被列出时众所周知,也可能成了其他显赫家族中收藏的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但我们也不禁猜测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作为亨利八世的臣仆时是否将画作拿掉了,毕竟那个时候现实(以安妮·博林这一形式)已经与艺术过于相像。

奥斯丁会宅邸最大的卧室是供克伦威尔和妻子就寝用的新房间。卧室中间放着一张有羽毛床垫的华丽大床,左右两侧是红色和绿色的床帘和镀金的铃铛,床下铺有精美的羊毛地毯。清单描述了这对夫妇拥有的多件长袍,这些长袍都由绸缎、天鹅绒和其他珍贵的布料制成,镶有很多不同的毛边。克伦威尔自己有至少16件紧身上衣,其中两件是深红色绸缎的,一件是黄褐色塔夫绸的,还有一件是黑色天鹅绒的。他还有很多紧身裤、手套、帽子和其他配饰,都是由最好的材料制成。他的日常穿戴也是一样,他有一件“蓝褐色”骑射外衣和一件镶有狐狸毛边的睡衣。他的妻子也有不少盛装,包括红褐色、黄褐色、黑色绸缎和天鹅绒的裙子,还配有项链、手包和帽子,其中有“一顶威尼斯金的贴头帽”——这是克伦威尔的众多珍品之一,显示出他对意大利事物的无比钟爱。
他们的衣服上还点缀有珍贵的珠宝。克伦威尔尤其喜爱金戒指,清单中列出了20枚不同的金戒指。其中有“一枚镶有平面钻石的金戒指”和“一枚镶有心形绿松石的金戒指”,两枚戒指在清单列出时仍戴在“我主人的手指上”。还有一个“大的平面红宝石”、一枚带着别针的珍珠和“一块镶在金子上的三角形钻石”。他的其他贵重物品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金银餐具,其中有银制高脚杯、勺子和盐碟,一个镀金杯子和麦芽酒罐,还有一个用银装饰的精致玻璃杯。
较为私人的房间里放置的物品可能更能体现克伦威尔的个人品味。其中,起居室的一块“桌布上印染有一对男女情侣的图案”。还有一张桌子的左右两边是沃尔西的纹章,克伦威尔在家里的公共和私人房间里都对此有所表现,表明了他对侍主的忠诚。克伦威尔家中还有两幅世界地图——一幅在起居室,一幅在用人住处——有这样一个四处游历的主人,这并不意外。他为其中一个挂毯选择了一个适合的主题:“一个镶边的阿拉斯挂毯,上面是消遣放松的图景。”
用人房间出人意料地舒适,墙上挂有壁毯和图画,有雕刻着花纹的镶金的床和羽毛床垫,还有一个新的壁板橱柜。紧挨卧室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船用箱子,用佛兰德斯铸造厂生产的扁铁条绑着,上面覆盖着黄色的羽毛。房子里还有几只这样的箱子,这表明很多——或者说大多——克伦威尔的贵重物品可能都被收藏起来了,不为人所见。
厨房的物件暗示了克伦威尔家庭及其宾客丰盛、多样的饮食。一个“大且圆的烤肉叉”立在火炉前,还有很多圆锅、平底锅、大浅盘、刀、壶、麦芽酒壶和红酒壶。从“铜质的阉鸡容器”、“挂肉的钩子”和“蒜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家厨房日常烹饪所用的一些食材。克伦威尔因大方好客而闻名显然是理所应当的。
房子的北面有一处小花园(约1/20英亩,220平方米)。清单没有提供关于这个花园的详细信息,不过如果在17世纪的房产调查时花园仍没有变化的话,这处小花园应该包括两座都铎时期盛行的方形结纹园,周围环绕有砾石铺就的小道。花园的东北角还有一座拱形的凉亭。

克伦威尔家中齐全的配置足以供他招待重要的客人,而他因大方好客闻名也证明他愿意投入相当数量的钱用于宴请和款待宾客。他雇有一支由约12名音乐家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他的账本上记为“布赖恩先生的音乐家们”。
[57]
他还赞助了一个剧团。“克伦威尔大人的表演者们”不仅在他的府邸表演,也到英格兰各地巡演,巡演最远到过德文郡的巴恩斯特普尔和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修道院。

克伦威尔和家人生活的舒适度毋庸置疑,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存有一种节制近乎节俭的意识。克伦威尔早年在佛罗伦萨街头乞求施舍的经历让他没有完全丢掉节约的习惯。在贵族宫廷同僚浪费大量钱财互相攀比炫耀的时候,他有计划地把钱花到最有用的地方。他这样做很有效果,以至于他的熟人都误以为他生活得跟那些公爵一样奢华。“他生活奢侈,”夏普伊说,“并且异常讲排场,热爱炫耀他的家庭和府邸。” [58] 事实上,克伦威尔的账本表明当他没有宴请重要宾客的时候,他甘于过简单的生活。这也体现了他的务实主义和他的自制力。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宫廷里或者在生意场上,所以为什么要浪费钱财修建一栋用于不间断宴饮娱乐的宅邸呢?他不是沃尔西,沃尔西的住宅和府邸几乎可以和宫廷相媲美,而克伦威尔权力的中心就在宫廷里。
数个世纪以来,克伦威尔背负着一名贪婪官僚的恶名,但他慷慨接济伦敦穷人的史料证据令这一形象缺乏说服力。一个生意上的联系人劳伦斯·贾尔斯(Lawrence Giles)曾向克伦威尔和他的妻子致信问好并感谢他的善意,向他保证上帝会眷顾那些帮助穷人的人。“在我来看……大人已受到上帝眷顾了。” [59] 《西班牙编年史》( Spanish Chronicle )佐证了这一点。一位居住在伦敦的西班牙商人[可能是安东尼奥·德·瓜拉斯(Antonio de Guaras),1529年随尤斯塔斯·夏普伊来到英格兰]于1552年之前编写的《西班牙编年史》漏洞百出,带有来自神圣罗马帝国视角的强烈偏见。尽管如此,几乎可以确定作者亲眼看到了他所描述的其中一些事件,所以它仍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后来回忆克伦威尔深受都城人们的爱戴,这说明他的慷慨是持续且为人熟知的。伦敦人同样也对他通过辛勤努力致富,而不像富裕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靠继承财产发家的人生历程怀有肯定和敬佩的态度。
[1] Cavendish,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p.7.
[2] Tyndale,W., The Practice of Prelates (London,1530),p.307.
[3] Weir,A., Henry Ⅷ:King and Court (London,2001),pp.1-2,19.
[4] Weir,A., Henry Ⅷ:King and Court (London,2001),p.2.
[5]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389;Weir,A., Henry Ⅷ:King and Court (London,2001),p.3.
[6] Hall,E., 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12.
[7] Starkey,D., 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2002),p.3.
[8]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1-12.
[9] Strype,J.,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 ,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6.
[10]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
[11]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1-12;Tyndale,W., The Practice of Prelates (London,1530),p.307.
[12] Brown,R.(trans. and ed.), Four Years at the Court of Henry Ⅷ:Selection of despatches written by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ebastian Giustinian,and addressed to the Signory of Venice,January 12th 1515,to July 26th 1519 ,2 vols.(London,1854),Vol.I,pp.139,15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art ii,Appendix,no.12.
[13]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02.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art i,no.1959.
[15]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17]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8.
[18]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14-15.
[19]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 pp.388-389.
[20] Payne,J.(ed. and trans.), 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 ,Vol.Ⅳ(London,1890),p.108.
[2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I,no.2441.
[22] 例如,可参见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I,no.2624。
[2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45.
[24]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0-44.
[25]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13-314.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262.
[2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752.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I,no.2394. 克雷克(又写为克里克)可能是文案处的一个文员。这是大法官法庭的一个职位。文员,也称为文案管理者,通过为特许状、公有土地转让证书和令状等盖章而获得工资和其他收入。
[29]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13-314.
[30]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14.
[3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247.
[32] 例如可参见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29。
[3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247.
[34] Richardson,W.C., Stephen Vaughan,Financial Agent of Henry Ⅷ:A Study of Financial Relations with the Low Countries (Louisiana,1953),p.18.
[35] 例如可参见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29。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29.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744.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107.
[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247.
[4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V,p.93.
[41]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50.
[42] Sampson,G.(ed.), 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 (London,1910),p.203.
[43] Roper,W., The Lyfe of Sir Thomas Moore,Knighte ,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197(Oxford,1935),pp.11-12.
[44]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8.
[45] Stow,J., 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ed. Morley,H.(Stroud,1994),p.190.
[4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09.
[47] Ellis,H.(ed.),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2 nd and 3 rd series(London,1827,1846),p.125;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Appendix,no.57.
[4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1768.
[49] Knox,J.,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 ,first published 1558(New York,1972),pp.9-10.
[50]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56-63.
[51] Black,M.et al., 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 (London,1993),pp.284-287.
[52] Black,M.et al., 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 (London,1993),p.140.
[53] Black,M.et al., 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 (London,1993),p.156.
[5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90;Vol.VI,Part I,p.17.
[5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09;Vol.IX,no.862;Weir,A., Henry Ⅷ:King and Court (London,2001),p.307.
[5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197. See also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
[5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s.819,840,855;Vol.XIV,Part ii,no.782.
[5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69.
[5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