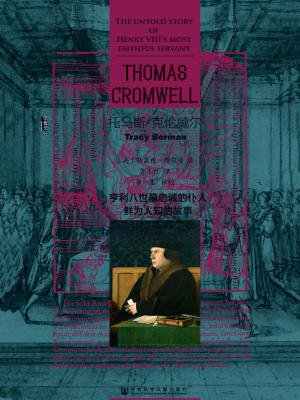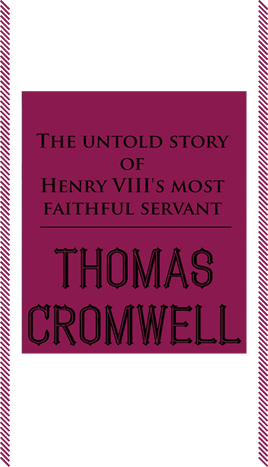
第五章
“人事的弱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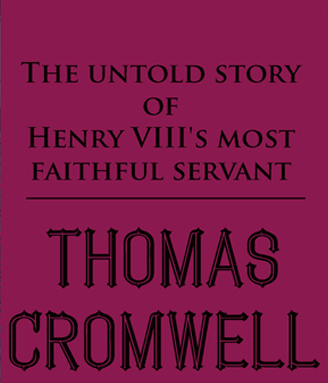
这一时期克伦威尔所在的宫廷是世界上最耀眼的宫廷之一。据一位心怀艳羡的外国访问者所说,亨利的宫廷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宏伟、非凡、华丽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供君王居住,但到16世纪早期它已成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政府机构所在地,以及学者、艺术家和该时代一些最伟大思想家的聚集地。作为时尚和优雅的典范,它决定了整个国家服饰、艺术和建筑的潮流。
亨利八世拥有的宫殿数量冠绝历代英格兰君王。其中最主要的是坐落在泰晤士河岸边的奢华宫邸群:从庞大的怀特霍尔宫到宏伟的伦敦塔,再到辉煌的汉普顿宫,他的宫邸令举世羡慕。这些宫殿以最精致的挂毯、色彩艳丽的丝绸和天鹅绒装饰,有金银图版、精美的雕塑和绘画点缀,即便在阅历丰富的廷臣看来也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家具上镀有大量金属,挂毯都穿织着大量的金丝线,所有的东西都涂着明亮的色彩,以现在的品味来看可谓艳俗。就连地板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或是铺上了色彩艳丽的地毯。尽管大多数室内装饰如今都已不存,但假如站在汉普顿宫巨大的大厅里,抬头凝视那些留存至今的悬臂梁屋顶上令人惊叹的工艺,以及为提醒众人宫廷内隔墙有耳而设的、俯瞰着廷臣们的小型人头像“窃听者”(eavesdroppers)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敬畏和惊奇。
亨利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度过,在他伦敦的宫殿里住的人是最多的。每天挤在议事厅里的廷臣没有数千也有数百,为他们提供食宿等必要服务的工作如军事行动般忙碌。在夏季或伦敦城受时疫威胁的时候,国王和少数受宠的廷臣会去伦敦以外的宫殿或者显赫的贵族和枢密大臣的府邸“巡游”。他们会在一地待到正好耗尽主人所拥有的物资为止,然后带着庞大而冗杂的车马与侍从队伍搬到下一个住处。这支队伍就是一个流动的宫廷,国王和随从平均一年要搬迁30次——不过随着国王的身体不再矫健,搬迁的次数也少了一些。
皇家宫殿是按照大致固定的规划建设的,这反映了都铎王朝的王室成员比生活极其公开的中世纪君王更渴望隐私。因此,诸如大厅之类的公共空间抑或“公务”空间和私人起居套房之间的划分越来越明确。亨利和妻子的住处彼此分开,沿着一条正式的、列队仪式时用的路线分布,越往里走就越隐蔽、越私密。外围的房间有守卫室和接见厅。接着是寝宫——国王的内室,他在这里用餐、跟客人交谈、处理公务,或者休息。再往里是一个人的或者说“私密”的住处,其中有国王的主卧室和小卧室,还有一间密室(可以是个人祈祷室也可以是书房)和马桶。
因为只有最受宠的廷臣才可以进入寝宫,所以它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重要性,只有枢密院可与之相比。后者通常由19名左右的成员组成,几乎每天都要聚集讨论并决定所有政务。亨利在位的时候寝宫的内侍人数有所增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持续工作。随着亨利的统治延续,这些寝宫内侍的个人权力抑或非正式权力——他们可以在国王的“休息”时间向他请愿、影响他的决策——跟枢密院大臣掌握的正式权力抑或“官方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聪明的廷臣会确保自己在两处都有涉足。
不过,宫邸仆人和枢密院大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随着亨利在位时间的增长,宫廷因派别斗争日益分裂。这些派系在不同的时期,由有影响力的廷臣和枢密院大臣根据不同的问题结成,其成因涵盖了对外政策乃至国王的婚姻问题。他们的权力之争主导着亨利宫廷正式和非正式的生活。弗朗西斯·布赖恩爵士(Francis Bryan)说那里有着“过剩”的“恶意和不快”是有充分理由的。政治联盟的聚散之快令人不知所措,如果某个派别看上去要失去国王的青睐了,它的成员就会叛离,没有什么忠诚或原则可言。诺言不能当真,没有人值得完全信任——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真诚。很多人批评这种生活方式。莱尔夫人(Lady Lisle)的代理人约翰·休斯(John Husee)也认同布赖恩的观点,他提醒道:“每个人都应该当心宫廷里的阿谀奉承。”同时,亨利后来的王后简·西摩尔把宫廷描述为一个“充满骄傲、嫉妒、愤慨、嘲弄、轻蔑和讥笑”的地方。 [1]
亨利八世喜欢被跟他志趣相投的廷臣所簇拥。诸如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安东尼·布朗爵士(Anthony Browne)和威廉·康普顿(William Compton)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不仅与他兴趣相投,体格也跟他相仿:高大、仪表堂堂。据说国王有意挑选跟自己相似的人。从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来看,克伦威尔——至少在体格上——跟他的君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克伦威尔开始辅佐他的时候,亨利已经没有了青年时对运动的热情,腰围也长了不少。克伦威尔的体格也可以称得上肥胖。跟他的君主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有很好的运动技能,虽然在青年时期他的身体足够强健可以从军。不论怎样,两人现在都安于中年的舒适,有着与年龄相称的腰身。
要不是在宫廷服侍的回报至少与风险大抵相当——甚至比风险大的话,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在这种诡谲多变的地方度过一生就令人费解了。虽然亨利对宫廷和政府的掌控绝没有他的父亲那么紧,但他依然是权力和晋升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廷臣来说,能够近距离、经常接近国王是一个关键的前提——克伦威尔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曾向夏普伊坦言:“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人事的弱点,特别是宫廷的人事,他亲眼见证了几个可以称得上是身边的例子,他总说如果命运像待他的前辈一样待他,他会以耐心为装备,把剩下的交给上帝——这是非常正确的,正如我之前说过,他要依靠上帝的帮助才不致遭逢厄运。” [2] 奉行这种哲学是明智的,但是后来克伦威尔的乐观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考验。
到1530年年初,克伦威尔显然已经成为宫廷中的后起之秀。他不仅用最初几个月来稳固自己的位置,还坚持不懈地修复沃尔西与国王的关系以避免前者被控告叛国。失宠的枢机主教的感激之情横溢,用各种方式称呼他的前门徒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唯一的救兵”“我忠诚的托马斯”“我唯一的避难所和帮手”。 [3] 不过,尽管充满感激,但枢机主教对他这位门徒的期待有些不切实际。他拒绝承认自己辉煌的日子已经结束,一直试图再得国王宠爱,称克伦威尔是他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敬畏上帝的你不要现在离弃我,因为如果你离弃我,我将无法继续生活在这令人痛苦的世界上,”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呼求,“你不会相信这让我改变了多少,因为我没有从你那里收到关于我的事情的进展和行动。” [4]
尽管说了这些好话,但沃尔西是所有乞求克伦威尔帮助的人当中要求最高的。虽然他声称不在意“这个世界的好与坏”,只想“有适当的收入可以供养自己的家,恩待自己可怜的用人和亲戚”,但他显然不能适应经济窘迫的境遇,坚持说他生活一年最少需要4000英镑——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相当于今天的130万英镑。他甚至要克伦威尔给他送来一些鹌鹑做晚餐。以没有人愿意给枢机主教送鹌鹑为借口,克伦威尔相当恼火地拒绝了他。一份约在这个时期制作的沃尔西物品的存目揭示了他过去10年异常奢靡的生活。存目收录了很多挂毯和天鹅绒幔帐、27个羽毛铺盖、157床羊毛床垫、88个羽绒枕头、绣花丝绸床单、“金线绸”垫套、威尼斯地毯、水晶杯和金杯、镀金杯盘,还有很多其他财宝和装饰品。
克伦威尔在看到前侍主这些越来越坚决、不切实际的来信时的愤怒可想而知。沃尔西把他置于一个在任何能力或说服力略差的人看来都难以忍受的境地。但是克伦威尔在欧洲大陆游历多年和辅佐沃尔西期间学会了交际的艺术,他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国王的性格和情绪。这一点在1530年2月12日他求得亨利对沃尔西的赦免时得到证明。 [5] 之后不久,他的前侍主恢复约克大主教的职位,重获除了约克坊以外的其他资产。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略长于四个月的时间里,克伦威尔将沃尔西由一位行将面临叛国指控的失宠大臣再一次转变成英格兰最重要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他是在没有职权、缺乏人脉的基础上,在为枢机主教的政敌所充斥的宫廷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现在,沃尔西和克伦威尔本人都得到了国王青睐。
但沃尔西仍不满足。一个稍微不那么有野心的人可能会满足于仅得赦免,这样即使不能飞黄腾达,也可以安稳度过余生。但是枢机主教太习惯于富足和奢靡,他给克伦威尔寄送了多封语带恼意的信件,督促其保护自己的财产。他特别想保留温彻斯特教区和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或者,如果国王想从他这里收走这两处圣职名下的财产,他希望克伦威尔能够为他谋得一笔抚恤金。“上帝做证,在我上交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并且也得到保证不会失去我的任何一个职位;尽管法律严苛,但我被指控任一罪行都不应受如此惩罚;因而,抱着对国王之仁慈的信赖,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希望国王陛下也能给予相应的考量。我听到很多好听的话,但很少看到令人欣慰的行为。” [6] 尽管他口头忏悔,但枢机主教满是自以为是的愤慨,他督促克伦威尔对国王晓之以理。“至于加诸我身上的罪状,一大部分是不真实的,其中真实的那些也不足以用来控告我曾对国王本人或王国怀有恶意,或蓄意蒙骗。”从沃尔西建议克伦威尔用在国王身上的策略可以一窥他本人跟亨利的关系,因为他力劝克伦威尔把对国王的顺从放一边,“要大胆行事”。 [7]
这种策略在沃尔西权力位于巅峰的时候或许有效,但是克伦威尔与国王还不够亲近,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更加圆滑得体的方式。他对沃尔西说:“我已就财政部门(Exchequer)对您的控诉和其他针对您的控告为您请求了赦免,这已在国王的各法院得到批准;针对您行为的控诉也因此取消了。”但沃尔西仍旧不满意。虽然他被赦免了,但约克的地产并没有被立即还给他,他敦促克伦威尔查一下发生了什么。他的这位前门徒请他耐心等待,因为结案要走必要的法律程序,而这要花一定时间。“这会让您非常不快,但是最好忍受。这是因为,倘若您不能收回这些资产,那么即便在得到赦免之后,您也无法安坐主教之位,而由于国王在法庭备案之前为您提供了赦免。所以这一赦免目前仍未生效。只有等到您的职务正式恢复之后,赦免令才会名副其实地完全生效” [8]
诺福克公爵因枢机主教逃脱了更多报复而被激怒。当约翰·罗素爵士以为沃尔西现在有望返回宫廷的时候,这位公爵“开始大声宣告自己宁可生吞了他也不愿就此罢休”。在这件事上,他要把枢机主教赶得远离宫廷才罢休。3月初,他通过克伦威尔命令枢机主教出发去约克。因不愿离宫廷那么远,沃尔西延迟启程。但到1530年4月,他再无借口拖延,不得不开始向北的漫长旅途。他缓慢而(根据某些说法)庄严地向北进发,途中几次在各个居所停留。虽然以贫穷为借口,但是他以“奢华得让一些人以为他像过去一样大胆的方式”出行。在到达约克的时候,他告诉亨利“让我极为忧伤的是,没有任何可以供我和我可怜的手下们使用的家具用品……我既没有谷物也没有家畜,或者其他用于维持主教府运转的必需品,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借得这些物资”。因此,他总结到,自己正“陷于困苦之中,各方面都缺乏;除了最仁慈、慷慨的国王陛下以外,不知道还可以从哪里得到援助和解救”。 [9]
克伦威尔耐心渐失。沃尔西此前一直抱怨他不来伊舍拜访自己,现在又扮成了一个完全被忽视的人。尽管枢机主教的反应趋于夸张,但他对克伦威尔不再关心他的指控并非全然无稽。毫无疑问,克伦威尔仍在为沃尔西的利益而努力,但他慢慢开始建议枢机主教向枢密院的其他成员请求援助。 [10] 他还开始仅传达国王和其他人的话,而不是用未来情况会好转的保证让信件更乐观轻松。在一封信中,他甚至传达了诺福克公爵的口信:“你要满足于现状,不要经常打扰国王……因为他认为这不合时宜。”克伦威尔也提醒枢机主教,亨利已经“告诉我他注意到自您与诺福克大人结怨以来,您在他和其他贵族面前对诺福克大人素有微词,这些言语听起来像是在挑拨他和诺福克大人”。他继续说道,尽管沃尔西仍在一些领域受到尊重,但他的敌人“要把他彻底搞垮”,并提醒道:“大人,有一些人提出大人您的房子太大、家仆太多,而且您一直都在建造。因此,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克制一下以示尊重。” [11] 这足够让大多数人胆战、保持低调了,但是沃尔西仍固执地企图重获他认为当属他的资产和财富。
虽然克伦威尔继续为枢机主教效劳,但是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克伦威尔对他前侍主的忠诚让他无论在名誉还是钱财上都受损很多,而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放过他人借债的人。1530年7月,他告诉枢机主教继续为其辩护“花费太多”,自己已无力再承担。他说:“我的财富比您刚陷入困境时减少了1000英镑。”这促使沃尔西给他的这位前门徒一些补偿,但这是由克伦威尔的秘书拉尔夫·萨德勒而非克伦威尔本人出面接受的。这很难说是一种有礼貌的回应。萨德勒告诉沃尔西,他的主人“已经接受了他的好意,但是这跟他期望的补偿有差距”。 [12]
9月29日迷迦勒节当天,沃尔西搬到了约克以南几英里外的卡伍德城堡(Cawood Castle)居住。之后不久,他获悉国王开始占有他的学院以及圣奥尔本斯和温彻斯特的地产。因为这时枢机主教以蔑视王权罪被指控,只要沃尔西还活着,亨利对这些学院收入的转让都是合理的。这时克伦威尔看到了他的优势——或者像卡文迪什所说的那样,“察觉到一个碰巧可以为己谋利的机遇”。只有一位具备他那样出色本领的律师能够在冗长复杂的程序中找到出路,其中一道程序是确保这些转让可以长期有效。这些转让的获得者们因此不得不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并给予丰厚的报酬。“他们都是来获得我家大人对土地转让的确认的,”卡文迪什说,“继而在温彻斯特和圣奥尔本斯获得土地转让的每个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富绅,都开始请克伦威尔代理他们的案子,从我家大人那里得到他的确认,他们为他在其中的付出给予丰厚的回报,并且每个人都向他保证始终乐意用他们不大的权势为他效劳。”
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收获。“现在凡事都开始以与他的职位晋升相对应的方式增加克伦威尔大人的名望”,卡文迪什说。以前请求沃尔西介入的所有人“现在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诚心诚意地拜访克伦威尔大人,他从不拒绝,承诺会在相应的案子上竭尽全力,他有很好的接近国王的机会,可以处理各种各样他负责和管理的事务;通过这种途径、靠着机智的言行,他越来越得国王宠爱”。据卡文迪什所言,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通过解决棘手的法律难题使每个人获益(可能除了他的前侍主以外),他让自己一跃成为宫廷中极受尊崇、极有影响力的人。“因此他的名气和友好态度在众人中传响。他诚实而贤明的名声传到国王耳中……以至于国王也认为,他拥有与名声相符的智慧……他在这个过程中跟国王的对话使国王越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一个适合辅佐他的人,正如后来的实际情况一样。” [13]
沃尔西听闻他挚爱的地产被夺取后非常悲痛。克伦威尔本人记录道:“枢机主教因他的学院被解散并拆除一事而深受打击。”起初,沃尔西的悲伤还较轻,将他的“可怜的房产和学院”托付给“你和其他好朋友,帮助、救济他们”。但当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被拆除时,枢机主教在悲痛面前丧失了平常的冷静,他“谦恭地跪着流泪”恳请国王至少放过牛津学院。他也给克伦威尔送了相似的信息,哀痛地说他“因悲伤流泪以致下不了笔”。他继续感谢他的这位门徒付出的“所有努力”,承诺在他有能力的时候“报答他”。 [14] 然而,由于回信迟迟不到,沃尔西的悲痛变成了怨恨——大多是针对克伦威尔的。显然沃尔西听闻传言说他的前门徒背叛了他,从他地产的四散中获利。枢机主教跟别人抱怨,惹得克伦威尔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质问枢机主教是否还信任他。
有人告诉我大人您对我有些怀疑,就像我真的对您有所隐瞒,或者做了任何有悖于您利益和名誉的事一样。考虑到我的所有付出,我很惊讶您会这么想,或者私下这么控诉……我真的恳请您,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请让我有机会为自己正名。我认为大人您应该写信直白地告诉我而不是暗中诬告我……不过我对大人你的善意不减……上帝在我们中间做证。大人您确实在一些事情上做过了头,您应该在考虑可以跟哪些人说哪些事情时三思而后行。 [15]
克伦威尔精明地判定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朋友告知沃尔西克伦威尔在代理他所有案件时的忠诚之后,情绪缓和的沃尔西温顺地向他保证,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传闻是站不住脚的。“枢机主教努力向克伦威尔表白自己,”有记载显示,“明言没有怀疑他,这点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来,因为除克伦威尔以外他没有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或建议……他向他们共同的朋友询问克伦威尔对他如何,令他欣慰的是,他发现克伦威尔很忠诚。”沃尔西信末是饱含热情的请求,他“悲痛流泪”恳请克伦威尔“保持坚定,不要相信任何不真实的使我们之间产生分歧、让我丧失所有援兵的暗示”。沃尔西后来还寄去了更多都是以卑微的语气写的信函。“我最亲爱的克伦威尔”,他在1530年8月一封称赞这位门徒“仁慈心肠”的信函开头如是写道。 [16]
克伦威尔给沃尔西回信一封以示安慰,但他在信中虚与委蛇,态度近乎无礼。克伦威尔肯定知道自己给出的保证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但他显然急于掩饰自己从这整件让人抱歉的事件中得到的好处。“请大人保持安静,沉着对待关于这些职位的决议,在归还您的资产一事上,会有法院裁决,这不会影响您得到收入,也不会让您另外受任何新的庄园诉讼案的干扰。”他在另一封信的结尾说道:“我恳请大人您知足,好遂陛下之心意。” [17] 通过暗示这一切是国王而不是他的所作所为,克伦威尔精明地转移了沃尔西对他仍存的怨恨。
这个插曲不仅显示了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关系的裂痕,还表明了二人是何等易受宫廷阴谋的影响。虽然沃尔西远离宫廷并且显然不可能重新获得影响力,但是他跟克伦威尔的联盟在意图完全摧毁他们的对手眼里仍是一个威胁。即使在远离宫廷的伊普斯威奇(Ipswich),一名与克伦威尔通信的联络者也汇报称:“在这些地方关于您跟我的谣言会让您震惊。” [18] 在卡伍德显然也是如此,那里也不乏诋毁克伦威尔和他的前侍主的告密者。
沃尔西跟克伦威尔的关系从未完全修复。后来的通信透露了克伦威尔对枢机主教不能接受事实而感到越来越失望,但对个人和政治利益的追求并没有完全冲刷掉他的忠诚。虽然他不能阻止国王占有学院,但他知道这在沃尔西心中有多重要,所以他尽自己所能帮助那里的居住者。牛津主教学院一位心怀感激的教士约翰·克雷克(John Clerke)在12月21日给克伦威尔送了一副手套,以感谢他善待自己和兄弟。克伦威尔10月21日很有礼貌地向沃尔西建议他雇用他的亲属,一个名为卡伯特(Dr Karbott)的学士,“虽然他外表有些朴素,但如果加以重用会很得力”。他接着为沃尔西的一位年轻侍从尼古拉斯·克福德(Nicholas Gifford)做出了推荐并给这个人的性格以敏锐的评价:“虽然年轻、有些轻率,但他诚实、正直、坚韧,会全心全意爱戴大人您。” [19]
忙于枢机主教府中杂务让克伦威尔误以为枢机主教的个人兴趣仅限于那个范围。但除了处理主教教区的事务以外,有传言称沃尔西又开始干预政事了。据他的对手宣称,沃尔西正在跟罗马皇帝和法国国王协商,意图获得教宗禁令让亨利放弃安妮·博林。至于枢机主教是否真的如此鲁莽行事尚有争议。考虑到他是如此迫切地想重得国王的宠爱,这看起来不大可能。更何况,在一份7月向教宗请愿要求批准国王离婚的教会和世俗要人名单上,沃尔西也名列其中。但是,10月23日,当亨利收到一份禁止他再婚并命令其将安妮·博林从宫廷中驱离的教宗手谕时,嫌疑直指沃尔西。
国王很快采取了行动。11月1日他派国王寝宫的侍从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以叛国罪逮捕枢机主教,并快速将他带到伦敦塔。法国使臣暗示流言起于沃尔西府邸的一员:“国王说他密谋在王国内外反抗他们,并且告诉了我地点和计划,此外他的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侍从已经发现了他的阴谋并指控了他。”沃尔西遵命出发去伦敦,但他的行程因病受阻,这场病让他差点倒下。勉强坐在骡子上的他在11月26日晚上到达莱斯特修道院,在那里他对修道院院长说的第一句话是:“神父,我来这里是要埋葬在你们中间。”第二天早晨,他做了最后的告解,说出了那段有名的忏悔:“我看到于我不利的事是如何成形的,但是如果我像侍奉国王一样殷勤侍奉上帝,他不会在我头发花白时放弃我。” [20] 不久之后他就死了。
沃尔西的敌人急于确保枢机主教的名誉在死后得不到恢复,于是迅速开始谴责他。除了将国王离婚陷入僵局归咎于他之外,他们还宣称不能指望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法国使臣轻蔑地说道:“他一直认为一个出身如此卑微而十分自负又有野心的人总有一天会显出他粗鄙的本性,而大多数把他从低位推至高处的人一般会反对他。”简单地说,一切取决于血统之高贵抑或卑贱。夏普伊在这期间也向他的皇帝汇报:“约克枢机主教于圣安德鲁日在离此地约40英里,最后一位理查国王
 战败而亡的地方去世。两人被葬在同一所教堂,人们已经开始称那个地方为“篡权者的坟墓”。
[21]
战败而亡的地方去世。两人被葬在同一所教堂,人们已经开始称那个地方为“篡权者的坟墓”。
[21]
克伦威尔在接到他旧主的死讯后一定五味杂陈。沃尔西是他曾经服侍多年的侍主,也是他在宫廷得以崛起的途径,但克伦威尔在为这个男人的逝世感到悲伤的同时,可能也感到了一些宽慰,因为自沃尔西失势以来他的处境一直颇为不利,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然而,他在国王那里的声望还有被枢机主教最终无可挽回的失宠所破坏的风险。不过,在1530年最后几周克伦威尔被任命为枢密院一员的时候,这样的担忧很快消除了。
对于克伦威尔被选入枢密院的原因,当时的评论者做出了种种猜测。福克斯称克伦威尔的突然晋升得益于他的一些时机得宜的评论被隶属于亨利国库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听到:“正巧克伦威尔所在的地方,有人讨论起国王的资产和财富。当时克伦威尔说,如果国王听我的忠告,我会让他很快成为所有基督教国王中最富裕的。越是听起来合国王利益的话,越早传到国王耳朵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国王就更加了解并看重克伦威尔了。” [22]
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说一位名叫约翰·沃洛普爵士(John Wallop)的外交官兼政客,就沃尔西之死对克伦威尔又是侮辱又是威胁。克伦威尔深受其扰,去寻求国王的庇护。在接下来单独面见的时候,他承诺要让亨利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国王对他的这一提议印象深刻,立刻任命克伦威尔为枢密院成员,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国王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西班牙编年史》也认为“克伦威尔总是在找可以让国王富裕并强化王权的方法”。 [23]
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福克斯和夏普伊一致认为克伦威尔得宠是通过说服君主他可以让后者成为一个富裕的人。这一策略与克伦威尔在掌权者身边天生的近似于鲁莽的自信相称。他在1517年精心安排跟教宗的会面时就展示了这一点。1530年年末,他已经在亨利身边待得足够久、可以判断出亨利对相似的策略会有很好的反应。从此,他所享有的接近亨利的特权不断增长,时常近乎垄断。约翰·福克斯描述他是“国王最私密、最亲近的枢密大臣”。 [24]
加入枢密院对克伦威尔在宫廷的生涯来说是重要的一步,这让他得以进入受国王信任的顾问圈。虽然他是那个团体中次要的一员,主要负责法律事务,但他在表达对各种事务的看法时毫不犹豫。《西班牙编年史》记载,在枢密院会议上“他(克伦威尔)……总是第一个发言”。这完全符合克伦威尔的个人风格。夏普伊曾经记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当时克伦威尔“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沉思了一会儿”。另一次,他打断了一群显贵人士的交谈,说:“够了,我们开始工作吧。” [25] 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直言不讳并且——最糟糕的是——出身低下、自命不凡的人突然出现,无疑令一些更高贵、地位稳固的人,比如沃勒姆大主教(Archbishop Warham)和沃尔西的旧敌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厌烦。尖刻的乔治·卡文迪什用下面的诗来描述克伦威尔在枢密院的突然出现:
有高贵的鹰在,一个骑士也无法动弹;
虽然一只鸟可以在金笼子里叽叽喳喳,
但是鹰依然会鄙视他的出身。 [26]
相反,霍林斯赫德称,克伦威尔卑微的出身使得他迅速崛起得势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很好地显示了英勇美德的好处,让人向着名望和荣誉前行,不单靠着出身和血统这些仅适用于贵族并被贵族占有的优势,而是靠着所有天赋的赏赐者和给予者——伟大上帝的安排,他无数次抬高最低下的贫穷人使他们与君王共处。” [27]
诺福克在沃尔西失势之后迅速夺权。1530年11月,威尼斯大使就汇报说,国王“在所有谈判中重用他超过任何一个人……各项职责都被移交给他”。 [28] 虽然一年前他帮助克伦威尔在议会谋得一个议席,但他不是克伦威尔的盟友:事实上,他迅速将对沃尔西的敌意转移到克伦威尔身上。同时,枢机主教的另一个前门徒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成为克伦威尔的死敌。他深以为国王会将对已故枢机主教的宠爱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没想到这种宠爱却给了克伦威尔,因而他对这位新任枢密大臣产生了难以平息的、经久不衰的憎恨。虽然他们的通信不失礼数,正如宫廷礼仪规定的那样优美,但是敌意偶尔会暴露出来。在一封信中,克伦威尔责备加德纳:“你的这些信言辞表达不甚友好,我认为与我对你的好意并不相称。”在另一封信中,克伦威尔指责对方“易怒”并且对自己持有“恶意”。 [29]
不过——至少此时——这段危险而牢固的对立关系没有阻挡克伦威尔继续得宠。亨利很快发现了克伦威尔的潜力,并且在让其进入枢密院的任命之后很快进一步提拔了他。翌年年初,克伦威尔开始担任从已故枢机主教那里获得的学院地产的接管总负责人和管理者。一年后的1532年1月9日,他的这一职位正式确立。
克伦威尔学习沃尔西的经验,决意要让自己成为国王不可缺少的人。他负责王室地产的出售和接收,监督在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的建筑工程,听取诉讼并且决定带到他面前的囚犯和重罪犯的命运,并参与其他各种执法事务。他很快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求助缠扰,表明时人普遍认可他对国王的影响力。一些在宫廷里颇有地位的人现在收回了他们的傲慢,转而寻求这位铁匠之子的帮助。其中有亨利最亲密的朋友和妹夫萨福克公爵,还有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Henry Bourchier)。
尽管在宫廷的职责越来越多,但是克伦威尔在这期间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私人法律业务——或许是考虑到如果自己的政治生涯化为乌有的话,还有这份生意可以养活他。但是在当时看来,克伦威尔的仕途几乎没有所有都化为乌有的迹象。他的私人事业与政治事业都进展顺利。对他法律援助的请求从四面八方涌来:商业机构、宗教场所和个人都花费相当大的金额购买他的服务。1526年8月一位名叫乔治·莫诺克斯(George Monoux)的市议员向克伦威尔保证,如果他的“大事”能够成功结案,他会支付后者20马克(约等于现在的4500英镑)。 [30]
克伦威尔也继续他的个人借贷业务,这令他获益颇丰。他的一个债务人名叫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借了一笔100英镑的巨款。当他无力偿还的时候,克伦威尔写信告知他:“因为拖欠债款,你已经欠了国王1000马克,我认为你应该充分重视此事,因为国王既不是你可以欺哄也不是你可以嘲弄的人。” [31] 这封信证明,不论当时在政府的新职位如何占用了克伦威尔的时间,他依然紧盯着自己的个人生意。他显然还使这两个事业相互配合:如果有一个债务人没能偿还,他就会用国王的怒火威胁他。
1531年1月议会再次召开。
 虽然议会自克伦威尔1523年第一次进入下议院以来只召开了寥寥几次,但他现在的影响力已举足轻重。1531年3月该次议会结束,他带回家不少于29项已被录入法案汇编的法案——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由他发起的。到了夏天,远至德比郡也有传闻称“克伦威尔一人确定了议会的某些事务,没有人反对”。
[32]
国王本人现在也充分意识到克伦威尔的能力,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就当时最要紧的事积极地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
虽然议会自克伦威尔1523年第一次进入下议院以来只召开了寥寥几次,但他现在的影响力已举足轻重。1531年3月该次议会结束,他带回家不少于29项已被录入法案汇编的法案——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由他发起的。到了夏天,远至德比郡也有传闻称“克伦威尔一人确定了议会的某些事务,没有人反对”。
[32]
国王本人现在也充分意识到克伦威尔的能力,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就当时最要紧的事积极地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
克伦威尔参与国王“大事”的第一个迹象是他起草了一些关于此事的法律法规。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任何程度上影响了诉讼:他看起来只是作为亨利的代理人和起草者,沉默而勤勉地执行一项既定政策。这所有一切都将改变。
枢机主教波尔提供了一份亨利和克伦威尔之间第一次讨论这件“大事”的谈话记录。在请求国王原谅自己大胆在这样一件他所知甚少的大事上发表观点之后,他说自己对国王的忠诚不允许他在有机会——不管多小——为国王提供帮助的时候保持沉默。克伦威尔继而把未能促成离婚的责任完全推到亨利的顾问身上。他们太看重“平民大众”,而不是“睿智博学”但支持离婚之人的建议。鉴于唯一的阻碍是教宗,那这个难题的答案就简单了:与罗马当局断绝关系,像德意志的路德宗教徒那样。
长达几个世纪以来,教宗和他的宗教会议把持着对教义的决定权和对教会司法事务的最后裁决权,征收教会税并对主教的任命有最终决定权。此前英格兰在天主教会辖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所接受的——尽管那些支持国王婚姻无效的人对此日益不满。但现在,波尔声称,克伦威尔让国王明白跟罗马决裂不仅合他心意,而且颇为可行。英格兰就像是一个两头怪兽,他说。如果国王让自己成为教会的首脑,那么教宗这个头颅就必须被砍掉,且他的追随者(包括神职人员)只能听命于亨利。波尔说国王对克伦威尔的计划大感喜悦,命他立即实施。 [33]
尽管波尔的记述令人信服,但是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他的这一记载。宫廷里大多数主要的同时代评述者——尤其是帝国大使夏普伊——把1530年到1533年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件看作国王一人所为。不过也许——甚至很可能——克伦威尔在这整个期间都在幕后默默地工作。亨利本人几乎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一个政坛新人,并且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政坛新人的建议下采取这样激烈的举措的,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可信度,相比之下让世人以为这些举措源于自己则要好得多。这个时期人们对他权威的尊崇是如此之高,一个政策以他的名义推行要比以一个枢密院新成员的名义推行更能成功得多。克伦威尔的权柄来得如此突然并且又如此稳健,他一定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这事实也暗示了在辅佐亨利的前三年克伦威尔的影响力被隐藏了起来。夏普伊不是宫廷中唯一了解这一事实的大使。 [34]
仅通过跟国王的一次简短会面,克伦威尔就把抵制教宗权威的想法植入了亨利的脑海,进而使国王开启了一系列剧烈并会永远改变英格兰政治、宗教图景的事件——虽然这一观点很吸引人,但亨利的这个想法可能是渐渐形成的,并且还要得益于除克伦威尔之外的其他影响。因教宗拒绝批准他的离婚而沮丧的亨利开始更加愿意倾听法律界和学术界很多不同专家的意见,来力证他对英格兰教会的绝对管辖权。不过,克伦威尔的论证更令人信服,并且拿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为一个即将被无止境辩论和谈判所充斥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1530年开始,一群由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博士引领的学者辛勤工作,在一堆包含《圣经》原文在内的旧文献中寻找可以支撑国王对教会的管辖权这一新观点的正当理由。他们收集的文献,又称《丰文汇编》(
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
)
 ,被用作论证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享有绝对宗教和世俗主权的依据。他们对文献的解读经不起推敲,但足以助长国王的改革热情。他开始了一场针对教宗权力的改革运动,不惜一切代价直到实现他的终极目的:跟凯瑟琳离婚,与安妮结婚。
,被用作论证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享有绝对宗教和世俗主权的依据。他们对文献的解读经不起推敲,但足以助长国王的改革热情。他开始了一场针对教宗权力的改革运动,不惜一切代价直到实现他的终极目的:跟凯瑟琳离婚,与安妮结婚。
意识到英格兰神职人员对离婚计划表现出的不满,亨利决定威胁他们屈服。1531年1月末,亨利签发了针对英格兰全体神职人员的王权侵害罪令状,要求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以1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320多万英镑)的津贴换取大赦。当时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抗,但是他们不敌国王。亨利增加了五个新的条款,包括要求他们承认他是英格兰教会至高无上的领袖。随着教会和国王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主要人物很快浮出水面。教会反抗的带领人是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连同坚定的保守派约翰·费舍(John Fisher)主教。国王的诉讼则由两人领衔:下议院发言人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和托马斯·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对国王诉讼的主导体现了他高升的程度和速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一个行政职责较次要的议会新成员转变成当时最重要、最有争议、最紧要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一事件既具有国内意义又具有国际意义。意识到亨利的威逼策略除了制造僵局之外很难达成更理想的结果,克伦威尔对沃勒姆和他的支持者开始了魅力攻势,向他们保证国王没有为自己增加新的权力。有理由保持怀疑的他们不为所动。克伦威尔继而改变策略,说服教士会议——神职人员的一个代表集会——接受给国王授予一个打折扣的头衔,只在基督律法准许的程度上承认国王的最高领袖地位。他们最终依克伦威尔之言同意了亨利的条款,并在1531年3月8日缴纳了津贴。这只是法律行文上的一个细枝末节,却有着巨大的意义。王权至尊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即使国王对教会的权力依然有些不明确,但也意味着这一权力仍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克伦威尔一下子促成了推进离婚所需要的短期协议,并且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宗教和政治变革打下了基础。时人没有忘记将英格兰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归因于他。一个世纪后,斯特莱普说:“克伦威尔大臣在这一事业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所有这些提议和方法都出自他的头脑。为此,在他被咒骂、引来很多人憎恨的同时,还有更多从对教会迷信的改革中受益的人高度赞颂他。” [35]
虽然克伦威尔越来越多地忙于蒸蒸日上的宫廷事业,但他仍然密切参与儿子格雷戈里的教育,并且定期与儿子的监护人玛格丽特·弗农通信。切金被一个名叫科普兰(Copland)的人代替,在他的指导下格雷戈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个人教育上曾受克伦威尔资助的尼古拉斯·萨德勒,同样也对格雷戈里的学业带来有益的影响。玛格丽特·弗农在1531年向克伦威尔汇报:“您的儿子和老师都身体安好,格雷戈里的学习进展顺利,一日顶之前一周,这都是因为有尼古拉斯·萨德勒,他的资质非常好。科普兰先生每天早上给他们每人上一堂拉丁语课,尼古拉斯能够牢记格雷戈里和他自己的课业内容,并且在给定的时间里帮助格雷戈里温习。老师非常欣慰,每天教他们三次。”在另一封信中,她向克伦威尔保证:“您的儿子安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并且能够理解祈祷文和教义。等您下次来我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您会非常喜欢他的。” [36]
玛格丽特对格雷戈里的信仰教育尤其关心。克伦威尔显然曾答应为这一目的派去一位神父,但是当这位神父还没到达的时候,玛格丽特找了一个她认为更能胜任此事的人。她力劝克伦威尔:“请让我尽快知道您的心意,因为我希望您的孩子不至于浪费更多时间。您答应会派来的先生可能主要听从您的命令行事,对孩子不会有很大的好处……您答应让我负责照管这个孩子直到他12岁。届时如果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可以为自己辩解,但现在他还不能,除非有我干预;如果他有一个轻视我的干预的老师,这会让我非常不安。” [37] 玛格丽特于1531年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11岁的格雷戈里似乎已经在剑桥开始大多数科目的学习了。除科普兰先生以外,他的家庭教师还有基督学院的老师亨利·洛克伍德(Henry Lockwood),以及约翰·亨特(John Hunt),他是一位律师,毕业于沃尔西在牛津的学院。后者的专业知识无非是要帮助格雷戈里走他的法律道路。
1531年9月29日圣米迦勒节之前不久,国王发布指令:“在国王即位以来的第23年,由他忠实可靠的顾问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代他向枢密院宣布命令并且毫不迟延地在圣米迦勒节执行。” [38] 这是克伦威尔一举得势的证明:他进入了枢密院的核心集团。仅两个月之后,威尼斯大使就把克伦威尔列入主要枢密大臣名单并位列第七。位置在他之上的是诺福克、萨福克和其他血统最高贵的人士。克伦威尔是唯一的平民,不过他被授予了比很多同僚大得多的职权。这些职权包括监管刑事诉讼、关税和应缴纳的款项,以及就从叛国到下水道等各项事务起草议会立法。同时,因与奥德利密切协作,他接管了国王的法律和议会事务。第二年春天,他已经开始影响下议院的选举了。
克伦威尔此时将他所有注意力转向回报更大也是国王最关心的事务上。如果他能够促成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那么他在宫廷的地位就会无人能及,并且一定不可撼动。
[1] Weir,A., Henry Ⅷ:King and Court (London,2001),p.27;Starkey,D., 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2002),p.17.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0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81-82.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181,6203.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203.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213,6214.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76.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226.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76.
[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199,6344,6335.
[10] 可参见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262。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71.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76;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27.
[13]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6.
[14] State Papers ,Vol.I,no.36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24.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76.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54.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71;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31.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10.
[1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100,6699.
[2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720;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74,178-179;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21] State Papers ,Vol.VII,no.213;Norton,E., 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149.
[22]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655.
[23]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17-18;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31,87.
[24]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5.
[25]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5;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207,239.
[26] Cavendish, Metrical Visions ,Vol.II,p.52.
[27] Holinshed,R.,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p.951.
[28]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p.294-295.
[29]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20,23.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2387.
[31]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57-358.
[3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628.
[33]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92.
[34]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90-91.
[35] Strype,J.,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 ,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316.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s.15,18.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7.
[38] State Papers ,Vol.I,p.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