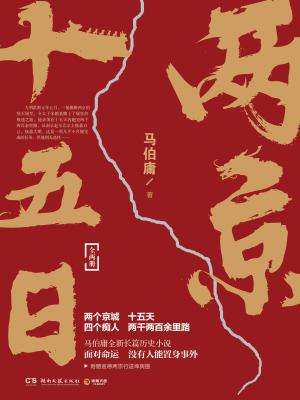第二章

这是明辨无误的杀心!
吴定缘眼神一闪,铁尺顺手往回一送,“铛”的一声,尺面正好挡住了刀尖的进击。他没任何迟疑,身子左旋,右拳直直砸向袭击者的面门。高个儿军汉完全没想到对方的反击如此迅猛,鼻子登时被砸得鲜血迸流,整个人朝后倒去。
吴定缘一击得手,右肩顺势朝前一撞,把犯人朝对面的矮个儿军汉推去。犯人双臂受缚,踉跄朝前,一下子扑到矮个儿军汉的怀里。
趁着两人纠缠的空当,吴定缘完成了转身,疾步向前,从矮个儿军汉腰间抽出佩刀,“扑哧”一声直接捅进他的胸膛侧面,随后立刻拔出。犯人和军汉同时软软倒地,那高个儿军汉才从眩晕中恢复过来。他大吼一声,挥刀砍过来。可吴定缘已完全拔出了刀,直接旋身格挡。
两刃相交,登时火花四溅。高个儿军汉本以为吴定缘是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废物,现在才惊骇地发现,对方居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技击老手。
这片刻的失神,对吴定缘来说已经足够。他用雁翎刀格挡本是幌子,左手铁尺已从下盘悄然递进,正戳在对方腰眼。高个儿军汉疼得“嗷”了一声,动作一霎变形,随即发出一声惨呼,因为雁翎刀的刀刃在他脖颈处抹开了一条深深的沟壑,鲜血喷出数尺之远。
从动手到结束,这一番攻防只持续了几个呼吸,可谓行云流水。吴定缘把雁翎刀插在河滩上,半跪在地,胸口喘息不定。他长期酗酒导致体力有限,只能趁对方心存轻蔑时放手抢攻。倘若陷入对峙,他以一敌二可没有胜算。
这两个军汉肯定是炸船者的同伙,他们沿河搜查,是要将可能存在的宝船幸存者灭口。如今敌人已然毙命,可吴定缘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欣喜,反而浮现出浓浓的悔意。
那个高个儿军汉认得吴不平,说明炸船者在南京城中买通了不少当地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沿途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炸船者的爪牙;任何一个熟人,都有可能拔刀相向。这样的人有多少?该怎么分辨?他一个也回答不出来。
那些连太子宝船都敢炸毁的狂徒,岂会容忍唯一的人证被带回官府,一定欲除之而后快。
吴定缘望着不远处的巍峨城墙,那连绵的墙垣背后仿佛涌现出了无穷恶意,像阴云一样迅速遮蔽了整个留都的天空。他意识到,一时心软救下的这个家伙,让自己陷入一片危险的泥沼。
可如今后悔也晚了,他已经动手格杀了两个人,就算现在扔下那人一走了之,也势必会引来更多杀手。吴定缘厌恶地低头扫视一眼,那个犯人依旧趴在矮个儿军汉的尸体上,虽然头被蒙住,刺鼻的血腥味却挡不住,身体不断地惊恐地挣扎着。
早知道就该让他淹死在秦淮河里,吴定缘不无遗憾地想。
可惜世上并无后悔药,吴定缘叹了口气,动手把高、矮两个军汉的尸体抛入水中,然后把犯人从地上拎起来。事已至此,赏钱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这家伙会惹来无数追杀,尽快把这烫手山芋送出去最好。
归根到底,还得先找到老爹。
吴不平身为应天府总捕头,此时应该是在长安街沿途巡查,那是进入皇城的必经之路。而从扇骨台到长安街,最短的路径是向北走到通济门进城。通济门就在东水关码头旁边,是十三座城门之一,进城后有一条宽阔的通济门大街,与秦淮内河相携北上,右转便是长安街。
不过现在东水关码头陷入瘫痪,通济门前一片混乱。吴定缘观望了一下形势,远远可以看到无数人要跑出来,无数人要冲进去,嘤嘤嗡嗡如炸窝的蜂巢。别说穿行,就连靠近都有危险——敌人能在宝船上放火药,说不定在码头上也有安排。
吴定缘想了想,决定带着钦犯朝东走去。东边三里开外,还有另外一道城门叫作正阳门,进门便是皇城南侧,离长安街不远,乃是御街正门。对方势力再大,总不至于能把每一座城门的门卫都收买了。
那个犯人许是被刚才的血腥搏杀骇破了胆,不再挣扎,老老实实被吴定缘押着走。两人一路沿着护城河向东,很快便来到正阳门前。
前一阵子总是地震,正阳门被震塌了一截门楼拱顶,城门关不牢,现在正在修葺中。灰黑色的城门前搭着密密麻麻的竹架子,门廊下堆满了泥浆盆子和青砖,两扇刚刚卸下门轴的大铁门斜倚在门洞旁边,露出一个大大的豁口。
一大群守军和工匠聚在城门前,惶恐地交头接耳。就连督工和城门将军都心神不宁,一直朝西边眺望。他们应该也听到那巨大的爆炸声了,只是还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
吴定缘亮出锡牌,说要押解犯人进城,一个负责核验的老军提醒道:“要不你换个城门走吧,这里今天可不太方便。”
“不行,这名犯人必须立刻送衙,不得阻滞!”吴定缘下意识地握住铁尺,生怕这也是敌人伏下的杀手。老军还要劝一句,吴定缘厉声道:“此人案涉行刺太子,耽搁了送官,你来背这口锅?”老军一听居然涉及这么大的事,手一哆嗦,连忙把锡牌递回来,让开一条窄路:“这可是你非要走不可,出了事,须怪不到我等。”
在守军和工匠们古怪的目光中,吴定缘押着犯人,迈进那条黑漆漆的城门洞子。
在迁都之前,正阳门是皇城外郭的正门,因此修建得格外宏阔,门洞宽可容两车并行,地覆石板,两侧青砖贴边,上顶用上好的青条石砌成。不过,此时正值修葺,门口堆放着各种营造杂物,遮去了大半边光线。
吴定缘往里走上七八步,周围便暗了下来,状如深隧一般。此时外头是五月天气,可城门洞里还一片凉沁沁,有丝丝缕缕的阴气从砖缝与地隙中钻出来,缠腿而上。
他们两人走到一半,吴定缘忽有所感,一抬头,才明白老军的反应为何如此古怪。
原来在他的头顶,正悬着一块长约三丈、宽一丈的大石条。石条还没被嵌入拱顶,只靠几根麻绳捆吊在半空,晃晃悠悠。在拱顶下方,是塌了一地的脚手架残骸。很明显,刚才的爆炸把支撑的脚手架给震塌了,抬吊到一半的石条一下子变成悬空。匠户们不知何时会再震一次,怕石头掉下来砸死人,先逃去了城楼外面。
这块青灰色的巨石采自幕府山中,边钝质厚。如此庞然的身躯,居然如吊钟一样在幽暗中缓慢摆动,那种随时可能泰山压顶的死亡威胁,着实令人不寒而栗。不知为何,吴定缘没有急忙躲开,反而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苦笑。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城门洞子里,无论来路还是去路都晦暗不清,偏偏在头顶,生死悬于一线。这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不祥谶兆,竟令吴定缘一时入了神。据说,人在面对注定的死亡威胁时,不会移开视线,反而会一直盯着。那种随时可能被砸成一摊肉泥的想象,居然让他皮肤浮起一层说不上是恐惧还是兴奋的鸡皮疙瘩。
身旁的囚犯一直蒙着头,浑然不知身处险境,老老实实站在原地。过了不知多久,他才不安地呜了一声,把吴定缘从死亡的遐想中拽回现实。吴定缘最后瞥了一眼头顶的巨石,摇摇头,这才带着囚犯继续前行。
两人很快穿过门洞,眼前忽现一片光亮,这便算是进到南京城内了。在正阳门北侧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宽衢大街,叫作崇礼街,它的西侧尽头恰好与长安街相交。
崇礼街上如今也不太平,这里是许多官署的所在地。宝船爆炸的冲击,让这边乱了套。一拨拨的步兵、骑兵拥出诸卫屯地,朝东水关那边疯狂地开去,无数马蹄和革靴将街面上的黄土高高扬起。很多小吏书手从衙署门前探出头来,在扬尘中茫然无措地呆立着。
吴定缘看着那些救援队伍,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出了如此大的事,吴不平身为总捕头怎么可能还留在长安街,一定第一时间赶去东水关现场。
可东水关码头现在绝不能靠近,吴定缘思忖片刻,本想干脆把犯人先扭送应天府,可转念一想,也不现实。且不说府衙远在城西,沿途变数太多,就算送到了,现在也没人接收——应天府的高官们,都跑去了东水关等着巴结太子,如今生死未卜。
至于其他衙署,也是同样问题。
南京城内的治安力量颇为复杂。五城兵马司归南京兵部管,十八卫所亲兵由五军都督府统辖,应天府控制着三班,守备衙门掌握着诸城门锁钥,皇城里还趴着一支年初从京城调来的禁军。
这几套城防班底各有统属,平日互不买账。东水关码头这一炸,一干高层灰飞烟灭,诸多衙署群龙无首。整个南京城,已经完全瘫痪。
他现在手握着一名朝廷钦犯,居然无处可以解送。
吴定缘环顾四周,忽然看到在崇礼街北侧,钦天监与行人司之间有一座朱门白墙的衙署。衙署上无匾额,两侧门柱漆成墨色,显出与寻常衙署卓然不同的肃杀气势。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个主意。
那里是南京锦衣卫的镇抚司,它不受南京任何一个衙门的节制,直接向京城的锦衣卫指挥使汇报,不挂匾额,不书牌面,在南京官场的地位超然。
吴定缘“啧”了一声,虽然不无遗憾,但他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到锦衣卫算了。锦衣卫未必会给多少赏赐,但至少可以甩脱这个大麻烦。他最怕麻烦,只想赶快了结这桩意外差事,回家让妹妹烫上一壶酒,清净地待一会儿。
吴定缘拽着犯人走到镇抚司,敲了敲大门,发现居然是虚掩的,一推即开。他往里走了几步,突然听到内院传来一声怒吼:
“国家有难,尔等竟敢置若罔闻?”
这声音势若洪钟,连屋顶的瓦片都被震得嗡嗡作响。吴定缘带着犯人绕过照壁,看到里面是一个宽阔的四方正院,一个身穿浅绿官袍的年轻官员站在院门之前,伸直双臂,死死挡住了对面一排锦衣卫。
这年轻官员二十七八岁,身材不算高大,但鼻梁硬直,眉角飞扬,尤其下巴特别方正,一抿起嘴来,整个面相顽若坚石。
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千户拍拍绣春刀,呵斥道:“我等正要去码头救援上官,怎么就置若罔闻了?”那年轻官员上前一步,目光灼灼,道:“东水关出事,自有守备衙门应对。你们锦衣卫的职责不是救援,而是尽快去查找奸凶!”
旁边一个副千户不由得嗤笑道:“你一个小小的行人,口气倒大得像个大学士!不好好在隔壁待着,反而跑来这里指手画脚!”上前作势要把他推开。
那小官见他们来推搡,涨红着脸,挺起胸膛大叫:“你们一窝蜂跑去码头,贼人正好可以趁乱远遁潜离。若错过时机,只怕东宫危矣!留都危矣!你们……怎么都不明白!”副千户见他脾气犟起来,手里反倒犹豫了。行人虽是个正八品的芝麻小官,可非进士不能担任,他一个武官不敢对文官真的动粗,一时两边僵持在那里。
吴定缘大概听明白了。这官员应该是南京行人司的一个行人。宝船爆炸之后,他跑到隔壁锦衣卫这里,要求他们不要去码头救援,而是马上展开调查。
从锦衣卫的角度来看,这确实莫名其妙。行人司的日常工作是负责颁布诏谕、出使外藩,跑来这里指手画脚,算怎么回事?可锦衣卫的长官此时也陷在码头,剩下这几个千户和副千户群龙无首,愣是被这小小的行人堵住了门口。
说实话,吴定缘很赞同这个小行人的判断。锦衣卫与其赶去码头添乱,还不如抓紧时间去盘查线索。只不过……关你屁事啊。
南京的行人司只是一个闲置空署,在这里注定升迁无望,无非混吃等死而已。南京城里那么多高官,轮得着你一个冷衙门的小角色忧心国事?这小行人八成是吃陈年禄米吃得脑壳坏掉了。
吴定缘懒得听他们争吵,使劲咳嗽了一声。
那个小行人和锦衣卫们同时转头看来,目光都有些诧异。吴定缘把犯人向前推了一步:“在下是守备扇骨台的应天捕吏。擒得太子宝船跳船疑犯一人,特来移交贵卫。”
听他这么一说,人群立刻骚动起来。吴定缘把犯人的头罩一摘,一踹腿窝,让他跪倒在地。那几个锦衣卫瞪大了眼睛,看到一张满面尘烟、神色委顿的狼狈脸孔,一头湿漉漉的乱发散披下来,头上缀满了碎屑残绳。
吴定缘把他在扇骨台的遭遇约略一说,但为了避免麻烦,没提那两个杀手的事。锦衣卫们惯于缉事,立刻明白此人的形迹确实可疑。老千户正要走近细问,那小行人却抢先凑到跟前,皱眉端详片刻,伸手把麻核从犯人嘴里抠出来。
蓄积已久的愤懑,猛然从犯人嘴里喷泻而出:“你们这些老獾叼的杀才!没眼色的驴狗卵子!我是大明太子!大明太子!快放开我!不然诛尔等三族!不,九族!十族!”小行人双眸一闪,赶紧将他从地上搀起,解开束手的绳子,然后一撩袍边跪倒在地,口称“殿下”。
这一番变故,让周围的锦衣卫都有点发蒙。老千户狐疑道:“你一个小行人,怎么知道太子长什么模样?”那年轻官员下巴一抬:“我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曾在殿试时亲眼见过太宗皇帝,和眼前这位,当真是一模一样!”
周围的人还有些不信。朱瞻基从脖颈里摘下一枚青莲云形玉佩,怒气冲冲地举手一晃,喝道:“你们来看!”
这枚玉佩是当年他跟随祖父出征时,永乐皇帝于营中所赐,上镌“惟精惟一”四字,他从不离身,天下都知道这是太子之物。锦衣卫们看到这件信物,登时再无疑问,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只剩吴定缘一个人愕然站在原地,全身僵直。
这个炸船的疑犯,居然会是大明皇太子?
这……这也太不合常理了,宝船明明已经接近东水关,太子应该在东宫幕僚的簇拥中准备下船才对,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船尾去?
一直到他的双臂猛然被人钳住,吴定缘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原来是几个小旗冲上去,恶狠狠地把这个挟持太子的反贼压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吴定缘“嘿”了一声,似是自嘲般地笑了笑,也不挣扎,把头慢慢垂下去。
老千户知道把此人留在现场,只会让太子尴尬,喝令道:“把此人先投进内狱,容后再审!”小旗们发一声喊,连拖带拽把吴定缘带到后院去了。看着那莽汉的身影消失,老千户这才亲自从院内掇出一张圈椅,讨好地请太子暂且歇息。
朱瞻基一屁股坐下去,双眼怔怔地盯着照壁,胸口起伏不定。他的脑子,一直到现在仍是懵懵懂懂,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先是一场令人筋熔骨销的大爆炸,然后又几乎溺毙于冰凉的河水之中,接下来被人蒙住了脑袋,踢踢打打,还有刺鼻的血腥透鼻而入——如果是噩梦的话,现在也该清醒了。
小行人从地上把玉佩捡起来,检查了一下并无破损,毕恭毕敬地双手递还给朱瞻基。朱瞻基抬起眼,喃喃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众人面面相觑,具体怎么回事,他们也说不清楚。最后还是那位小行人大声道:“殿下座船被贼人所炸,波及东水关码头百官。”周围的千户、副千户们倒吸一口凉气,你小子好大胆,局势尚未明朗,就敢铁口直断,这个话要不要负责?
朱瞻基看了这小行人一眼,他刚才脑袋被罩着,听见有个声音嚷了句“东宫危矣”,心中颇有好感:“你叫什么名字?”
小官连忙回道:“微臣是南京行人司行人,于谦。”他说这话时声音洪亮,双眸熠闪。那老千户暗自不屑,你三十岁不到就混在一个养老的冷衙门,不知有什么可自豪的。
朱瞻基点点头,说了一句“你很好”,便不言语了。于谦趁机道:“如今城内形势未靖,还请殿下暂且驻跸于此,待襄城伯、三保太监有回话过来,再动不迟。”
朱瞻基眉头轻皱,道:“他们如今身在何处?”于谦回道:“两位皆在东水关码头迎候殿下,目前情形……呃,尚不清楚。殿下万金之躯,得天独眷,宜遣人先行询问,待两位镇守前来接应为宜。”
于谦相貌端方,讲起话来又喜欢直视对方,颇有说服力。朱瞻基决定听他的,先留在锦衣卫这里观望形势。老千户不忿于谦抢了风头,也上前抢着给太子通报姓名。
朱瞻基对他可没什么好脸色,毕竟这小老儿刚才还试图阻挠于谦。老千户见状不妙,连忙自告奋勇,说要亲自前往码头打探消息,然后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老千户走了以后,院里的人给太子打来一盆井水,请他洗脸沐发。锦衣卫们平日里习惯收拾犯人,真伺候起贵人来实在粗手笨脚。朱瞻基勉强洗了几把脸,整个人随后蜷缩在圈椅里,双手无力地搭在两侧扶手上。
往常这些事,自有伴当代劳,可如今那一干人包括赛子龙都已粉身碎骨,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一念及此,朱瞻基心中便有无穷的悲恸涌上来。随悲恸而至的还有一阵紧似一阵的惊悸,像皮鞭一样抽打着脑中的神经,让那恐怖的爆炸画面不断被唤醒。
于谦不敢打扰太子,一个人骤逢大变,需要一些时间来静待消化。他走到旁边一个副千户前,说给太子端杯热茶去,最好搁点压惊的酸枣或柏子仁。副千户眼睛一瞪,心想你算哪根葱在锦衣卫指手画脚,可又一想,太子刚夸过这家伙“你很好”,只得悻悻转身,喝令旁人去泡。
于谦又问内狱所在,说要去看看那个绑来了太子的人。副千户有心回绝,可架不住于谦目光凛冽如刀,忍着气也回答了。他叫来一个小旗带路,顺便监视,别让这个行人做什么多余之事。
于谦跟着小旗步入后院二堂。垂花门后是一条回字雕花走廊,一圈都是重檐配房,正北是寅宾厅,两侧依次是签押房、录事房、值吏廨、架阁库,而内狱恰好位于正南位置的甬道尽头。
这里只是作临时周转犯人之用,牢房大多空着,虽然脏了点,怨气倒不算浓郁。小旗见快走到了,好心提醒道:“你问话时可离得远些,免得被这篾篙子沾上赖痞气。”
“哦?你认得他?”
长舌碎嘴乃是人类天性,小旗对应天府情形还算熟悉,便把吴定缘这个绰号的来历约略一说。于谦听完,默不作声走到最后一间,隔着木栅看到了那个有名的败家子。
吴定缘此时被绑在了一个十字木架上,身子紧贴直杆竖立,双手分开与横木平行,丝毫动弹不得,这是对重要钦犯才会采取的措施。他身后的石墙特别厚实,上头只开了一扇巴掌大的小气窗,窗上两根铁柱,把照进来的阳光分割成三道,像三把金黄色的长刀顶在囚犯的后背。吴定缘低着头一动不动,一副引颈待戮的姿态。
不过事起仓促,锦衣卫也只是把他简单捆住,身上衣衫还未剥掉,麻核也没塞嘴——话说回来,在锦衣卫内狱里,又能喊给谁听呢?
于谦吩咐打开牢门,走到吴定缘跟前。他身材不算高,必须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吴定缘的面孔。
“我知道你有救驾之功,只不过局势紧急,不得不从权处置。一俟大局落定,我会替你去向太子申明冤屈。”于谦轻轻道。
“我把他从河里捞出来平白受苦,实属罪有应得,哪里冤屈了?”
吴定缘依旧垂着头,嘶声回道。这个刻薄的反应让于谦皱了皱眉头。他走近一步,道:“太子骤经大变,神志未复,又不是故意陷害你。你快把太子落水前后之事,给我详详细细地说一遍,不要有半点遗漏。”
吴定缘懒洋洋地抬起头:“难道不是该锦衣卫来审吗?你一个小杏仁不管咸淡,倒管起闲事来了。”他故意把“小行人”说成“小杏仁”,于谦额头登时浮起一条青筋,不由得怒喝道:
“现在局势危殆、都城动摇,只要是食君禄者,人人皆有责任赴难济危,还分什么闲事不闲事?”
吴定缘笑道:“好,好,皇上和太子最爱听的就是这话。你把握好了机会,一步登天,须不是小杏仁了。”于谦仿佛受到侮辱似的,揪住他衣襟大声道:“别把每个人都想得像你那么龌龊!我于谦虽然官卑位贱,却不是幸进之徒!”
于谦出身钱塘于氏,最听不得被人说是钻营小人。他嗓门本来就洪亮,加上情绪激荡,竟震得天花板的灰尘都抖搂下来几缕。吴定缘嗤笑一声,斜眼乜着他,不再说什么。
于谦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松开对方衣襟,冷笑道:“你也莫装糊涂。一个应天府的捕吏拿住炸船疑犯,不交给本管府上邀功,却白白送到锦衣卫门口,分明是觉得有性命之忧,想要置身事外。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刚才却没说,对也不对?”
吴定缘嘴角一抽,这“小杏仁”当真敏锐得紧,一句便戳到点上。
于谦气呼呼地瞪着他,道:“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蠢物。太子落水时不知身份,你千辛万苦把他救下来;如今知道了太子身份,你反倒推三阻四,简直是个副藤头丝!”
他情绪过于激动,前头还说着官话,末一句却蹦出一句钱塘土话来。吴定缘多少能听懂一点,知道这是形容不知好歹、顽固执拗之人。
这个骂法,让吴定缘不期然想起自己的父亲。每次他们父子联手破获大案之后,吴定缘坚决不肯露面领功,只讨了钱钞去喝酒、逛窑子。他老爹吴不平给钱时,都会狠狠骂上一句“死孙”——这是个北方的词,意思跟“个副藤头丝”差不多。
想到自己父亲,吴定缘突然意识到,如今东水关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吴不平身为应天府总捕头,肯定也会被牵连进去。万一这案子没破了,以官府的禀性,说不定会把他推出来顶缸,谁让你负责南京地面的平靖呢?
想到这里,吴定缘叹了口气,道:“好吧,好吧,我说还不成吗?”
接下来,吴定缘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讲给了于谦听,如何看守扇骨台,如何看到宝船上的人影,如何救下太子,如何碰到那两个怀有杀意的卫所旗兵,自己又是如何改变主意把人犯押来锦衣卫。
一番话听完,于谦对这个惫懒捕吏倒真是刮目相看。这家伙的谈吐虽然粗鄙,但分析起事端来,简洁精准,切中肯綮,就是积年老吏也未必有这种见识。那个小旗嘴里的“篾篙子”,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精明人。
他极其鄙夷吴定缘一遇到危险便推卸责任的做法,但很认同其判断——这个幕后策划者显然是要把太子和南京官场一网打尽,其野心之大、规划之周密、手段之狠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不幸中的万幸是,太子奇迹般地得以幸免,吴定缘又临时起意,将其扭送锦衣卫。这一连串意外,神仙也没法事先预料,更别说那些炸船的反贼了。
也就是说,太子至少现在很安全。
吴定缘见于谦眉角一下子松弛下来,便猜到了他的心思,不由得嘿嘿一笑,道:“你说,他们花了这么多心思炸船,难道只是为了听个响动?”
“什么?”
“今天,可还没过完呢。”吴定缘抬起眼皮,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
于谦眼皮猛然一跳。
糟了,那个老千户跑去东水关码头打探消息,万一到处表功说收容了太子,难保不会被反贼的耳目侦知。一想到这个,于谦顾不上向吴定缘说明,转身迅速离开内狱,噔噔快步朝前院走去。不管这种可能有多少,必须让锦衣卫提前做好防范。
当于谦回到前院时,他发现圈椅上空无一人,太子不见了,附近那几位副千户也没了踪影。于谦大惊,抓着旁边一个留守的小旗问怎么回事。
小旗倒老实,直接全说了出来。原来在于谦离开不久,码头那边的老千户便传回消息,一好一坏:坏消息是,襄城伯受了重伤,他身在码头最前,受冲击最强烈,一时还未醒转过来;好消息是,三保太监侥幸无事。在爆炸前一瞬,他的大氅半边脱落,几个侍从正手忙脚乱地挡在身前摆弄卡扣,替他挡住了大半冲击。
三保太监见惯了大风浪,临危不惧,坐镇码头指挥。在他的调度下,东水关与南京诸衙署已逐渐恢复了秩序,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恰好老千户跑过来禀明太子下落,郑和一听,亲自赶来迎候,刚刚把太子接走。
那个老千户耍了点手段,接走太子时,故意没通知在内狱的于谦。
于谦听说接走太子的是郑和,不由得长出一口气。郑和是永乐老臣,其人忠直耿介,兼有韬略,几次下西洋的壮举攒下巨大声望。只要有他这尊山岳镇着,南京城乱不起来。
不过,眼下尚不是松懈之时。于谦认为,吴定缘遭遇两名旗兵袭击这条线索很重要,必须尽快让高层知道才行,便讨来一副纸笔。
他笔法流畅,转瞬就写满了一页工整的台阁体。信中警告太子与三保太监,南京城里还有敌人未除,要尽快彻查,不可轻忽。信末还不忘提了一句吴定缘的冤枉之情,生怕贵人们事情一多给忘了。
写完以后,于谦吹一吹淋漓的墨汁,四方叠好揣在怀里,举步匆匆出门。
此时,外头崇礼大街上还是一片混乱景象,两侧街面的旗幌下、沟渠旁、树荫下都站满了人,个个面色惶恐。先前大家只是听到巨响,不明所以,现在宝船被炸的消息已从东水关码头扩散开来,这在南京居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甚至已有零星百姓卷起包袱,扶老携幼,打算出城避难去了。
于谦不知道太子与三保太监如今身在何处,但以情势推断,他们一定会先行返回南京守备衙门,那里是整个留都最安全的地方。
南京守备衙门位于皇城西南角,无论队伍从哪条路线行进,皇城西侧的西华门都是必经之路。他只消从崇礼街转到通济门大街,一路向北穿过西皇城根南街,赶到西华门外的玄津桥,就一定能截住队伍。
于谦略扶一下幞头,把腰间的乌角带提了提,举步从惶恐不安的人群中快步穿过去,钻进一条小巷子里。他来南京已有数年,对城内地理轻车熟路,知道哪里有捷径可走。不消两炷香的工夫,于谦已经跑到了西皇城根南街的中段。
他一踏上街面,伸着脖子朝北边看去,只见烟尘滚滚,前方一百多步开外,一支队伍正匆匆移动着。
这队伍的构成颇为驳杂,里面既有顶盔贯甲的守备衙门亲兵,也有一身短衫的勋贵府家丁,有人腰悬弓箭,还有人手擎金瓜,乱七八糟不成章法。不用问,这一定是护送太子的队伍。东水关爆炸波及人数太多,只能临时拼凑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手。
队伍之中,最醒目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青海大马,上头的骑士头顶高丽冠、身披猩红大氅,无论马背如何起伏,双肩始终稳稳不动。在他身边,还有一抬黄绸阔轿,抬轿的却不是轿夫,而是几个身披彩肩的号手。
那个在马上的高大身影,想必就是三保太监郑和;而他旁边的阔轿之内,只可能是当今太子朱瞻基。
那支队伍移动速度很快,眼下队首已越过桥头的守桥石狮,即将踏上玄津桥面。于谦略喘了口气,加快速度追了上去。
玄津桥是一座三眼白石拱桥,两端斜坡,中间高拱如山。它横跨秦淮内河,对面即是西华门。当年南京还是京城时,百官每日出入皇城,都必须通过玄津桥从西华门入皇城,一度是南京最繁盛的路口。
这玄津桥最大的特点,就是桥两头各卡着两尊石狮,说是镇岁辟邪之用,其实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它们把石桥入口分成三条狭窄的通道,防止太多车马一次拥上桥面。
因此当这支队伍走到桥头,不得不让队形稍做变换。簇拥在前方的护卫让开路面,先让三保太监和那顶阔轿从两座石狮中间的狭窄通道走过,他们再从两侧过道跟上去。
可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没有默契,分进合流之间发生了不小的混乱,互相碰撞拥挤,一度与前头的两位要员拉开了距离。于谦趁机追到队尾,他身材不高,只能看到那顶高丽冠与黄绸轿顶在视野里逐渐升高,徐徐走到玄津桥的最高处。
突然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像毒蛇的牙齿一样狠狠钉在他心脏上。于谦的耳边,蓦然响起吴定缘那淡淡的声音:“今天,可还没过完呢。”
于谦一咬牙,把袍角一拎,骤然加速,瞬间超过了三四个押后的护卫,同时大喊:“快退!快退!”距离最近的卫兵一见有人闯阵,第一时间拦腰合抱,几下扭打便把这个小小文官按在身下。
于谦动弹不得,那副大嗓门却堵不住,“快退”二字的声量从石狮子旁一直传到玄津桥顶。三保太监听到声音,只是微微回了一下头,继续向前。他旁边那顶黄绸阔轿的轿帘,却兀然被一只手掀开。
朱瞻基探出头来,惊疑地朝后头望去。这个声音他记得,是那个锦衣卫里的小行人,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
太子掀帘,轿夫们连忙停下脚步。这一停顿,让轿子与郑和之间拉出了半匹马的距离。郑和勒住马头,正要催促轿夫们快走,鼻子却突兀地捕捉到空气中一丝奇怪的味道。
这味道在他漫长的航海生涯中时时能够闻到,每一次都与战场密切相关,而刚才在东水关码头,也弥漫着同样的味道。
三保太监的反应极快,他一勒缰绳,坐骑扬起后蹄对轿子高高踢去。那匹青海大马生得极为剽悍,钉了铁掌的漆黑巨蹄像一具攻城槌,狠狠撞在轿子顶边的蝠形铜角之上。轿夫们四散摔开,巨大的冲击力推着轿厢,顺着倾斜的石面仓皇滚落下去。
与此同时,从桥下传来一声闷闷的爆破声。整座石桥震颤了一下,从最中间裂开一条大缝。裂缝迅速扩成沟隙,沟隙又变成深壑,很快整座桥面便分崩离析。散开的石块化为无数张裂开的大嘴,裹挟着三保太监连同那头坐骑落入秦淮河中,溅起巨大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