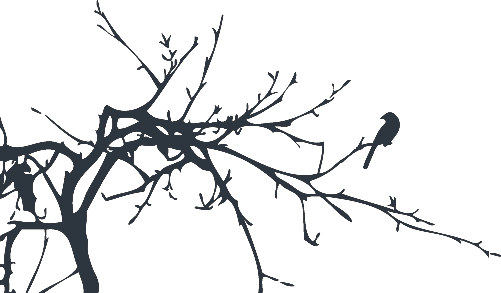
一信之考,旬月踌躇
——《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记事之一


编辑工作是一门学问,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就拿编辑已过世的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这项工作来说,文稿的收集,篇目的确定,版本的校勘,文内人名、地名、事件及其他史实的考订,个别文字的订正和作注释,等等,要求编辑人员具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水平,科学的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辑工作从1983年3月全面展开(1982年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有十几个人参加,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才告完成。
在编辑这本书信选集时,我们对一些信的收信人,写信的时间,信中谈到的一些时间、地点、人名、书名和事件等,进行了核实和考订。全书作了900多条注释。
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文献资料方面我们以档案材料为主要的依据。在北京,我们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和干部档案;还到其他几十个单位,查阅了有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物。我们还到湖南省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查阅档案材料。此外,我们查阅了许多书籍、刊物和报纸。同时,我们开展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在北京进行了300余次的调查访问,到湖南长沙、湘潭、湘乡等十几个市、县访问了近200个单位和个人,并在南京、上海、无锡、宁波等地访问了十几个单位和个人,了解到许多情况,收集到一些文字资料。我们还发出了上百封函调信。
《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辑工作,正是在文献档案资料同调查访问相结合的基础上,在二者互相补充、互为印证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
现在,就《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工作的情况和体会,写成这篇编辑记事。这是总结我们的工作,以便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也是向读者汇报我们的工作,进行编者同读者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把我们的某些一虑之得介绍出来,同我们的编辑工作同行们切磋,共同为编辑学的建设添砖加瓦。
“各位教授先生们”是谁?
在毛泽东书信中,有个别书信的收信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例如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有一封写给各位教授先生的信,这封信没有信封,信是用毛笔写的,有手稿。信的上款是“各位教授先生们”。“各位教授先生们”指的是哪些人呢?
当时的著名教授,较多地住在北平、上海两地。我们认为指北平的教授可能性较大,因为信中说“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当时的抗日前线是在华北。这封信中还说:“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这样,我们决定访问当年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
我们首先访问了郭明秋,询问“各位教授先生们”指的是哪些人。她建议我们访问当年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张友渔。
我们访问张友渔时,他说这封信他记不得了。关于火腿等是谁送去的?他分析说:如果说是上海送去的,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教授身份出面的人不多,主要是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而北平则是由黄松龄、许德珩、程希孟和我等人公开地以教授身份组织了华北救国会,火腿等是北平送去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他还说,黄松龄、杨秀峰和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党外的几位教授的,当时党外的著名教授有许德珩等。
这样,我们来到了许德珩家里,93岁高龄的许老热情地接待我们。当他看完毛泽东写给“各位教授先生们”的信(手稿的复印件)后,欣喜异常地说:“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他追溯那已经流逝的岁月,明确、具体、生动地给我们介绍了有关的情况。他说:“火腿和时表,是我和我爱人劳君展送的。劳君展是新民学会会员,早年就同毛主席相识。1935年12月,徐冰、张晓梅告诉我们,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我们听了很高兴,并问毛主席他们在那里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徐冰说,生活比较艰苦,最缺三样东西,一是没有鞋穿,二是没有时表,三是缺少吃的东西。我当即拿出几百块大洋,让劳君展和张晓梅去买东西。她们在东安市场买了三十几双布鞋、十几只金华火腿、12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徐冰他们。他们问我这些东西送到后要不要毛主席亲笔写个收条。我说:‘不要,这点小事不用写收条。’现在看来,要是有个收条就更好了,可以放在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展览。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请我和劳君展吃饭,周恩来等也在座。劳君展问毛主席:‘过去给你送的一些火腿等物收到没有?’毛主席说:‘收到了,收到了。他们都吃了,我也吃了。’”许老正说到这里,他的秘书牟小东走了进来,许老把信递给他看,并说:“你看这信,我过去对你说过的事,这上面都写着哩!”牟小东看完信后问:“您过去说送的是三样东西,信上怎么没有说到布鞋呢?”许老笑了,说:“信上不是写的‘火腿、时表等’吗?那个‘等’字里面就包含着布鞋了嘛!”我们又问许老,当时看见了毛泽东这封亲笔信没有?他说在记忆中这封信是由徐冰念给他们听的,没有见到亲笔信。
在考证一个问题时,人们常说“孤证不立”。许德珩关于这封信的回忆,对于考证“各位教授先生们”是哪些人,虽然也是一个孤证,但是,这个孤证是有说服力的,可信的。首先,许老的回忆是明晰、详细的,是有情节有过程的,而且是与信的内容相符合的。其次,许老说他没有见到这封亲笔信,而是由徐冰念给他们听的。这一点同我们从文献方面掌握的有关情况也是吻合的。毛泽东给“各位教授先生们”的这封信,在信的手稿第一页的右侧有他用铅笔写的“已发”二字。这一情况说明这封信不是通过邮政递送的,而是用电报发出的。这样,许老当然不可能见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而只能是由徐冰将抄收的这封信的电文念给他们听了。
这种确凿可信的孤证,我们认为是可以作为下判断的根据的。这样,我们将毛泽东给“各位教授先生们”的信,题为《致许德珩等》。
给高桂滋的信是哪一年写的?
毛泽东写的书信,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写明年份,有的没有写明月份,有的甚至连年月日都没有写明。还有个别的书信,他亲笔写了年月日,但仍有可疑之处。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考证写信的时间,也是很费力气的。
毛泽东写给高桂滋的一封信,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抄件上没有写明年月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印的一种内部文集收入了这封信,编者判定的写信时间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存在着一些怀疑。信中说“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这说明这封信是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写的。信中还说:“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这里所说的“政治决议”,应是指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内部文集的编者判定这封信的时间是1935年12月,那就是说这封信是在1935年12月26日至31日之间写的。瓦窑堡会议后的短短六天中,决议就印成了文件,毛泽东等就写信给高桂滋,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不存在,但一般说来是比较小的;相反,在1936年初写这封信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分析,要证实它需要有材料作依据。
信中与判断写信时间有直接关系的一段话是:“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如能查明“四年前抗日之役”指的是什么,那么这封信的年份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经查阅有关的材料和向长期追随高桂滋的齐天然进行了解,弄清楚了“四年前抗日之役”是指1933年的长城抗战。当时,高桂滋的84师与商震的部队在长城冷口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毛泽东等的信中将1933年的长城抗战称作“四年前抗日之役”,由此推算写信的时间似应是1937年了。但从信的内容看,这封信不可能是1937年写的。理由是:(一)信中的“卖国贼首蒋介石”这一用语,不可能出现在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的书信中;(二)信中所说的与高桂滋谈判签订停战抗日协定的事,也不会发生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因为那时国内和平已基本上实现了。我们认为,信中的“四年前抗日之役”是一个不精确的说法,将写信的1936年上溯到长城抗战发生的1933年所跨着的四个年头,说成是“四年前”了。如果说这封信是1935年写的,那“四年前”的说法就根本无从解释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封信是1936年写的。至于月份,则难以确定,我们倾向于是1936年初写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对这封信的时间只署“一九三六年”,放在1936年第一封信的位置。
艾思奇到达延安的时间
毛泽东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的下款没有年月日。有人曾说这封信写于1937年9月。我们考察和分析了这一说法的依据。毛泽东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谈到艾思奇的著作《哲学与生活》,并把自己对这本书的摘录随信附上请艾思奇看一看。毛泽东做的摘录共19页,题为《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署的日期是“一九三七,九月”。上述关于写信日期的说法,很可能是根据这个摘录所署的日期来判定的。
但是,写信的时间不一定就是作摘录的时间。这封信是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写给他的,查清楚艾思奇到延安的时间,对于分析和判断写信的时间是会有帮助的。
关于艾思奇到延安的时间,他1964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说:“1937.9—1938年底到延安抗大任主任教员”。但是,1937年9月24日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中说:“艾思奇已到西安,即来延安。”1937年10月4日《新中华报》关于陕北公学筹备情况的一篇报道中说,陕公聘请的教授“艾思奇、周起应、李初梨等五人已离沪北来”。从这两个材料看来,直到10月4日艾思奇尚未到达延安。为了进一步查清这个问题,我们询问过当年同艾思奇一起到延安的周扬,周扬说他们是1937年10月10日左右到达延安的。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艾思奇到达延安的时间应是1937年10月。那么,艾思奇在《干部履历表》中写的“1937.9—1938年底到延安抗大任主任教员”,又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时隔20多年之后填写的这个履历表,记忆有不准的地方;(二)表中所说的9月,指离开上海动身来延安的时间。
既然艾思奇是1937年10月到达延安的,那么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就不可能是9月的。是不是10月写的,我们难以作出最后的判断。但从信中毛泽东急切地要同艾思奇面谈哲学上的一些问题看来,这封信不像是在艾思奇到延安很久后才写给他的,而像是在艾思奇到后不久写给他的。由于缺少直接的根据,我们没有将这封信的时间写为1937年10月,而是写为“一九三七年”,在目录上将它排在1937年10月10日《致雷经天》与1937年11月27日《致文运昌》这两封信之间,表示这封信的时间不早于1937年10月10日。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应当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慎重的态度。
从林伯渠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判断出毛泽东写信的年份
毛泽东写给林伯渠的一封信,下款署的日期是“一月十九日”,没有年份。有关单位提供手稿复印件时,注明写信年份是1943年。这封信是不是1943年的,我们有些怀疑。信中说:“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生产运动是在1943年才比较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信中说生产节约去年已取得了好成效,这里的“去年”是指1942年吗?信中还说:“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从这里我们想到查明林老的个人计划是哪一年订的,对判定这封信的年份会有帮助。查阅资料后,我们了解到林老的个人计划是指他1944年订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这个计划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1944年新年墙报上刊出,接着又在同年1月2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样,毛泽东写给林伯渠谈到他的个人计划的这封信,不是1943年写的,而应是1944年写的。
“八年抗战”应当怎么理解?
毛泽东写给邓宝珊的一封信,手稿上只署明“十二月二十二日”,没有年份。信中说:“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最初我们认为,既然信中说到对八年抗战作简单总结,那这封信似乎应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写的,而且可能是在1945年写的。但是,信中还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去秋晤叙,又一年了。”这些又指的什么呢?抗战时期我们党同国民党将领和民主人士来往联系的一些具体事宜,有些是经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办理的。于是,我们向当时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的金城了解这封信的有关情况。金城十分肯定地说这封信是1944年的,并对信中提到的一些事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信中的“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是指邓宝珊在蒋介石1943年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采取不支持蒋介石的中立态度;“去秋晤叙”,指1943年11月邓宝珊由西安返回榆林时途经延安同毛泽东等会晤。他还说,这封信是经他交刘绍庭送给邓宝珊的。我们还向当时在邓宝珊处工作的沈求我(曾任民革中央副秘书长)了解这封信的情况,他提供的情况同金城谈的是一致的。毛泽东致邓宝珊信的年代,就这样确定为1944年。信中的“八年抗战”,可以理解为说的是跨着八个年头的抗战。
给符定一的信的年份是怎样确定的?
毛泽东写给符定一的一封信,下款署的日期是“九月三十日”,没有写明年份。毛泽东还有一封给符定一的信(这封信未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但同考证9月30日信的年份有密切关系),从内容看是在接到符定一对9月30日信的复信后写的,这封信的下款署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由此可以推导出前一封信也是1936年写的。但这有两点矛盾:(一)11月28日给符定一信的信封上毛泽东写有“剑英同志转陈”六个字,那就是说这封信是由叶剑英带交符定一的。但在1936年叶剑英根本没有去过北平,怎么能将毛泽东的信带给符定一呢?(二)这两封信的毛泽东手迹,不像他在1936年时写的字,而像他在抗战胜利前后写的字。这样,我们认为这两封信的年份需要考订。9月30日的信说:“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既接光仪”,说明毛泽东同符定一见了面;“德芳返平”,是说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从延安回北平。如果查清楚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那就可以确定这封信的年代了。符定一、符德芳均已去世。我们访问了符定一之子符同天,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的情况。他说:1946年毛泽东邀请符定一访问延安。这一年的夏天,符定一带着女儿德芳乘飞机去延安,同机前往的还有陈瑾昆夫妇。符定一到延安后因水土不服很快回北平,符德芳稍后才回北平。9月30日的信是由德芳带回来的,11月28日的信是由叶剑英转交的,两封信都写于1946年。
我们还查阅了陈瑾昆的档案材料,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六年六月,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央同志。”从这里可以印证出符定一是1946年6月去延安的,符同天提供的情况是准确的。关于陈瑾昆去延安的时间问题,需要补充一点情况。陈瑾昆1946年6月到延安见了毛泽东等后,离开了延安。1946年9月陈瑾昆率全家到达延安,此后一直住在解放区,1949年到达北平。
我们还查考了叶剑英到北平的时间。叶剑英是1946年1月13日由重庆飞抵北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1947年初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式宣告结束,叶剑英离北平回到延安。毛泽东11月28日给符定一的信是由叶剑英转交的,那应是叶剑英在北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转交的。从这里也可以推导出这封信写于1946年。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这两封信都是写于1946年,校正了11月28日信上毛泽东所写的“一九三六年”这一笔误。
判定《致陈瑾昆》写作年份的两点依据
毛泽东写给陈瑾昆的一封信,下款署明“一月十六日”,没有年份。有关单位提供这封信的手稿复印件时,注明写于1946年。根据信封和信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封信不可能是写于1946年的。
首先,毛泽东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的地址是“杨家岭”。陈瑾昆是1946年9月在张家口发表《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的声明后,举家来延安的。因此,1月16日写的这封送到杨家岭的信,不可能是写于1946年的。同时,这封信也不可能是写于1948年的,因为1948年1月延安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这样,这封信应是写于1947年的。
其次,从信的内容分析,这封信也应是写于1947年的。信中说的“目前美蒋所提和谈”,正是发生在1947年1月中旬的事情。据《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六章记载,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国民政府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或是邀请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南京来,以继续谈判,或同意在任何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圆桌会议。”蒋介石并请求司徒雷登同仍在南京的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王炳南接触,以试探共产党方面的态度。1月16日,司徒雷登会见王炳南,转告了国民党政府希图恢复和平谈判的意向。“中国共产党当即予以直截了当的答复,说如果政府同意以前所约定的两项条件(废除宪法与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军事位置),谈判即可在南京恢复;否则即使派代表团到延安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也谈到蒋介石的这一和谈欺骗。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判定这封信写于1947年。
信封上的“51377”编号有误
毛泽东给王首道的一封信,下款署的日期是“十月十一日”,没有年份。这封信的信封上有用编号机打印的“51377”字样,意即1951年的第377号。信的内容是说湖南教育界老人张次仑(张干)、罗元鲲(罗瀚溟)及袁吉六的夫人生活贫苦,请湖南省政府酌予接济。张次仑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校长,罗元鲲、袁吉六均为教员。10月11日,毛泽东还给罗元鲲一信(此信未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信中说:“赐示敬悉”,“先生及张次仑先生……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函王首道主席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1977年5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上交这封信的手迹时填写的“说明卡”上说,“这是毛主席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给罗瀚溟的复信”,“原件由罗的孙女罗宗华提供”。毛泽东写给王首道的信和写给罗元鲲的信应是同一年写的,但上述材料关于写信年份的说法却不一致,需要考订。
我们去湖南访问了罗元鲲的孙女罗宗华。她向我们提供了罗元鲲生前抄写的《第一次致毛主席的信和他的回信(一九五〇年八月—十月)》《第二次致毛主席的信和他的回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廿二日)》《第三次致毛主席的信和他的答复(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月)》三个抄件。罗元鲲的这些抄件只抄写了他给毛泽东的信,没有抄上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但所署的年月日应是分别包含了他写信的时间和毛泽东复信的时间。罗元鲲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信写于1950年8月16日,信中说,他“年届七十”,“个人生活,尤觉彷徨”;袁吉六已去世,“其夫人戴氏……日在饥饿线上挣扎,殊觉可怜,望主席垂意及之”;“当日校长张干先生,老境颓唐,与我略同,并乞垂念是幸”。上面说到的10月11日毛泽东写给罗元鲲的信,从内容看正是对他第一次来信的复信。从月份看也与罗元鲲抄写的“一九五〇年八月—十月”相符合,“八月”是他写信的时间,“十月”是毛泽东复信的时间。这样,10月11日毛泽东给罗元鲲的复信,应是写于1950年。我们还在湖南访问了袁吉六的儿媳,又写信向他的孙子袁大川了解有关的情况。袁大川回信说:“新化县人民政府接省府通知找到我们家的时间是50年冬天,嗣后(51年)我祖母奉召到北京参加了这一年的‘五一节’观礼,故毛主席给罗元鲲的和王首道的信一定在此前的50年,而绝不会在51年的10月11日。我母亲和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是准确的。”
综上所述,10月11日毛泽东给罗元鲲的信写于1950年,湖南省委办公厅“说明卡”关于此信写于1952年的说法有误;毛泽东在同一天(10月11日)写给王首道的信,也应是写于1950年的,这封信的信封上打印的“51377”号码,其中表示年份的“51”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