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虎记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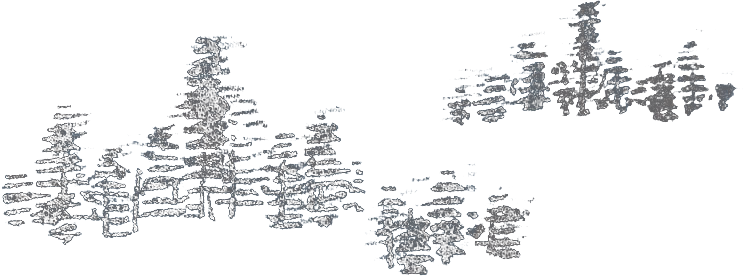
1952年4月底5月初,我带着一个很大的土改工作团在广东云浮县做土地改革工作,正进入一个转变地下串联为大张旗鼓的工作方法的关键时期,忽接叫我即回广州的命令。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在南方日报社(任社长)。我匆匆赶回一问,说是本单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其中“打虎运动”,即反贪污运动,已经打出了一群大、中、小“老虎”,关在“老虎洞”里了,副社长杨奇同志已经被打成“大老虎”。我问是怎么回事,单位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张敏年(广东人,抗日战争初到华北参加根据地抗日工作的)说: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是分局(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同志带着一个工作队来打的,现在关在那里,所以上面要你回来处理。我先去看了一下“老虎洞”,在一间大房间门口看了一下,杨奇等七八位同志在其中。我应该也可以进去看望他们一下,并讲几句请他们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按照事实处理的话。但是我没有,至今我还为此事感到十分可耻。因为我当时如果进去看看他们,是完全不会产生任何麻烦的。因为我没有被怀疑的可能。但是我没有进去,所以我至今感觉很可耻。之后,我就上楼去见打虎队长××同志。他是老前辈兼老熟人了,他说把这群“老虎”交给你了,我立刻就走。我也没有留他,我不能不立刻就接管这个问题,他留下来反不好办。下午与张敏年商议,现在天天还要工作,稳定军心最重要。我们决定晚上9时召开党员大会。我建议请杨奇同志出席。杨来了。会议的唯一议程,是叫我发言、表态。我站起来好几分钟,终于落泪了,我说了大约一分钟。我说“打老虎”的事情,完全决定于是否有可靠证据,今天大家都要我表个态,我就表这个态,余无别事。结果无人发表意见,散会。这个会至多开了十来分钟。
后来,我也未怎么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比这更严重的事,我都体验过,所以我能判断这些全是假的。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吗?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想我自己没有在进城后想要过一分钱,他们与我有同一个目标,走同一条道路,解放后做同样的工作,过同样的个人供给制生活,我没有想到去贪污,他们怎么就会成群结队地去贪污呢?一群冒着贫困、流亡、被捕、死亡的危险而干了几年、十多年的革命,总算保住了生命的中青年们,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贪污分子了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因为,这同说我也是“老虎”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事情。我了解到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也已被打成“大老虎”了。同杨奇一样,均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大黑字体公布了的。罗明是谁?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福建省省委书记,他提出在边界地区宜施行一些相对和缓一点儿的政策,于是,他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罗明是提出相对正确政策的人物,是被极左错误坚持者批判的相对正确一些的上层人物的代表。延安整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罗明是比较正确方面的代表。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后来,为罗明、杨奇两位同志“从轻处理”“宽大处理”开了几千人的大会。那时没有“平反”一说,如果确属无罪时,也是“宽大处理”。这就是说,本来你还是有罪的,来个“宽大处理”就无罪了。
罗明、杨奇同志半正式地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了——不过未用“平反”二字。
如果我回广州说了一句“打虎”的话,我今天就不敢写这个回忆了,因为同事中有相当多的人比我年轻,他们会记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