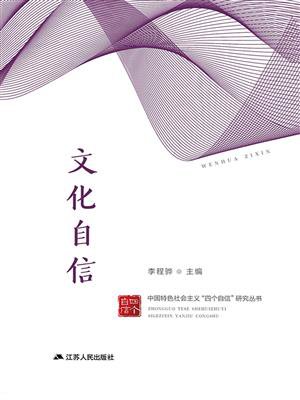第二节
文化自信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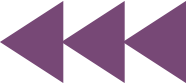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崭新文化观,它的形成与发展,是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从其理论自身来看,也存在着内在的发展逻辑,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成熟完善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承袭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对当时德国封建统治危机和即将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反映。《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文化观开始松动,“物质利益的支配作用使马克思同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黑格尔的理性决定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促使和推动马克思将其视阈由政治、法的观念转向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从而逐渐转向对文化问题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唯物主义文化观进行了初步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早期形态,即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逐步由理性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立场。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和成熟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即从人的劳动实践本质的视阈,阐发了文化的本质及其发生过程,以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否定了以往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抽象人性论,把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即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产生关系的存在来进行考察,颠覆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使马克思对文化的阐释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工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以往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划清了界限,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自我意识的理性决定论和强调抽象人性的人本主义,其二是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首先,现实的、社会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前提。其次,马克思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上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诠释原则,强调精神文化对社会生活存在依赖关系,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当阶级社会出现后就出现了阶级的意识,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再次,精神文化最初是与人类的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其与物质生活的分离,是随着社会分工尤其是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而发生的,“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形态发展的分析主要在于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考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分别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总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关系又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两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一定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社会组成各阶层的变化,从而带来社会形态的变化及意识形态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宣言》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原则,进一步重申唯物主义文化观的一般原理。《宣言》批判了超阶级的观点和永恒真理的说教,具体考察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当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时,所有制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从而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社会有机体理论,论述了文化以及社会各组成要素相互影响和辩证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出发,论述了社会有机体中人的生产及交往活动、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的相互关系,论述了三大生产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为避免形形色色的“经济决定论”即把人类的物质生产看作社会发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的倾向,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阐发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历史发展合力论等思想,继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恩格斯强调了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仅是实践的主体,同时还具有意识能动性,人的思想意识既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又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因素相关,政治、哲学、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经济的因素不能自动发挥其决定作用,要借助文化和政治等意识形态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基于此,恩格斯晚年把加强理论斗争和道德宣传教育以达到文化自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和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文化观上的重要变革,其基本内容首先在于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在阶级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与社会其他构成要素的相互影响关系等方面,强调了先进的文化或者体现先进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其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从‘人类生存的前提’即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来阐发自己的文化观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贯彻了文化观上的唯物主义原则,将文化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看成是一定社会阶段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产物。二是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将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看作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人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确证了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活动相比,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等特征。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发生、发展、成熟、完善几大历史阶段,是在“扬弃”旧有的唯心主义文化观以及对自身理论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实现的。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它也必然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五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出整体观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生产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结构及物质生产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愈来愈得到凸显。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上观察,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产又和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精神文化生产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武器的批判”即先进的无产阶级,也要重视“批判的武器”即先进理论的指导。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批判的武器”即先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将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建构的文化自信理论,在贯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党的建设文化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文化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的理论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和完善的逻辑过程。早在浙江任职之时,习近平就意识到了人的本质中的文化向度,也意识到了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文化这一社会功能的体现,主要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推出优秀的文化作品,这一时期可视为文化自信理论的酝酿时期。在担任总书记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更加重视文化的社会功能,并且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系统提出“文化自信”。在其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不断完善着文化自信理论,始终强调文化发展的民族本位,始终强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格局,始终强调文化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功能,始终强调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向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自信有了更加全面和完善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一定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继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一)提出“文化的人”概念
习近平在《文化育和谐》中提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主要指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在物质生产及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了人的需要等其他理解人的向度。而习近平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人的文化向度,人虽然是以从事物质生产为最主要的任务,但物质生产包括社会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指向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不能一味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要时刻不忘人的幸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
(二)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上升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非常重视文化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很早就认识到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习近平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在承认经济对文化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渗透性的力量和因素,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重视,正是基于当今世界的历史图景发生的变化,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对此,任平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中指出,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历史图景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两条就是“文化因素成为渗透一切的主导因素”,“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时代的主导地位的产业,从而使历史观以往的整个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的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从物质的生产与人类的生活方式来看,已经从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结构的普遍化,使消费对于物质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三)强调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首先体现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持文化的民族本位。民族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提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来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重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比如传统的“和合”文化。“‘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在习近平看来,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既追求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也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这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理想,也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所在。民族性的第二个表现是要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邓小平早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批判性地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但“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习近平秉持并重申了文化的民族本位立场,在倡导虚心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强调“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气魄,才是中华文化体现时代性和“走出去”的根本保证。
(四)重视文化产业对文化功能的发挥
在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实现路径上,习近平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调文化产品的重要性。习近平在《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中指出:“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这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所在。”只有生产优秀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才能将优秀的文化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中,习近平肯定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做法,并强调“‘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文化经济”的概念,不仅要求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互相促进,更加强调发展的目的在于人这一根本宗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同时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具体方略,为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