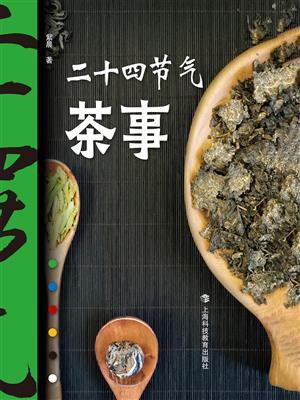序

我从事茶学工作已经整整70 年了,从解放时一个茶店的小学徒做起,到与上海茶叶学会会员一起宣传、推广茶文化,为中国茶学倾注了一生心血。这70年中,我看着中国现代茶学从开创到兴盛,心中尤为欢喜。年轻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我们的茶事业能够得到复旦大学的几位茶学大师的支持照顾。中国第一个茶学系1927年在复旦大学筹建,1940年复旦大学茶学系正式成立,首任系主任“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一直是我们业界的中流砥柱。遗传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创始人谈家桢院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又帮助我们成立了“上海茶叶学会”,让上海的茶界在科学指导下蓬勃发展。特别还要提起,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对我们上海茶叶学会的谆谆关心,号召“弘扬茶文化得从娃娃抓起”。我有幸亲历这一段历史,感觉无比欣慰。可以说,中国茶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这些老前辈的保驾护航。
这几十年中,中国茶学研究的成绩也是令人瞩目的。各大类茶种内含物质的分析、医疗效果的检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6000多年前神农时代流传至今的茶,真正进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但是,现在主流观点对茶的认知也让我特别困惑。一位著名的茶学研究专家在讲座中经常提到各种茶维护健康的显著效果,而最后的结论却是“茶不是药”。茶能够治病,怎么就不是药呢?神农发现茶的时候,就是把它作为药使用的。茶是第一味中药,至今还在药典里面,中药怎么就不算药呢?看来,国人对茶的认知,还存在很多混乱,还需要有专业的研究来拨乱反正。
其实,老前辈们也是一直在期待这样的变革,期待这一个时机。吴觉农先生说,要有这样一个人,他“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博爱,哲学家的修养,艺术家的手法,革命家的勇敢,以及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分析能力”(吴觉农1941年同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学生谈话)。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要培养这样的茶学家变成非常艰难的任务了。8年前,学会的江虹蔚接手了朱家角的江南第一茶楼,挂出了复旦大学李辉教授制作的“六脉茶气”图,让我眼前一亮!六大类茶与人体的六根正脉对应,这是全新的认知!相应的保健功效也与科学研究及我们的实践经验吻合,而其中承载的浓浓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让我不禁想起吴先生的话:“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博爱,哲学家的修养……”
后来,我在谈家桢先生的各种纪念活动中与李辉教授相遇,从谈向东处得知李教授原来从本科时期开始就是谈先生耳提面命的弟子。因为他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做科研,所以谈先生特别关注他,经常唤他到家里品茶谈心。谈先生忧国忧民,认为茶学研究的目的是让大众“科学饮茶,艺术品茗,以茶养生,健康长寿”,但是目前的研究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对茶的认识存在很多谬误。比如,很多人说“黄茶、白茶微发酵,青茶半发酵,红茶全发酵”,但是,如果只是发酵程度有差异、内含物比例有不同,怎么各类茶的气味和功效有这么大的不同?理论上,应该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工艺生成了完全不同的产物,而不是因为相同反应的程度不同。这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研究了。一老一少的思想碰撞,给李辉留下了一个使命。他在研究生期间师从金力教授做人类进化学研究,在耶鲁大学又继续从事人类医学遗传学的研究。谈先生仙逝以后,他毅然从耶鲁大学回到了复旦大学。我问他,在国外发展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呢?他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没有好茶啊!”在我听来,这恐怕不是开玩笑。
年前,江虹蔚转交给我两本李辉教授的书稿——即将出版的《茶道经》和计划出版并邀我写序的《二十四节气茶事》。拿到书稿,我戴上厚厚的老花镜,秉烛夜读,欲罢不能,原来谈先生的猜想被证实了。一气读完,我想说两句话:“要是谈家桢先生看到,肯定高兴坏了!”“要是吴觉农先生看到,也肯定高兴坏了!”
彻底推翻传统认知,这是革命家的勇敢;节气转变与六大茶类的阴阳规律,这是哲学家的修养;茶叶与人体的理化分析,这是科学家的头脑;主动投身云贵的扶贫攻坚,又心系大众的苦病,这是宗教家的博爱。更没想到的是,李辉教授还是位优秀的诗人,整本《二十四节气茶事》都是以诗话的形式呈现的,既有格律诗词,又有现代诗,读来回味悠长,这不又是艺术家的手法么!这个人终于等到了!
今年清明,趁我还走得动,我要和李辉教授一起去西湖边,品一杯龙井,走进春天的明媚里,走进李教授的《二十四节气茶事》里。
刘启贵
己亥初春记于江南第一茶楼
紫晨注:刘启贵先生为中国茶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本文写作后不久,2019 年 10 月 9 日,刘老先生忽然离世。本序是刘老最后的遗作,谨此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