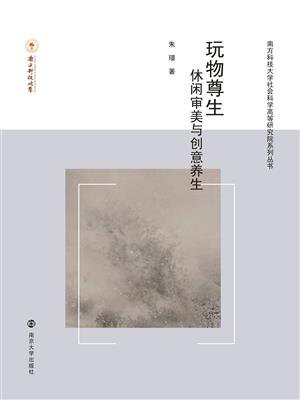第一节
养生知止
对于养生与“止”的关系,最直接的是“止”代表着繁忙工作的停止或劳碌生活的休止,人们获得时间的自由与空间的独立,从而可以放松身心,养生活动借此进行。而停止劳碌就是休闲,在这样的状态中养生,也是大众对“休闲养生”的普遍理解。
但我们说养生要知止的这个“止”,绝非仅指这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肤浅理解,而是与休闲之“止”的深层内涵密切相连。
以审美体验的角度来看,“从根本上说,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一方面,“自在生命”表达着生命在世的此在圆满,是休闲的存在状态。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寻得人生的安顿与终极关怀。“休闲美学着眼于人的当下存在,关注人的自在生命之本然状态,既不会用虚幻的彼岸来否定人的此在之身,也不会以理性式样去束缚活泼的生命性情。”
。一方面,“自在生命”表达着生命在世的此在圆满,是休闲的存在状态。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寻得人生的安顿与终极关怀。“休闲美学着眼于人的当下存在,关注人的自在生命之本然状态,既不会用虚幻的彼岸来否定人的此在之身,也不会以理性式样去束缚活泼的生命性情。”
 休闲美学的审美对象是眼前这个生动真实的鲜活世界。另一方面,“自由”“自得”传达着人们对休闲境界的理想体验。自由是无染纤毫、没有任何牵绊,自得是无入而不自得的浑然自适。如果抛去这类比较主观化的描述,而以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去更具体地描述这一理想状态,那么可以用“恰如其分”这一词汇。因为上面所述的“自由”“自得”,不就是俗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恰如其分之体验吗?所以,自由的审美体验与自得的理想状态,源于生命个体对内、外世界“恰如其分”的把握。
休闲美学的审美对象是眼前这个生动真实的鲜活世界。另一方面,“自由”“自得”传达着人们对休闲境界的理想体验。自由是无染纤毫、没有任何牵绊,自得是无入而不自得的浑然自适。如果抛去这类比较主观化的描述,而以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去更具体地描述这一理想状态,那么可以用“恰如其分”这一词汇。因为上面所述的“自由”“自得”,不就是俗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恰如其分之体验吗?所以,自由的审美体验与自得的理想状态,源于生命个体对内、外世界“恰如其分”的把握。
简言之,对生活于当下世界的个体自身而言,“休闲”的美感体验,在本原上就是一种“自如”“恰好”的生命状态:一种得其所哉的自我认同,一种恰如其分的处世体验。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生命状态,自然是“闲”的,是无为的、无扰的、无复多虑的。我们把这种状态,作为休闲的本然、应然状态;如果用一个哲学话语来对此加以把握,那就是深蕴中华审美精神的“止”范畴。
“止”的“各得其分”“恰如其分”之义,最早见于朱熹,近来被潘立勇先生引申到休闲美学的研究中来。《周易》“贲卦”的彖辞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文明以止”的“止”字所阐明的,是“化成天下”的“人文”根本。朱熹解“止”字义为“各得其分”
 ,也即是“恰到好处或恰如其分”
,也即是“恰到好处或恰如其分”
 ,而这也正是休闲美学之本体:自在生命之所以得以自由体验,乃是生命个体能对世界进行恰如其分之把握;又因本体与现象界是不二的存在,所以这一体认与把握所要通达的本体,不是泯灭自我的抽象理念或彼岸神祇,更不是睥睨外物的妄自尊大,而是使得世界与我之间回复到“止”的本然应然之关系状态,恰到好处、各得其分。
,而这也正是休闲美学之本体:自在生命之所以得以自由体验,乃是生命个体能对世界进行恰如其分之把握;又因本体与现象界是不二的存在,所以这一体认与把握所要通达的本体,不是泯灭自我的抽象理念或彼岸神祇,更不是睥睨外物的妄自尊大,而是使得世界与我之间回复到“止”的本然应然之关系状态,恰到好处、各得其分。
“止”字在《大学》开篇之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释曰:“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是而不迁之意”“当止之地”“至善之所在”,皆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休闲本体。
“是而不迁之意”“当止之地”“至善之所在”,皆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休闲本体。
只有回到恰如其分的休闲之本,养生活动才可能得以进行,因为养生所追求的,也正是身心的自在、自由、自得,这是养生的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内核,则养生的延年益寿之期难以实现——饶是实现也无甚意义。我们讲养生是一种休闲,其根本也就是因为养生是要以身心来体知这个蕴含休闲奥义的“止”。
而且,“知止”不仅是养生的根本,也是中华文化中修养功夫的基础。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作为修“大学之道”的“七证”(七个修证层次),并且认为,“这不但是曾子特别提出孔门心法求证实验的修养功夫,同时也代表周、秦以前儒道不分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化学养的特色”。饶是在秦、汉以后,这七证也“被道家修炼神仙之道所引用”。且在东汉后,“佛学传入中国,讲究修习小乘禅定的罗汉果位和修证大乘道菩萨地位的止观方法,也借用了‘止、定、静、虑’的说法”。所以这一修证体系,实是中华文化的“擎天一柱,屹立万古而不可毁”。
 在这一体系中,“止”无疑是根本所在,可以说它涵有内明(内圣)外用(外王)的两重作用,是修“内圣”与“外王”之学的“恰如其分”之根据。
在这一体系中,“止”无疑是根本所在,可以说它涵有内明(内圣)外用(外王)的两重作用,是修“内圣”与“外王”之学的“恰如其分”之根据。
 龚鹏程先生虽然指出南怀瑾于三教之分际的掌握或不精准,但也认同其眼力,亦云“我国一切修证法门,确实可说全赅于此数语中”。
龚鹏程先生虽然指出南怀瑾于三教之分际的掌握或不精准,但也认同其眼力,亦云“我国一切修证法门,确实可说全赅于此数语中”。
 以此,“止”义可谓是中华三教教法之所本。并且,龚鹏程认为不是“七证”而只有“六证”,即首证当为“知止”,这里的“止”,就是“大人之学”的“依止、归向与目标”
以此,“止”义可谓是中华三教教法之所本。并且,龚鹏程认为不是“七证”而只有“六证”,即首证当为“知止”,这里的“止”,就是“大人之学”的“依止、归向与目标”
 。如此,就更凸显了“止”的本体地位。
。如此,就更凸显了“止”的本体地位。
所以,无论是从休闲养生的本身内涵来分析,还是从中华修养工夫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知止,都是养生者应该首先明确的一个命题。但是,如果只说养生知止即是养生者要恰如其分地把握内在自己、自己与外界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啻在说一句空洞无物的废话。因为“恰如其分”本身,就体现着本真的又至善至美的休闲审美状态。并且,若以历史的、生成的视角观之,“止”也具有流动的、随境遇而化生的内涵。因之,我们需要进入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以探讨本体之“止”的具体意涵;并进一步地阐明,恰如其分之止是怎样在事物中体现以及如何才能对其加以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