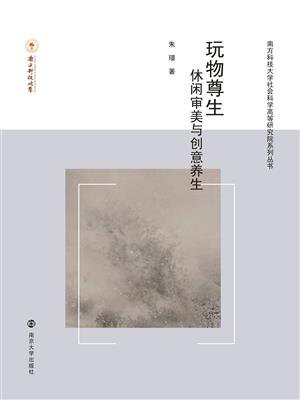引言
明万历十九年(1591),钱塘(今杭州)儒生高濂即将实现晚年的心愿,把编撰完成的养生巨著《遵生八笺》自刻出版。他请当时的名士屠隆为其作序。就像其他常见的序言一样,屠隆在对高濂其人与全书内容进行介绍的同时,不吝溢美之词。不过他随后话锋一转,以他人的视角,称既然“大道以虚无为宗,有身以染着为累”,那么反过来看高濂在书中所述游具品物、宝玩古器、书画香草花木之类,名目繁多,描述琐碎,“颇极烦冗”,有“驰扰神思”“障阂身心”之患,于是质疑这怎么还能称之为“遵生”呢?
当然,这看似诘难的问题,也只是屠氏在道出自身体悟之前,所卖的一个关子。紧接着他给出了对这个质疑的回答:
人心之体,本来虚空,奈何物态纷拏,汩没已久,一旦欲扫而空之,无所栖泊,及至驰骤漂荡而不知止。一切药物补元,器玩娱志,心有所寄,庶不外驰,亦清净之本也。及至豁然县解,跃然超脱,生平寄寓之物,并划一空,名为舍筏,名为甩手,嗟乎,此惟知道者可与语此耳。
大道是以虚无为本,人的心体也以虚静为尚,但人自从出生以来,何日何时不与物相刃相靡!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物事纷扰人心既久,如果顿然抽空这所有物事,那么七情六欲、贪嗔痴怨的人,必将陷入茫然空虚之地了。既然如此,不如以药物服食来补其身形,以器玩物品来怡其心志。这些活动,相比于时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谈”(袁宏道语),以及“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张岱语)等穷奢极欲的追求,无疑是能使人归于“清净之本”的更佳选择。
由此可知,“遵生”或曰文人式的养生所涵盖的诸般物事,其意义即在于消除俗物俗务被抽空之后,身心“无所栖泊”的困境。在这里,此一说辞也可能仅仅是屠隆等人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物质生活所寻得的借口;却也难以否认,这一思路所透显的,正是文人养生与佛、道养生的不同之处。文人养生认为心志必须有所寄托以免流于虚泛,而佛、道养生更强调要保持空明、虚静的心灵状态;文人养生以任情旷达的活动、极尽雅致的物品来陶冶心性,而佛、道养生更警惕物欲、情欲对修行的妨碍,其所寄托者则是对信仰的奉献以及对来世或彼岸的向往。饶是同样以虚静的方式养性,文人养生的根据与归宿都仍是现世的身体,而教徒们的心灵之力,却导向神秘的宗教理想。当然,这样的比较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尤其是明代的文人养生,已经是融汇三家的现世践履;不过其主导精神,仍是富有儒家特色的入世的、注重与人情物事相接的现实态度。因此,各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逸游活动、与生命灵气相应感的清赏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充满才华的文人雅士所创造、发现与描摹,以此作为人生一世的身心栖泊。
于是,以高濂所勾勒的养生世界为代表,中国古代的文人养生文化既呈现出多样化的实现方式,又流溢着个性化的创意色彩。在这样的创意养生中,身体栖泊于万物,万物是为“宝筏”,身与物在细腻、深刻的感知体验中互相印证,所谓“舍筏”,是以自在之身体悟到恰如其分的存在根本,所以无假于物而生自由自得之境;在这样的创意养生中,生命又栖泊于身体,形神相合的身体是为“宝筏”,在形与神的对位、和声中趋向生生道本,所谓“舍筏”,是身体消解的终极解脱,还是身体尸解的化入圣境?“惟知道者”可以答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