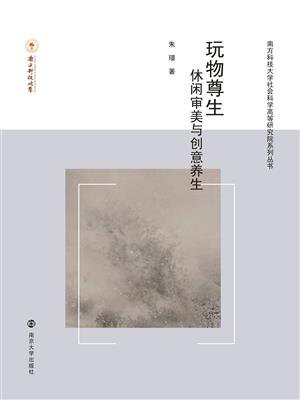第三节
创意养生的体系
本书对创意养生的内容体系的搭建,也以《遵生八笺》的成书框架为模型。如果说,高濂的这个创举以及《遵生八笺》之所以能成为创意养生的主要体现,只是因为此书收集的资料极多从而以量取胜,那么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以其为例而展开说明创意养生的文化形态与休闲审美内涵。事实上,《遵生八笺》实有着体系的自觉,实蕴含着宛然自足的休闲审美的理论体系。《遵生八笺》以“古所未有”的独特体例,传达了一位晚明文人的尊生思想与生活态度,勾勒出一个使身心得以沉浸其中的休闲审美世界;并在汇总前代相类著作的基础上,俨然建构出一个以身体为基石的、宛然自足的思想体系。其内容与体系,无不是为了身心在世之闲、身心体验之美而设,以富含创意色彩的文人情趣与雅致,达到尊养生命的宗旨。
一、文人立场的养生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以《遵生八笺》为典范讨论创意养生,有必要明确养生者的文人立场。因为佛、道的养生传统,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与宗旨,人性化与个性化的主张与实践方式极少,这也就极大地减弱了其养生的创意色彩。而文人养生以此世身心的颐养为根本,体现出个人化的感性诉求,并且所动用的“俗世”器具,多有优雅的韵味、审美的意涵,最能代表创意养生的休闲审美精神与文化样态。
晚明养生文化大盛,养生类的书籍数量有暴增的现象,这些养生著作有许多即为文人所撰写。这是因为,与前代养生文化的引领者和传播者基本局限于方士(包括医家、房中家)道徒不同,晚明养生群体呈现出鲜明的文人化特点。晚明养生文本的作者中,可见许多著名文士、学者、藏书家甚至官员的名字,如罗洪先、袁黄、李贽、陈继儒、周履靖、胡文焕等。日本学者坂出祥伸就曾指出,明代的养生书至少呈现两个特色:一是养生阶层的扩大,不再限于医家与道士;二是养生范畴的延伸,与所谓的“文人趣味”密切相关。以朱权、周履靖与高濂等人的作品为例,他指出明代的养生有不少文人参与,且当时养生范畴开始扩及居处、日常器用、书画古物、花竹鉴赏等活动。

中国文化中素有“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传统认识,且养生思想又常与二氏相关,所以,在三家相融的背景下,观察晚明士人对其养生立场之辩护,则更可见其文人养生之本色。
晚明文人王文禄就曾言:“今以养德属儒,曰正道,养生属仙,曰异端,误矣,身亡而德安在哉!故孔子慎疾,曰父母惟疾之忧,教人存仁致中和。孟子曰养气,持志集义,勿忘勿助。是故立教以医世,酌人情而制方。……故曰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
 因此儒士养生,并无不可。这样的思想在《遵生八笺》中多有表述。
因此儒士养生,并无不可。这样的思想在《遵生八笺》中多有表述。
《遵生八笺》的两篇叙文,分别落款为“弢光居士”与“贞阳道人”,这也反映了其杂含释道的思想内蕴。但在其自叙开篇,高濂即言:
自天地有生之始,以至我生,其机灵自我而不灭。吾人演生生之机,俾继我后,亦灵自我而长存。是运天地不息之神灵,造化无疆之窍,二人生我之功,吾人自任之重,义亦大矣。故尊生者,尊天地父母生我自古,后世继我自今,匪徒自尊,直尊此道耳。不知生所当尊,是轻生矣。轻生者,是天地父母罪人乎!

直言父母大义,这种角度自然不可能是道释角度,而是儒家的孝道。
虽然《四库全书》云《清修妙论笺》“其宗旨多出于二氏”,但在此笺中,仍时时可见高濂的儒生文人之立场。在本笺开头的“高子曰”中,高濂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摄生尚玄,非崇异也。三教法门,总是教人修身、正心、立身、行己、无所欠缺。为圣为贤,成仙成佛,皆由一念做去。……指神仙之术为虚诬,视禅林之说为怪诞也。六欲七情,哀乐销烁,日就形枯发槁,疾痛病苦,始索草根树皮,以活精神命脉。悲哉,愚亦甚矣!保养之道,可以长年,载之简编,历历可指,即《易》有《颐卦》,《书》有《无逸》,黄帝有《内经》,《论语》有《乡党》,君子心悟躬行,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岂皆外道荒唐说也?

此乃高子为自己的养生之论正儒家之名,说明儒释道的在“养生”“尊身”“保身”方面实有着一致之看法。该笺中又有儒家养生之说:
陈茂卿《夙兴夜寐箴》为吾人一日修行矩度,当熟读之。《箴》曰:“……乃启方策,对越圣贤,夫子在坐,颜曾后先。圣师所言,亲切敬听,弟子问辩,反复参订。……读书之余,间以游咏,发舒精神,休养情性。日暮人倦,昏气易乘,斋庄恭敬,振拔精明。夜久斯寝,齐手敛足,不作思惟,心神归宿。养以夜气,贞则复元。念兹在兹,日夕干干。”

圣贤犹且如此,何况后生学者。高濂引龙舒居士之言,对杀生、偷盗、邪淫之戒,阐释为“儒释未尝不同也,其不同者,惟儒止于世间法,释氏又有出世间法,此其不同耳”
 。又引论曰:“欲脱轮回,立德为本;凡修况业,济物为先。忠君孝亲,固臣子之大节;恭兄友弟,实长幼之当然。夫妇别,朋友信,人伦乃正;道德亲,善良近,学行斯全。”
。又引论曰:“欲脱轮回,立德为本;凡修况业,济物为先。忠君孝亲,固臣子之大节;恭兄友弟,实长幼之当然。夫妇别,朋友信,人伦乃正;道德亲,善良近,学行斯全。”
 “脱轮回”虽为佛教用语,但现实践履却落在了“立德”“忠君孝亲”“恭兄友弟”“正人伦”等儒家要义上。
“脱轮回”虽为佛教用语,但现实践履却落在了“立德”“忠君孝亲”“恭兄友弟”“正人伦”等儒家要义上。
此外,在李时英为《遵生八笺》所作序言中,亦指出高濂编《尘外遐举笺》的宗旨,是“树箕颍之风声,以昭儒家功令”
 ,即点明了其儒家文士之立场。高濂既然请其作序,自然也是因为两人的相互了解;且此语句亦随书刊行,所以高濂对此无疑是认同的。
,即点明了其儒家文士之立场。高濂既然请其作序,自然也是因为两人的相互了解;且此语句亦随书刊行,所以高濂对此无疑是认同的。
故而,从根本立场上说,《遵生八笺》是儒士文人的养生之作。高濂曾引用“释如白璧,道如黄金,儒如五谷”
 之论,而他的态度,也正如当年说出此论的儒生一般,认为“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
之论,而他的态度,也正如当年说出此论的儒生一般,认为“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
 !尽管高濂的养生之论“融会道释精神,却不脱儒生的本分。他沿用道教的按摩、叩齿、漱津等修炼法,对于念佛、持咒、焚香诵经也不排斥,究其精神,仍是以儒家的修养伦理为核心”,实际上,这也正是晚明养生文化中,把道佛“世俗化”“文人化”的取向与特点。
!尽管高濂的养生之论“融会道释精神,却不脱儒生的本分。他沿用道教的按摩、叩齿、漱津等修炼法,对于念佛、持咒、焚香诵经也不排斥,究其精神,仍是以儒家的修养伦理为核心”,实际上,这也正是晚明养生文化中,把道佛“世俗化”“文人化”的取向与特点。

最后,结合前文简述的高濂生平,可知在时代风潮之外,高濂本身的文人身份与人生际遇,也奠定了此书的思想底色。高濂的父亲对爱子着意栽培,实是希望他能仕途顺利,复兴家族声望。但高濂屡次科举失利,颇受打击。最后因为汲汲于仕,在父亲离世时也未在身旁,殊为遗憾。晚年时的高濂,虽然对功名再无进取之心,甚至有厌弃之意,但长期的儒家教育以及先父的厚重期望,还是让他以儒家的、文人的立场看待世界。因之,在他晚年这部颇具道家色彩的遵生巨著的笺面上,除“瑞南道人”之号外,高濂还多处钤上“宋宣仁高太后父北作坊副使封武功郡王遵甫公十五世孙”“武功郡王孙”两方藏书印,以彰先祖功名,这反映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他内心中的交织。儒家思想可以说更多的是时代与父亲加在他身上的烙印,对道家的喜爱则更多的是他个人对生命体认的结果。但他绝不是真正的道士或彻底的道家拥趸,儒家学说与思想倾向在他身上是抹之不去的血脉留存。就像他在说尊生之义时,也不忘引儒家经典与要义,以论证自己养生主张的合法性。与其说这种合法性是向外界的宣称,倒不如说这是他为自己的内心反思所做的交代。
二、以身为本的架构
由前文的讨论,可知以性质言,《遵生八笺》是文人立场的遵生之作,表现为其所呈现的休闲审美的身心世界;以汇编集成之内容体系言,《遵生八笺》是以尊生为核心的养生巨著,八笺皆围绕尊生主题而设。所以,在《遵生八笺》自身性质、内容与形式的契合中,八笺所尊之“生”与休闲审美所依之“身心”达成了融合。此处,即关联到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一直隐而未发、却无时而不紧扣的基本范畴:身体。
身体是人之“生”的现世依托,尊生当以身体为根据与基石。在中国身体观中,身体又是身心一合之存在。所以,尊生即是身心怡养。在高濂的论述系统中,直接略去了对“身体”概念的直接阐发,一同略去的,还有以中国传统身体观为思考出发点而推衍此书的思想进路之表述。高濂之所以略去,是因为由前代养生文化所积累、由同时代人所普遍理解接受的身体观,正是他编撰《遵生八笺》的默认前提。对于他与他的期望读者来说,此为不言而喻、不辩自明之论。但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要探讨本书的思想体系,则必须阐明其中起根本作用的身体观,因为在当下全球化的思考语境中,“身体”实已成为思想纠缠的渊薮与观点碰撞的路口,故而不可不辩,不能不先明确这一基石与前提。并且,一旦以此为基点进行考查,则可发现《遵生八笺》旁通三家、间杂医药日用而又自成一体的精妙所在、枢纽所在;通过这样的考查,也更可明了创意养生的身体基础。
要探明本书是如何以身体为基石与主线来加以次第组织的,则首先要明确其八笺篇目是否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即以尊生为核心的八笺内容,是平行并列地平铺陈述,还是以一定的思想进路来组织,从而相互应合地构成一个有机体系。
以内容性质言,《遵生八笺》全书大概可分为三个不同部分,且三部分之间存在着养生主题的一以贯之,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其中,抄录修身省心格言的首笺“清修妙论笺”为第一部分,体现了该书的尊生宗旨与纲要;辑录历代尊生高人的末笺“尘外遐举笺”为第二部分,代表了该书所期望达到的理想人生境界;中间六笺,则是记述尊生工夫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实践途径。“燕闲清赏笺”的艺术品鉴诸事,主要是对人心神的调适;而心神调摄的重要性,在“清修妙论笺”中多有体现。如其载曰:“心静可以固元气,万病不生,百岁可活。”
 “服药求汗,或有勿获,愧情一焦,涣然流离,是皆情发于中,而形于外也。……故心不挠者神不疲,神不疲则气不乱,气不乱则身泰寿延矣。”
“服药求汗,或有勿获,愧情一焦,涣然流离,是皆情发于中,而形于外也。……故心不挠者神不疲,神不疲则气不乱,气不乱则身泰寿延矣。”
 “人神好清而心扰之,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
“人神好清而心扰之,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
 这也是《遵生八笺》的“创意”内容相契于“养生”之旨的明确体现。
这也是《遵生八笺》的“创意”内容相契于“养生”之旨的明确体现。
但是,只把全书内容大概分为三个不同部分的做法,还是止于浅层意义,对这三部分进一步深入探讨仍然阙如。这也导致对整书的研究还是停留在资料层面的整理与浅层意涵的阐释,使得各部分之间,特别是审美与尊生两大命题之间,总还存在着捅不破的“窗户纸”;而这也事关“创意”与“养生”两个命题的打通问题。
诚如黄妙慈所言,“仔细探讨,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在人格涵养、日常作息、居室安排、甚至艺花莳草、古董书画清赏等层面,皆与‘遵生’理念关系密切,遵生与审美并非两个并立的概念,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中种种美感欣求的取向,其实隐含了‘遵生’的价值判断在内”
 。在黄氏之前,毛文芳也曾撰有《尊生与审美——晚明美学之两大课题》
。在黄氏之前,毛文芳也曾撰有《尊生与审美——晚明美学之两大课题》
 ,将“尊生与审美看似无关的课题牵连起来”,认为“一个极具审美意趣的起居生活,是文人为养护生命而细心营造出来的。站在尊生与审美的立场上,同样要创造一个身心居处的安乐环境,二者其实是合一的,这是晚明闲赏美学的独特性”
,将“尊生与审美看似无关的课题牵连起来”,认为“一个极具审美意趣的起居生活,是文人为养护生命而细心营造出来的。站在尊生与审美的立场上,同样要创造一个身心居处的安乐环境,二者其实是合一的,这是晚明闲赏美学的独特性”
 。但是,二者是如何在本底层面相融合的,毛氏并没有系统地回答,这也使她所论述的合一更多地集中于内容的“纳入”层面,如仅拈出《起居安乐笺》与《燕闲清赏笺》,认为它们“代表着高濂在尊养生命的理论体系中,正式将审美生活纳入”。
。但是,二者是如何在本底层面相融合的,毛氏并没有系统地回答,这也使她所论述的合一更多地集中于内容的“纳入”层面,如仅拈出《起居安乐笺》与《燕闲清赏笺》,认为它们“代表着高濂在尊养生命的理论体系中,正式将审美生活纳入”。

因此,在《遵生八笺》中,“遵生”与“审美”两个概念并非平行,而是合一的。但这两者究竟是如何相互包含的,其融合的根据何在?如何在现实践履中体现?如何在理想境层中呈现?这都是有待贯通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打通这一问题,则又要回到对《遵生八笺》全书体系特别是其三个部分的深入解读,以明确包罗遵生与审美的各部分之间并非单纯内容之整合,更重要的是内在肌理之连通。笔者认为:身体,这一生命存在的基石,为“尊生”与“审美”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思考的肇始点;更进一步地,以身体性的践履体认为特色的中国哲学“本体—工夫—境界”之范式,则为这一思考的充分展开提供了思想的“脚手架”。
本体真如与现实体验相生不离,并渗透于身心践履的现实工夫中,呈现于在世身心对生命境界的感知与体会中,这是中国哲学话语与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本体意识固然存在于中华文明之源,“本体”一词也是中国哲学古已有之的核心概念。由先秦的生发初思到王弼的玄学本体论,再到宋理学对本体自觉追求的理本论,直至王阳明的“心之本体”:“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态之义,也是应然状态之义;按其思辨的逻辑,本然即应然,应然即本然,心之本体既指心的本来状态,亦指心的应然状态;本然为逻辑本体,应然为理想境界,在王阳明那里本体即境界,境界即本体,两者合而为一。”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要通达的,也就是澄明辉照这个本体,“以自己真实的生命去体认、透悟和证会它,这便是中国心性哲学尤其是心学本体工夫论的核心问题”。于是,本体与工夫又契而合一,“本体为工夫之依据,亦必经由工夫而现实地呈现”
“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态之义,也是应然状态之义;按其思辨的逻辑,本然即应然,应然即本然,心之本体既指心的本来状态,亦指心的应然状态;本然为逻辑本体,应然为理想境界,在王阳明那里本体即境界,境界即本体,两者合而为一。”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要通达的,也就是澄明辉照这个本体,“以自己真实的生命去体认、透悟和证会它,这便是中国心性哲学尤其是心学本体工夫论的核心问题”。于是,本体与工夫又契而合一,“本体为工夫之依据,亦必经由工夫而现实地呈现”
 ,亦即境界地呈现。
,亦即境界地呈现。
“本体—工夫—境界”这一体现中国哲理智慧的理论模式,由后来的新儒家进一步地系统化。与西语传统本体论及语言体系的抽象逻辑性、纯粹客观理性截然不同,“本体—工夫—境界”的理论话语体系有在世性、体验性的鲜明特征。在世性,即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相生不二;体验性,即人以自身生命去体认本体与现象相合无间的世界,在个人的身心体验中确证此世。体认自践履中来,强调知行合一。
以“本体—工夫—境界”话语的在世“体验”与身心“体会”之特点而言,则毋宁说它是身体性的,因为正如杜维明所说:“‘知道’是一种认知,‘会’是一种体验。”
 而“中国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体验之学’,中国思想家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抟成其宇宙论、人生观、社会政治论,莫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以这一中国思想文化系统,正是具备着“身体之基础”。
而“中国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体验之学’,中国思想家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抟成其宇宙论、人生观、社会政治论,莫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以这一中国思想文化系统,正是具备着“身体之基础”。
 因此,我们以“本体—工夫—境界”这一中国哲学思想的范式来研究《遵生八笺》,不止是因为二者同样地化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且有着形式、体例方面的吻合;更是在“身体”这个基础与核心上,我们认为“本体—工夫—境界”的话语体系天然契合于养生思想的研究。
因此,我们以“本体—工夫—境界”这一中国哲学思想的范式来研究《遵生八笺》,不止是因为二者同样地化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且有着形式、体例方面的吻合;更是在“身体”这个基础与核心上,我们认为“本体—工夫—境界”的话语体系天然契合于养生思想的研究。
就《遵生八笺》而论,所谓身体之本体,即身体的本然、应然状态;所谓工夫,即是以身体本体状态为旨归、以身体养护为中心的养生工夫,也即落脚于现实生活各层面尊生实践;所谓境界,即在尊生工夫中澄明显现的身体本真,它既是对身体本体的回归,同时也指向生命理想的最终实现,体现为身心逍遥、全身自得的生命形态。
所以,《遵生八笺》的三个部分,完全可以用基于身体的“本体—工夫—境界”体系来统摄。首笺主要是三家各派养生思想的汇总,论身体之本;中间各笺主要是务实地论述文人生活中尊生、修身事宜,物有考证,事有细则;末笺主要是对修身之理想结果的描摹,以典范人物的品格风貌、生命境界加以体现。其实,这种始以本然、应然状态的思想论述,继以身心的现实践履,终以身心品格的达成的立说方式,即“本体—工夫—境界”的模式,也正是高濂的一种思维范式。如其在《遵生八笺叙·自叙》中所言:“八者(八笺)出入玄筌,探索隐秘,且每事证古,似非妄作。大都始则规以嘉言,继则享以安逸,终则成以善行。吾人明哲保身,息心养性之道,孰过于此?”
 这一范式非但散布于各笺之内,也体现于全书八笺的组织中,这在各笺有序言性质的“高子曰”中尽有体现。如《清修妙论笺·上卷·高子曰》所述:
这一范式非但散布于各笺之内,也体现于全书八笺的组织中,这在各笺有序言性质的“高子曰”中尽有体现。如《清修妙论笺·上卷·高子曰》所述:
高子曰:摄生尚玄,非崇异也。三教法门,总是教人修身、正心、立身、行己、无所欠缺。……保养之道,可以长年,载之简编,历历可指,即《易》有《颐卦》,《书》有《无逸》,黄帝有《内经》,《论语》有《乡党》。君子心悟躬行,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岂皆外道荒唐说也?余阅典籍,随笔条记成编,笺曰《清修妙论》。

这里,高濂是为其身体观立三教根本而证之。以三教嘉言,明本书尊生所依身体观念之本然为何。以三教之共识,论证了身体本体无可置疑之地位。而所谓“心悟躬行”,实是以本笺之“心悟”,作为其后诸笺“躬行”工夫之所本,以此也能看出高濂把此笺作为立论本体的意图。
尊生之工夫,即是如何维护、尊养这个本体。接下来,本书从时间的(《四时调摄笺》)与空间的(《起居安乐笺》)、积极意义(《燕闲清赏笺》)与消极意义(《延年却病笺》)、日常饮食(《饮馔服食笺》)与特殊补益(《灵秘丹药笺》)等六个大的方面具体论述,其核心即是在各种情形下保持身体的本真状态。进一步地,根据身心的存在与运行机制,在各笺中有更周到细微、具体务实的工夫践履。
《四时调摄笺·春卷·高子曰》:“余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而配以五脏寒温顺逆之义。不务博而信怪诞不经之条,……不尚简而弃御灾防患之术,……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和其性灵,悦其心志。……诚日用不可去身。”
 此为以时养生的身心法门。
此为以时养生的身心法门。
《起居安乐笺·上卷·高子曰》:“吾生起居,祸患安乐之机也。人能安所遇而遵所生,不以得失役吾心,不以荣辱萦吾形。”
 心、形为身体之里表,且其后的“高子六安乐论”,正是围绕身心的晨昏起居、闲游交接而论。
心、形为身体之里表,且其后的“高子六安乐论”,正是围绕身心的晨昏起居、闲游交接而论。
《燕闲清赏笺·上卷·高子曰》:“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闲时则“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编成笺曰《燕闲清赏》。”
 此笺更偏重心之清赏审美,不过与蕴含天地生机、灵气之物相接相摩,亦有身之感官享受。
此笺更偏重心之清赏审美,不过与蕴含天地生机、灵气之物相接相摩,亦有身之感官享受。
《延年却病笺·上卷·高子曰》:“生身以养寿为先,养身以却病为急。”
 此笺更偏重身之袪病求安,但经由其中的导引呼吸之法,亦可得生命存在的美感体验。
此笺更偏重身之袪病求安,但经由其中的导引呼吸之法,亦可得生命存在的美感体验。
《饮馔服食笺·上卷·高子曰》:“饮食,活人之本也。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
 日常饮食,也是对生命原理的践行。
日常饮食,也是对生命原理的践行。
《灵秘丹药笺·上卷·高子曰》:“所冀智者原病合方,心运妙用,宝以护命,兼以活人。”
 方术丹药,也需要“心运妙用”地体会,并应用到护命、活人的现实治疗之中。
方术丹药,也需要“心运妙用”地体会,并应用到护命、活人的现实治疗之中。
若按以上各笺之工夫“心悟躬行”,则尊生的理想境界庶几可达,这一理想的化身即是《尘外遐举笺》所录“人外高隐,凡百人焉”。“高子”曰若达其境,“则心无所营,而神清气朗,物无容扰,而志逸身闲,养寿怡生,道岂外是”
 !在此,仍以身体话语而论身心之境界。
!在此,仍以身体话语而论身心之境界。
故而,对《遵生八笺》而言,“创意”与“养生”的融合,“审美”与“尊生”的融合,或曰“审美”与“休闲”的融合,正是在身体基础上得以实现,并表现为“身”与“心”的一“体”两面,且能够为“本体—工夫—境界”体系所充分阐释。
由此,通过对《遵生八笺》的初步分析,为我们以其身体观为基石,以“本体—工夫—境界”为理论统摄,对其全书富含休闲审美内涵的创意养生体系进行阐述奠定了思路。以下,本文即以身、心两个方面,从身体本体、尊生工夫与身心境界三个层面,展开其关于身体在世的思考与感悟,展现其作为休闲审美巨著与创意养生典范的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